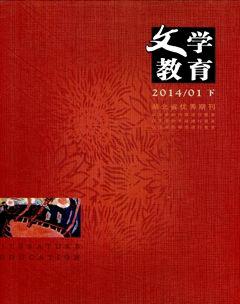憶父親姚雪垠
姚海天
2011年是先父姚雪垠百年誕辰。100年前的10月10日,父親生于河南鄧縣(今鄧州市)城西50里偏僻的不足百戶人家的姚營。因為村子周圍筑有防御土匪的高土墻,村子又叫姚營寨。父親的一生,歷經清末、民國和新中國三個歷史階段,也如20世紀新舊中國百年滄桑一樣,可謂命運多舛、多災多難。但父親的一生,也是傳奇的一生、幸運的一生。
父親一出生就經歷了第一道生死關。他雖然生于地主之家,但家道已經敗落。父親有兩個哥哥,母親不堪承受生活的重擔,決心等第三個孩子一生下來,不管是男是女,就塞進尿罐淹死。當時,家鄉溺嬰風氣盛行,但溺死的幾乎都是女嬰。幸運的是,父親在陰歷九月初八半夜里一呱呱落地,就被守護在一旁的老祖母搶救下來,才保住了小生命。
父親14歲時,同二哥到500里遠的信陽一教會中學讀書,因直奉戰爭,學校提前放假,他們在返鄉途中被土匪綁票,大約在土匪營中生活了100天。抗戰后,父親就以這段百日傳奇經歷寫出了自傳體長篇小說《長夜》。
1931年,父親在河南大學讀預科期間因參加學潮,先被逮捕,后被開除學籍,即到北平“漂泊”,以投稿維持生計。不幸染上肺病,常常大口吐血,貧病交加,生活十分艱難。肺病在當時是絕癥,父親也無錢醫治,幾年后竟不治而愈。
當然,父親一生最大的磨難,還是在政治和創作方面,屢經挫折和打擊,幾乎陷入滅頂之災。特別是1957年,他響應號召,真誠幫助黨整風,因發表《談打破清規戒律》《創作問題雜談》《打開窗戶說亮話》等文章而獲罪,經過幾場猛烈批判斗爭后,被劃為“極右派”。會上宣布,今后不能再搞創作,養起來充當“反右”教員。父親一時對前途絕望,甚至產生投江的念頭。當情緒稍稍平復下來,即以司馬遷的精神激勵自己,開始一邊痛哭,一邊偷偷寫作《李自成》。經過10個月的日日夜夜,趕在去農場勞動改造前完成了第一卷的草稿。在漢口郊區東西湖農場的三年艱苦勞動中,又對草稿進行了整理。父親原想生前出書無望,死后由后人交給國家,對祖國的文學事業作出自己應盡的貢獻。父親在1960年底摘掉“右派”帽子,不久又逢歷史的機遇,《李白成》第一卷在1963年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風靡全國。從這一點說,父親是幸運的。“文革”后,父親在他的回憶錄《學習追求五十年》中記述了《李自成》第一卷的寫作經過。他寫道:“如果讀者詢問我第一條重要經驗是什么,我必須回答說:立下較高的追求目標,在逆境中艱苦奮斗,死不動搖,不實現決不罷休。我常常一邊寫一邊哭,有時不能寫下去,只好停頓下來,等胸中略微平靜時繼續寫。可以說,《李自成》第一卷是用眼淚寫出來的。所以當1961年我將《李自成》第一卷的初稿整理完畢后,題了一組七絕抒懷,其中第一首有這樣兩句:三百年前悲壯史,豪情如淚著新篇。”
父親從1957年開始寫《李自成》起,就走上了一條艱難漫長之路,一路上風風雨雨,直到病倒,歲月長達半個世紀。父親常把寫《李自成》比做“長征”,“艱苦的長征”。在長征途中,每天凌展3時即起寫作,每天寫作、讀書、抄卡片、思考研究問題十余個小時,幾乎天天如此,年年如此。一年到頭,沒有星期天,沒有節假日,即使除夕之夜也不停筆。父親還以“下苦功,抓今天”、“耐住寂寞”、“生前馬拉松,死后馬拉松”等座右銘來激勵鞭策自己。1990年,父親在《八十愧言》中說:“我今年僅僅八十整壽,離百歲還差遠呢。我對追求事業的熱情依然未減,藝術構思能力也未衰退,我不能停止長征。”“我要像一匹老馬,馱著重負,趁著夕陽晚霞,不需鞭打,只愿在艱苦的寫作上繼續長征,中華民族的新文學需要發展,人民需要文學,我不能放下我的義務。”
父親盡管信心百倍、熱情似火,但不能違背自然法則。進入上世紀90年代后,父親明顯衰老,寫作進度越來越慢,原來字跡工整、干凈的書稿變得凌亂,掉字漏字越來越多,到處是涂涂抹抹。一天只能寫出幾百字,頂多千把字,后面還有幾個單元尚未動筆。我越來越為父親著急、擔憂,有時不免抱怨“爸爸,這樣下去,什么時候才能完成四、五卷?”父親低聲回答:“盡力吧。”不久,父親病倒了,我才意識到,父親為《李自成》已經耗盡了他的全部精力和心血,透支了生命,在最后的歲月里并在大腦嚴重萎縮的情況下(病后體檢才得知),仍在做最后的拼搏和奮斗啊。在耄耋之年仍在創作三百多萬字的鴻篇巨制,這在老作家中已是奇跡。自己的抱怨,只能加重父親的壓力和內心痛苦。多年過去了,至今回想起來,仍常常為自己對父親的抱怨感到愧疚和自責。
1972年2月,父親終于累倒了,倒在了書桌前,是因勞累過度而中風。住進醫院的第一天夜晚,我值班看護,因白天忙了一天,夜里睡著了。突然,同房另一病床的護工一邊推我一邊驚叫:“快醒醒,老人怎么躺在地上了!”我猛然驚醒,看到父親,平躺在水泥地上,我急忙跑到跟前問:“爸爸,怎么啦,怎么躺在地上了?”父親神志清醒,聲音低低地、不連貫地說:“我要起來寫《李自成》,寫不完《李自成》對不起讀者。”我一聽,眼淚奪眶而出:“爸爸,你病了,等病好了再寫不遲。”一邊說一邊和護工一起把父親抬到床上,蓋好棉被。這時我看看表,時間是凌晨3點多一點,正是父親每天夜里起床寫作的時間。這一夜,我再也不敢入睡,父親在病床上也輾轉反側,一夜無眠。這一情景,使我想起了父親在《八十愧言》中的一句話:“假若我寫作到九十多歲或近百歲,忽然醫生告訴我說,你活不多久,不能再寫作了。我不是想著我這一生曾經為祖國人民寫過多少作品,而是對醫生點點頭,表示感謝,然后輕輕嘆息一聲,在心中惋惜地說:‘可惜呀,我還有一些寫作計劃不能完成!到那時,我不得已,只好懷著愧心放下我的所有計劃,辭別人間。”
父親一生中最大的幸運是找到一位好伴侶——我的母親王梅彩。父親和母親于1931年春在開封結婚,當時父親21歲,母親18歲。兩人從此攜手度過了患難與共、相濡以沫近70年的漫長歲月。關于父母的婚姻,還有一段傳奇經歷。1930年在河南大學預科讀書的父親,因積極參加學潮,作為“共黨嫌疑”被捕,因查無證據,由河南知名辛亥革命元老、鄧縣同鄉王庚先保釋出獄。從此父親成為王先生家的常客,和母親王梅彩相識、相愛,喜結連理。婚后,父親常年奔波在外,很少回家,母親留在家鄉含辛茹苦,獨自撐起家。解放后,全家終于團聚、生活在一起,但1957年父親被劃為“極右派”,年年被評為先進工作者、積極要求入黨的母親,自然受到牽連,從此斷了入黨的夙愿。1961年,家從開封遷到武漢,母親辭去工廠教職,成為一名家庭主婦,照顧父親的生活和工作。每天忙完家務后,就戴著老花鏡,用老式打字機把《李自成》一個字一個字地敲打出來。在“文革”中,批斗、抄家成風,母親每天擔驚受怕,不知度過了多少不眠之夜。
70年代末,全家定居北京,景況好多了。在很長一段時間,為了讓父親每天吃上可口的飯菜,為了節省開支,母親堅持不請保姆,自己料理家務。每天買萊、做飯、打掃衛生、整理書房、送信、取報,從早忙到晚,把家里安置得井井有條。家里來了客人,更是忙著倒茶讓座,熱情招待,還常留下客人吃飯。人們無不交口稱贊,說母親淳樸、善良、熱情、好客、能干,為《李自成》作出了很大貢獻,是一位平凡而偉大的女性。
1992年母親不幸中風,留下癱瘓、失語、思維受損的嚴重后遺癥。母親住院兩個月,因病情危重,需要不斷交納押金,這時候父親才知道家庭經濟的拮據。有一次一時拿不出足額押金,父親像小孩子一樣號啕大哭。他萬萬沒有想到《李自成》印了幾百萬部,家里還如此清苦,連為母親交住院押金都如此困難。但父親對錢財又很慷慨。1982年,《李自成》第二卷獲茅盾文學獎,當即把3000元獎金捐給了中國少年兒童基金會。1984年,又捐出家鄉祖產房退賠款4200元,設立了鄧縣中小學生“春風作文獎”(后易名“姚雪垠作文獎”),每年又拿出一個月工資作補貼,為發展家鄉的教育事業傾盡綿薄之力。
2000年,我們子女代表母親遵照父親生前心愿,捐出《李自成》四、五卷版稅50萬元,經中國作協批準在中華文學基金會設立了“姚雪垠長篇歷史小說獎勵基金”。
父親是個性十分鮮明的人。父親的性格特點是什么?每個人因接觸不同,視角不同,感受不同,認識不同,會有不同的答案。1984年,父親應邀去新加坡參加一次文藝活動,新加坡女記者張曦娜在訪問記中寫道:“要怎樣形容姚雪垠呢?自信、直率、爽朗、豪氣、幽默……都是,但都不足以形容我眼前這位一頭銀發、神采奕奕、敢說敢言、心思靈敏、反應迅速、毫不矯情做作的作家、學者。”“姚雪垠已達74歲高齡,卻一點也沒有給人垂垂老矣的感覺。他能言善道,談得深,談得廣,言談間還透著那么一點點童心未泯的戲謔和詼諧。”
國內一些友人則這樣評價:“一個真誠、正直的人”;“一個倔強的人”;“一個滿懷天真之氣的人”:“一個有獨立人格、獨立思想,不人云亦云、隨波逐流的人”;“一個有正義感、是非感、愛憎分明、剛直不阿、錚錚傲骨的人”;“一個透亮的人,一個一旦認準真理就九牛拉不回的人”;“一個心胸極其廣闊,對真理對人民事業執著追求的人”;“姚雪垠的精神世界就像廣闊無垠的白雪一樣,具有冰清玉潔的美好品質”。當然,也有不少人認為父親是一個“自信、自負、狂妄的人”。
父親則這樣解剖自己:“我的思想性格中‘狂妄占著很重要的一面,我很少迷信名人,也不迷信名言。對許多文藝問題,喜愛發表不同意見,特別是有獨特見解的意見,決不隨聲附和、人云亦云,有時也不為權者諱,尊者諱,故常開罪于人,被斥為狂妄。”
父親在《我的前半生》中寫道:“假若你向我的老朋友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姚雪垠的性格特點是什么?你準會得到各種不同的回答,甚至是毀譽各異。假若問我自己,我會告訴你,我的性格有各種弱點和毛病,但有一個重要的特點,使我在一生中能夠屢經挫折而不曾消沉和倒下。我的這個十分重要的性格特點是非常堅強的事業心和永不消沉的進取心。”
正是由于父親的這些突出、鮮明的性格,才能使他堅忍不拔地克服種種艱難困境,成就了《李白成》,使自己的文學事業達到了高峰。現在人們也越發認識到:在世風、學風、文風不正的情況下,父親的性格和精神顯得多么難能可貴。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父親駕鶴西行已11年了。父親辭世3年后,母親也跟隨他而去。今年又迎來了父親的百年誕辰,在紀念父親百年誕辰的日子里,10月9日中國作家協會在北京舉行了紀念座談會,在其先后,中國文學學會、鄧州市委市政府、湖北省文聯和省作家協會也先后在南陽、鄧州和武漢舉行了學術研討會、紀念會和座談會,其隆重、熱烈、誠摯的氛圍讓我們感動不已、感慨不已——隨著歲月的流逝,人們并沒有忘記父親,或撰文、或著書、或發言、或講座,對父親的文學成就和人格精神給予很高的評價。
我想,父親若在九泉之下有知,一定對此會感到欣慰的。(選自《文藝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