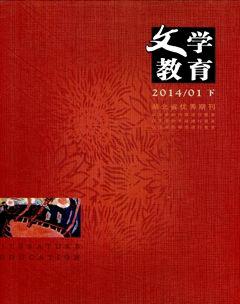純潔語(yǔ)言文字 杜絕謬種流傳
逯新君
內(nèi)容摘要:本文通過(guò)列舉當(dāng)今報(bào)刊上出現(xiàn)的諸多語(yǔ)言文字的硬傷,來(lái)反思當(dāng)今社會(huì)語(yǔ)言文字的使用不當(dāng)現(xiàn)象。認(rèn)為有必要純潔語(yǔ)言文字,杜絕謬種流傳。
關(guān)鍵詞:硬傷 例舉 引以為戒
時(shí)下,凡報(bào)刊必有錯(cuò),似乎已司空見(jiàn)慣。見(jiàn)怪不怪,其怪自敗。但諸多“硬傷”的存在,確乎讓人大跌眼鏡。以訛傳訛,謬種流傳,貽誤不淺。現(xiàn)略舉幾例,以便窺一斑而知全貌,且引以為戒。
僦不盡的<論語(yǔ)>》一文指瑕
近讀彭國(guó)翔先生的《說(shuō)不盡的<論語(yǔ)>》一文(原載《讀書(shū)》2007年第7期),受益良多。此文向大家勾勒了古人前賢和外國(guó)學(xué)者對(duì)《論語(yǔ)》注解和詮釋的大致輪廓。但文中的幾處說(shuō)明,似有不妥。
一.“何宴”應(yīng)為“何晏”。
何晏為三國(guó)魏玄學(xué)家,其網(wǎng)羅漢儒舊義,著有《論語(yǔ)集解》。“宴”的某一義項(xiàng)雖與“晏”的某一義項(xiàng)相同,且“宴”在古文中有時(shí)通“晏”,“晚”的意思,如《管子·立政》:“憲既布,乃發(fā)使者致令,以布憲之日,早宴之時(shí)。”但“晏”與“宴”是兩個(gè)不同的字,兩者之間的關(guān)系既非古今字,又非異體字(在同一時(shí)期里,音同、義同只是形體不同的字),更不是繁簡(jiǎn)字。作為人名中的用字,更不能把“何晏”寫(xiě)為“何宴”。《說(shuō)不盡的<論語(yǔ)>》一文皆把“何晏”寫(xiě)為“何宴”,實(shí)為謬誤。
二。此“皇侃”非彼“黃侃”。
皇侃為南朝梁武帝時(shí)期著名的經(jīng)學(xué)家,其廣輯自魏迄梁諸家,著有《論語(yǔ)義疏》。何晏的《論語(yǔ)集解》與皇侃的《論語(yǔ)義疏》,乃《論語(yǔ)》古注之淵藪。《說(shuō)不盡的<論語(yǔ)>》一文中言“……分別考察了何宴的《論語(yǔ)集解》、黃侃的《論語(yǔ)義疏》、朱熹的《論語(yǔ)集注》以及劉寶楠的《論語(yǔ)正義》……”,這里的“黃侃”顯然應(yīng)為“皇侃”。“黃侃”亦有其人,乃國(guó)學(xué)大家黃季剛也。黃侃師事國(guó)學(xué)大師章太炎,治學(xué)勤奮,擅長(zhǎng)音韻訓(xùn)詁,所治文字、聲韻、訓(xùn)詁之學(xué),多有創(chuàng)見(jiàn)。
三.《論語(yǔ)》乃“四書(shū)”之一,而非“五經(jīng)”之一。
眾所周知,宋代始有“四書(shū)”之說(shuō),即指《論語(yǔ)》、《孟子》、《大學(xué)》、《中庸》。宋代的宰相趙普有“半部《論語(yǔ)》治天下”的言論。唐代陸德明所撰《經(jīng)典釋文》中的“經(jīng)典”文本包括儒家經(jīng)典《論語(yǔ)》,還包括道家經(jīng)典《老子》和《莊子》。“五經(jīng)”是指《詩(shī)緲、《尚書(shū)》、《禮記》、《周易》和《春秋》,簡(jiǎn)稱(chēng)為“詩(shī)、書(shū)、禮、易、春秋”。漢武帝建元五年設(shè)立五經(jīng)博士,以此五本著作作為經(jīng)典,從而奠定了儒家經(jīng)典的尊貴地位。唐代孔穎達(dá)所撰修的經(jīng)學(xué)義疏的結(jié)集——《五經(jīng)正義》,其中的“五經(jīng)”即指此,不包括儒家經(jīng)典《論語(yǔ)》。《說(shuō)不盡的<論語(yǔ)>》一文中所言“隋唐時(shí)期……《論語(yǔ)》的注解工作并未中斷。陸德明的《經(jīng)典釋文》和孔穎達(dá)的伍經(jīng)正義》自然包涵《論語(yǔ)》……”等等,其措辭欠謹(jǐn)嚴(yán)。似有誤導(dǎo)為“《論語(yǔ)》既是四書(shū)之一又是五經(jīng)之一”之嫌。
四.何來(lái)“支言”及其他
《徐州日?qǐng)?bào)》2007年12月25日“副刊”上刊載的《用典》一文,在談及莊子行文的特點(diǎn)時(shí)說(shuō):“莊子行文好稱(chēng)‘三言:寓言、重言,支言。寓言其中就包括了很多典故;重言,就是重復(fù)別人的話(huà),就是用典;支言才是真正的自己的無(wú)拘無(wú)束的言論。”我們姑且不論其在內(nèi)容表述上是否準(zhǔn)確,單從字面上來(lái)看,這兩句文字中的“支言”應(yīng)為“卮言”才對(duì)。例如《莊子·寓言》所言:“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莊子說(shuō)他的文章中寓言和重言所占的比重很大,隨意變化的“卮言”則日出不窮,這很合于自然之道。又如《EE子-天下》有云:
“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作者把“卮”誤寫(xiě)成了“支”,屬同音誤寫(xiě)。(從行文表述上來(lái)看,這段話(huà)中第一次出現(xiàn)的“重言”一詞后的標(biāo)點(diǎn)——逗號(hào),改為頓號(hào)才好!)
2012年下半年在中央電視臺(tái)某頻道,看到一位女主持人穿著“唐裝”在講中國(guó)“古典文化”的有關(guān)內(nèi)容。其中提到古代的“修禊”活動(dòng)時(shí),把“禊(xì)”字誤讀成了(qì)。“禊”本是古人于春秋兩季臨水洗濯以祓除不祥的祭祀儀式,后成為古人的一種消災(zāi)求福的風(fēng)習(xí)。魏以后固定為三月三日,即在農(nóng)歷三月上旬的巳日,到水邊嬉戲,歡聚洗濯。《晉書(shū)·禮志下》解釋為:“漢儀,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于東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西晉作家潘岳在《閑居賦》中有云:“或宴于林,或禊于汜。”東晉“書(shū)圣”王羲之在《三月三日蘭亭詩(shī)序》中寫(xiě)道:“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huì)于會(huì)稽山陰之蘭亭,修楔事也。群賢畢至,少長(zhǎng)成集……”,對(duì)當(dāng)時(shí)進(jìn)行“修禊”活動(dòng)的場(chǎng)景,作了精彩的描繪。
總之,以上諸多“硬傷”,有的屬于“小兒科”,都應(yīng)該堅(jiān)決杜絕。試問(wèn)責(zé)任在誰(shuí)?在作者?在編者?在朗誦者?在主持人?在校對(duì)者?在審核者?……我們的激光照排技術(shù)是如此得發(fā)達(dá),各種視覺(jué)、聽(tīng)覺(jué)等媒介是如此豐富,但我們的語(yǔ)言文字的純潔度卻不高。
“為純潔祖國(guó)的語(yǔ)言文字而奮斗”此口號(hào)并非言過(guò)其實(shí)。
- 文學(xué)教育下半月的其它文章
- 難忘外公
- 我的房間
- 城城的春游
- 感動(dòng)于那一株野花
- 那夜,注定無(wú)眠
- 綠色保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