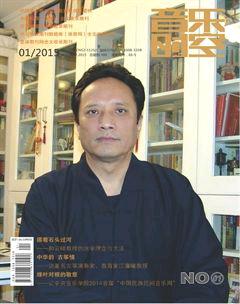民族民間音樂周精彩展演回顧濃妝艷抹總相宜
趙婉婷

2014年11月7日晚七點,來自我國云南富寧壯鄉的“坡芽歌書”民間合唱團,在中央音樂學院演奏廳上演了一場“坡芽情歌”合唱專場音樂會。“坡芽歌書”這個頗富詩意的名字,對于大多數人來說,也許還有些陌生。所謂“坡芽”,是一個毗鄰中越兩國邊境的邊陲村寨,位于云南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富寧縣剝隘鎮,“芽”指壯族染制五彩花糯飯時所用的一種“黃色的花”,“坡芽”意為開滿黃飯花的山坡。所謂“歌書”,乃是坡芽村人記載與傳承民歌的獨特方式。它以狀似原始的圖畫文字,將81首民歌記錄于一塊寬約一尺、長二尺余的土布上,每一物象對應一首歌調;當地壯語稱為“布瓦吩”,意為看著圖畫唱歌的一塊布。與壯鄉其他村子一樣,坡芽村莊也有“自幼習歌”的習俗。對于他們來說,“坡芽歌書”就是習唱情歌的教科書,從相遇相愛直至相約終身,壯族男女以此對歌聯情。情歌歌詞常作賦比興,簡潔含蓄猶如《詩經》。這次音樂會上演的十三首坡芽情歌,就是以符號與文字表達的情愛之音。
音樂會一開場,兩位“坡芽歌書”女性傳承人一邊清唱坡芽情歌,一邊手持那塊古老傳奇的畫布走上舞臺,將八十一個密密麻麻的、用紅色植物汁液勾勒的陌生字符展示給觀眾。而后,年輕的“坡芽歌書”合唱團演員手持道具與樂器,從觀眾席兩側出場,混聲齊唱著一首《趕瓏瑞》,正式開始今晚的演出。每年三月的“趕瓏瑞”是壯族民間最隆重的傳統節日,除了唱歌、跳舞、趕集之外,也是青年男女相遇戀愛的日子,故而又名“趕風流街”。以歡快輕巧的《趕瓏瑞》迅速活躍氣氛之后,二十多個演員立刻分男女兩隊,靜靜地開唱一首曲調輕柔的《命好才相會》。在合唱指揮的引領下,統一有序的氣息控制,很有分寸的輕重起伏,精心安排的男女真假聲混搭,再加上成熟的肢體語言和自不必說的良好音準,這就是“坡芽歌書”合唱團帶給觀眾的初印象——“專業”。他們演唱的曲目本身也是經過專業作曲家的二度創作,原先較為樸實簡單、變化不大的坡芽情歌旋律得到嶄新的擴展和演繹,比如《水母雞》的開頭加入了音效渲染,《火燒芭蕉》以戲曲角色和鑼鼓點開場,再加上密集的固定節奏和打擊樂烘托,突出了原先民歌的詼諧性質;除此之外,我們也能夠從表層的民歌旋律之下明顯聽出一些專業創作的手法,比如ABA的曲式安排,常規和聲進行與終止式等等。尤其是《舍得舍不得》,這首作品的主題是流傳廣泛的郎恒山歌,改編成多段體之后長度大大擴展,從主題發展、旋律進行、和聲調式變化乃至節奏型的安排、收束方式、高潮控制都十分“學院化”。相比之下,《哪里鷓鴣飛》聽上去改編幅度不是很大,它的主題是一個山歌旋律的循環往復,還原了坡芽情歌那種悠長不斷的氣息感;簡潔的旋律通過不同的歌唱方式——獨唱、對唱、齊唱搭造出了音樂的層次;《鷓鴣飛》的情緒是動情相思而暫不得,這種處理清清淡淡的,反倒很有韻味。與此手法類似的還有《逗趣歌》,很常見的民歌體裁,音樂亦十分純樸,演員們還加入了男女邊對歌邊嬉戲的舞蹈,力圖讓觀眾感受到熱鬧的鄉間生活場景。在演出的中場,由四位“坡芽歌書”傳承人穿插了一次“原生態”表演,只見他們圍坐在一起,其中一位歌者往畫滿月亮、動物、植物等物象的畫布上隨手一指,另幾位歌者當即會意,開口便唱。觀眾們從他們未加修飾的聲音中,聽到了這些民歌最原初的樣子:像山歌一樣自由的節奏,長線條的氣息,但旋律跳進很小,回環往繞,不斷重復且篇幅非常短小,男女對唱真假聲切換,聲音低而輕。情歌第一要義是“情”,雖然言語不通,但我們的確從他們毫不做作的歌聲、動作乃至表情之中感受到了真摯。之后,“坡芽歌書”合唱團重又登臺,以象征禮儀的壯族《酒歌》以及《坡芽放歌》結束了整場音樂會。
在學者汪瑤《文字敘事——坡芽歌書與坡芽情歌》的講座中,她曾談到,如同其他民族民間音樂一樣,坡芽歌書目前也存在三種狀態:一是“原生態”,即基本保持傳統、尚未變異的原初面目;二是“次生態”,即在原生態的基礎上有所發展與擴充;三是“新生態”,指引用外來音樂元素進行再創作。顯然,這場“坡芽情歌”音樂會是一場“新生態”展演,間或加入了與“原生態”的對比。作曲家們在原有曲調的基礎上進行了二度創作,原先男女對唱定情、短小簡單的山歌調,變成了有指揮、有編排、表演于舞臺的無伴奏合唱。“原生態”音樂被發現,而后衍生變異為更符合當代社會城市人審美的藝術形式,這已是多年來相當數量的民間音樂在“走出去”之后選擇的道路,也是無數次“繼承與發展”這個老問題爭論過后的結果。所謂“原生態”音樂,依托于未被破壞與“污染”的生態與文化環境,適應于“前現代”的生產方式與人際交往模式,但這種狀態不可能恒久——悖論的是,它一旦“被發現”,就意味著“將改變”。坡芽歌書雖說直至2006年才被發現,由于地理位置的偏僻以及所知人尚少,文化生態相對來講保存較好,但我們已經看到,如今的“坡芽歌書”合唱團表演的山歌改編版才是呈現于觀眾面前的主流形態,原先的情歌被催化為專業作曲家的作品。本次“坡芽情歌”音樂會作品的編創者之一劉曉耕談及過自己創作這些作品的心得,從其話語間我們可以了解,他們先入為主的西方音樂思維是不可避免的,“原生態”與專業創作之間必然會存在一種張力,同時也是一種壓力。那么現在問題來了,如何去檢驗“新生態”的成功與否呢?我想這其間并不存在一個絕對標準,對于大眾而言,聽覺的接受度是先決的,審美需求是最單純的動機,他們對坡芽山歌的印象取決于“好不好聽”;對于編創者而言,他們的目標是竭盡全力保存坡芽情歌最本真的狀態,希望“手法”與“素材”和諧共處而不是緊張沖突;而對于本民族人來講,他們在意的也許是新的音樂“像不像”,即有沒有失真?在音樂會結束之后,有一位老師問及坡芽山歌傳承人是否喜歡作曲家的改編,他們用非常樸實的語言表達了滿意之情:“我們的歌更好聽了。”事實上,在這幾方角色中,身為坡芽山歌傳承者的“局內人”的認可才是起決定作用的,這從一個角度印證了“坡芽情歌”合唱團的成功。在現代社會沖擊與審美變革之中,坡芽情歌的轉型是一種必要,也是一種必然。從聽眾的角度來說,坡芽情歌的改編依然有上升空間,不止有一種套路可以發展;我們期待多種風格的共容并存,也期待即使沒有“原生態”作參照,依然獨立、自成一體的好作品。
如今,有關“坡芽歌書”的研究工作已在學界展開,它特殊的存在方式引起了民俗學、符號學、文字學、圖像學、人類學以及音樂學等多個學科的關注,有的學者對其起源年代、形成背景以及內容意義作了詳細考證,有的學者從文字學角度對其進行界定,還有從審美、民俗和“非遺”保護方面作過研究。雖然坡芽歌書是以“民間文學”的名義申報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但它的根本屬性還是音樂,它的圖像符號是指向民歌演唱的,可是在音樂學領域,相關成果則稍顯滯后,目前僅有寥寥幾篇從音樂角度著眼的研究性論文。坡芽歌書作為一個特殊載體,在民歌傳承、曲調分析以及變異形態等方面尚待深入探討,特別是其蘊含的多學科交叉的研究潛力,望日后能夠引起音樂學界的進一步關注。
“坡芽歌書”合唱團指揮葉明菊曾在音樂會中吐露了一番肺腑之言:合唱團隊員都沒有受過專業訓練,他們來自各個基層單位,有小學教師、公務員、鄉鎮文化站職工,還有地地道道的農民。他們的家鄉很偏僻,生活與教育條件相當艱苦。深受感動的葉明菊于是決定留下,與他們一起探索坡芽情歌的“活態”傳承。通過組建合唱團、參加比賽與演出、成立研究所、出版《坡芽歌書》、申報“非遺”等等一系列工作,如今的“坡芽歌書”已有了一定知名度,這背后是許許多多像葉明菊一樣的人,他們選擇了堅守。從地方政府、專業音樂工作者到坡芽村村民,他們用不同的方式齊心協力保護著坡芽文化。我們從中感受到了他們維護傳統的熱誠以及對外界接納的期待,也看到了一條趨于完善、成熟的民間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鏈。正是在這樣的嘗試與協作中,身處激流中的“原生態”民間音樂,完成了它的記憶與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