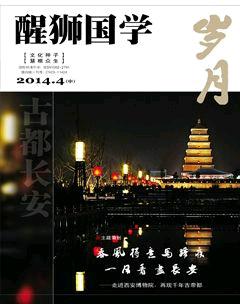引言 長安久聞
田繼偉+薛瑞芳
人類是大自然這位母親香醉懷抱孕育出的萬千物種的“后生”“晚輩”。一群在三疊紀大毀滅中幸存下來的小型哺乳動物,是我們“最近的父母”。此處無關單細胞,無關三葉蟲。斗轉星移,時光荏苒,此處省略萬千字符,或根本無法用簡單的維度來衡量這里的久遠。
我很難想象人類的嬰兒時期,是如何的脆弱,如何的無助,如何摸著“冰冷”和“孤獨”,漂泊在這顆藍色的星球上?是哪些偶然和必然,使得人類向著“主宰”這顆原本懼怕的星球的方向,義無反顧的前進?進而又是哪些要素的作用,使得人類走向繁榮昌盛、文明富庶?
文明的曙光太刺眼了,使我們的眼睛一下子致盲。等我們的雙眼完全適應了光,我們的記憶卻沒有跟上。剛才的適應過程經歷了多久?無人相告。斷裂,記憶在維度中無法相繼,只有我們面對文明的殘痕時才想起了邏輯的前因。線索若有似無,有力與孱弱相伴,我們用力的揉揉眼睛,慢慢地憶起———盤古大陸的東方有一塊神奇,至今,令人向往。
長安,不知我們用今生截取的是你生命的哪個部分?暢想未來,自然過問既往,我的先祖來自何方?訣云:三皇五帝夏商周……從蠻荒的口耳相傳中走來,在時光的走廊里標注了段落,有了名,連續流轉未曾斷絕。
“長安”,這個名字來自哪里?最遠的記錄載于《史記》之中:秦始皇的弟弟成蟜帥秦軍攻趙后,被封為長安君,這就是“長安”二字的最早出現,當時還不是一個作為“國之中心”的稱呼。按照秦人的習慣,基本活動中心還是在咸陽附近的鄉聚,長安自然還沒有登上現在的名頭。到了公元前的202年漢高祖劉邦才正式的將大漢帝國的首都定名為長安,從此這美好的寓意也就始終保佑著這片黃澄澄的土地。當時,西漢王朝的都城像一塊大大的磁石,吸引著世界的目光。就這樣,長安像個蹣跚學步的孩子,跌跌撞撞的走過了近800年的時光。
公元618年,隋唐的長安在外國人口耳相傳中頻頻成了“胡姆丹”或者“庫姆丹”,這種歷史證據在中外多見:西晉末年《粟特文信札》中有“XWMTN”,很明確的指出長安被稱為“胡姆丹”。在阿拉伯文獻《蘇萊曼東游記》《黃金草原》《世界境遇志》以及中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中就有“鐵證”。2003年在西安北周史君墓出土了一篇題銘,粟特文33行,漢字18行,記載了一位粟特人在公元579年以86歲高齡長眠于“庫姆丹”。粟特文中的“庫姆丹”這個名詞,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長安”。
隋唐的長安變成了中國人心里永恒光明的字符。隋富唐強,物質的極大豐富造就了萬邦來朝的盛世奇章,開放的社會風氣和海納百川的氣魄則造就了文化層面的不斷擴張。這里有大唐飛歌,這里有大唐詩云,這里也大唐萬千氣象———長安,蔚然可觀!當然,長安的歷史不能盡數,也有太多的信息消逝在煙塵中,在我們不經意的指尖滑落,要完全復起舊觀實在不可能,但是只要靠近長安,用自己的感覺來承接文化的溫度,我們就能在溫暖中戰勝千年孤寂,克服對未來未知的恐懼,成全自己今日現世的小美滿。
如今,長安流遠。這里的山水人文猶在,這里的風土人情猶在,這里暖暖的“小文藝”猶在,就像陜西人至今還在稱“鄉黨”,至今還在“諞閑傳”,還在“侍弄”這片土地。這就是我的長安,一顆驕傲的心臟永遠隨著他跳動,隨著他一起“嘹咋咧”。
第一次來長安的人,可能會被這里的文物遍地、遺址處處所吸引。古城“水深”,若是不具備中華歷史人文的底蘊,便只能無聊閑逛,莫可奈何。這里的歷史氛圍厚重,即使五次三番的來到長安,也是很難一日看盡長安花的。如果能夠做到仔細品味、耐心觀察,在這里就一定能找到一個個文化的“源頭”,那種“認祖歸宗”的喜悅,足以讓人喜極而泣。愛長安,愛這片土地的根,那千般的等待終究化作了蝶戀雨花的嬌媚,永遠的滋潤子孫炎黃。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