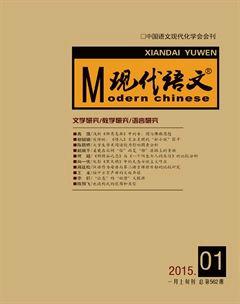試論張愛玲作品中的懷舊意識
摘 要:張愛玲是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上值得花費筆墨去研究、挖掘的女作家之一。張愛玲的作品,有許多沒落家族的故事,蘊含著濃郁的舊式文化的氣息,熔鑄了懷舊的血液。張愛玲作品中的懷舊意識主要體現(xiàn)在頹廢的藝術(shù)與古典意象上,顯現(xiàn)了身世經(jīng)歷及傳統(tǒng)中國小說對張愛玲懷舊意識的影響。筆者認為張愛玲作品中傳達的懷舊意識表達了其對不公時代的“回避式”反抗。
關(guān)鍵詞:張愛玲 懷舊 回避
一、前言
懷舊的英文單詞是nostalgia,原來是由兩個拉丁字母組成:nostos,回家;algia,一種渴望。即“渴望回歸一個早已不存在或從未存在的家園”之意。懷舊是試圖通過回到過去,從而克服虛妄世界中的失落和頹廢,追尋和重現(xiàn)故去歲月的優(yōu)美和崇高的一種獨特的心理狀態(tài)。蘊蓄于張愛玲作品中的內(nèi)在情緒便是對歷史與人世滄桑的喟嘆,這種喟嘆中又飽含了濃濃的懷舊意識。
二、懷舊意識在張愛玲作品中的體現(xiàn)
(一)頹廢的藝術(shù)
懷舊意識在張愛玲作品中主要體現(xiàn)為頹廢藝術(shù),表現(xiàn)了一種逸出現(xiàn)代主流時間軌道的獨特性。她作品中的舊式生活和舊家子弟都有著一種深刻的頹廢感,其中氤氳著一種讓人沉迷的鴉片式的氣味。
張愛玲描繪了一個又一個與世隔絕的小小“清朝”,他們既是《玻璃瓦》中姚先生的家,《傾城之戀》中的白公館,也是《金鎖記》中的姜公館等沒落的舊式貴族家庭。她通過對舊式家庭日常生活細節(jié)、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等的描寫,將過去的舊式生活轉(zhuǎn)化為環(huán)繞主人公揮之不去的背景。她筆下的舊式生活充滿頹廢感,沒落的都市、封閉的房間、畸形的愛情、扭曲的婚姻還有變態(tài)的人性,恰如《金鎖記》中“一步步走向沒有光的所在”,舊式文化的衰落在這種頹廢的背景中得到真切的表現(xiàn)。
她筆下的這類舊式子弟,時或有一種玩世的瀟灑、無所追求的自在,比如《金鎖記》里的姜家老三姜季澤,他交游廣闊,斗雞走狗無所不包,不僅吃光了他自己的那一份遺產(chǎn),而且還動了公帳,雖然好尋花問柳,對嫂子七巧時不時言語挑逗,但嚴守叔嫂的大防,點到即止、游刃有余,使七巧倍受情欲的折磨;再比如《傾城之戀》里的范柳原,從英國回來的花花公子,一點也不相信愛情,但在談戀愛方面則是個無往而不利的高手,是個精致的愛匠。這些人物或多或少都沾染了一些晚清遺少的色彩,這些遺少通常都帶有一些皇氣,如若所處的朝代即將沒落,他們便等不及了似的拼命玩樂,坐吃山空、狂賭爛嫖,在喝不完的醇酒和抽不完的大煙中迷醉自己的一生,她的筆墨在華麗之中沉浸著頹廢感。這是一種頹廢的藝術(shù),張愛玲很好地表達了一種頹廢美,這種頹廢美來自于一種深刻的時間感受,既沉浸在現(xiàn)實時空中又出離于現(xiàn)實時空,既是俗世中人又冷眼觀世,既熱鬧又空虛,浸透了深深的文化宿命感。
(二)古典意象
懷舊意識在張愛玲作品中的另一體現(xiàn)是她對古典意象的運用。其筆下的精彩意象,皆取自舊日生活室內(nèi)的基本陳設,都是人們所熟悉的器物,通常都帶著鮮艷的色彩和綺麗的紋飾,具有濃厚的象征意味。
最為典型的古典意象莫過于月光。張愛玲喜歡寫月光,她筆下的月亮通常有不同的模樣:“年輕人想著三十年前的月亮該是銅錢大的一個紅黃的濕暈,像朵云軒信箋上落了一滴淚珠。”[1](P47)在張愛玲的文中,幾十年前的月亮是虛化的景致,而信箋上的淚珠則是具體的實景,王安憶把這種筆法稱作“以實寫虛”;而當七巧要兒子長白給她徹夜燒煙并談起兒子的房中私事時,媳婦芝壽所看到的月亮卻是這樣的,“隔著玻璃窗望出去,影影綽綽烏云里有個月亮,一搭黑,一搭白,象個戲劇化的猙獰的臉譜,一點,一點,月亮緩緩的從云里出來了,黑云底下透出一線炯炯的光,是面具底下的眼睛。”[2](P64)這里對月亮的描寫避免了約定俗成,通過描寫一個迥然不同的月亮意象和主人公的心理、命運相對照,以“陌生化”的方式來寫月亮,寫出了七巧對兒子病態(tài)的愛意和對媳婦不動聲色的折磨,與此相對照的月光也少了幾分皎潔,多了幾分猙獰,幾分可怖。還有一處,小說開始時小雙和鳳簫在房中竊竊私語,偷偷在背后談論七巧的身世,此時的月光別有一番風味:“天就快亮了,那扁扁的下弦月,低一點,低一點,大一點,像赤金的臉盆,沉了下去”[3](P48),恰如唐詩“夜深聞私語,月落如金盆”的意境。除此以外,在張愛玲的成名作《沉香屑·第一爐香》中還有更集中的意象描寫,“梁家那白房子在白霧里,只看見綠玻璃窗里晃動著的燈光,綠幽幽的地,一方一方,像薄荷酒里的冰塊。”[4](P39)這個意象也是“以實寫虛”,通過酒中的冰塊這個誘人的意象具體地展現(xiàn)了主人公葛薇龍初到香港時內(nèi)心的欲望和掙扎。月亮象征著美好理想,就像是“一頭肥胸脯的白鳳凰”[5](P40)那樣的美好,前程似錦,展翅欲飛。當薇龍初遇愛情時,此處的月亮是“黃黃的,像玉色緞子上,刺繡時彈落了一點香灰,燒糊了一小片”[6](P42),顯得朦朧羞澀,讓人又忐忑又喜悅。而在薇龍真正陷入與男主人公喬琪的愛情中時,她在月光下的等待,充滿了沉甸甸的心事,顯得格外動人,“那陽臺如果是個官鳥漆小茶托,她就是茶托上鑲嵌的羅錮花,她詫異她的心里那般的明晰,她從來沒有這樣的清醒過。”[7](P44)這個絕妙的比喻恰如其分地點出了薇龍對這份感情的堅定和執(zhí)著,這也是小說中唯一一處比較明凈溫馨的描寫。而當薇龍和喬琪發(fā)生了關(guān)系,愛情發(fā)生了質(zhì)變后,那月又變成了“一團藍陰陰的火”[8](P44),充滿了肉欲的色彩,用一種冷峻的語調(diào)嘲弄著他們的愛情,他們的愛情原先是浪漫的,之后卻耽于肉欲的沉淪,“藍陰陰的月”暗示了薇龍的沉淪。在薇龍對愛情感到極度絕望時,月亮“如同冰破處銀燦燦的一汪水”[9](P45),月夜里“到處都是嗚嗚咽咽笛子似的青輝”[10](P45)。不同的月光代表了主人公不同的心理狀態(tài),反映出了薇龍在不同的階段里性格上的一點一滴變化。
此外,在張愛玲的作品中,《金鎖記》中“屏風上的金絲鳥”、《更衣記》中曬衣服時“樟腦甜而穩(wěn)妥的舊味”、《我的天才夢》中把人生比作“華美的袍,上面爬滿了虱子”等,都是她筆下一些經(jīng)典的物象,令人印象深刻。張愛玲在文本中最擅長的,便正是借助這些舊式的意象烘托出小說中人物不可名狀的心緒和命運。即一種在文中一以貫之的“蒼涼感”。
三、身世經(jīng)歷、傳統(tǒng)中國小說對張愛玲懷舊意識的影響
(一)身世經(jīng)歷
張愛玲出身于前清名門,祖父張佩綸二十四歲中進士,授編修充國使館協(xié)修官,在仕宦生涯最得意時期,曾在福建督軍中擔任三品欽差大臣會辦海疆大臣之職,后雖然仕途不順,但得到了李鴻章的賞識,并偶然結(jié)識了晚清名臣李鴻章之女李菊耦,和李鴻章成就了一段翁婿之緣。張佩綸與李菊耦雖然年齡相差較大,但是婚姻生活很幸福,他們談詩作畫,琴瑟和鳴,還生下了兒子張延重女兒張茂淵。張延重就是張愛玲的生父,是個典型的晚清遺少,他的妻子黃逸梵也是名門望族的千金,祖父是清末首任長江水師提督黃軍門黃翼升,顯赫的家世給了張愛玲一個幸福、富足的童年。1992年,張廷重夫婦由上海搬到天津,“我父母二十六歲。男才女貌,風華正盛。有錢有閑,有兒有女。有汽車,有司機,有好幾個燒飯打雜的傭人,姊姊和我都還有專屬的保姆。那時的日子,真是何等風光。”[11](P31)但是這樣的幸福和平靜因為張延重的遺少作風而被打破。張延重的一生,就是吃喝嫖賭的浪蕩子的一生,抽鴉片,養(yǎng)姨太太,如此種種,不一而足。他的家業(yè)、身體和精神,都在鴉片的裊裊余煙中一點點消散殆盡。最后,他的妻子選擇和他決裂,開始新的生活,勇敢地出國留學,從此張愛玲開始了缺少母愛、獨立成長的人生,在舊式的家庭中深受了舊文化的熏陶。張父代表著那個頹靡的、逐漸沉淪的,但又充滿日常細節(jié)感觸的舊文化的世界:“另一方面有我父親的家,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鴉片、教我弟弟作‘漢高祖的老先生,章回小說,懶洋洋灰撲撲地活下去。父親的房間永遠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覺得沉下去,沉下去。”[12](P113)“房屋里有我們家的太多的回憶,像重重疊疊復印的照片,整個的空氣有點兒模糊。有太陽的地方使人瞌睡,陰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涼。而在陰暗交界的邊緣,看得見陽光,在那陽光里只有昏睡。”[13](P114)
從《對照記》中所列的相當可觀的張愛玲祖父祖母一代人的照片中,同樣也可以讀出身世經(jīng)歷對張愛玲懷古意識的影響。她深深地懷念著她祖父祖母那一代人的人物和生活,這自覺或不自覺地展露了她的歷史懷舊意識。正如其中所說的:“我沒趕上看見他們,所以跟他們的關(guān)系僅只是屬于彼此,一種沉默的無條件的支持,看似無用,無效,卻是我最需要的。他們只靜靜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時候再死一次。我愛他們。”[14]
(二)傳統(tǒng)中國小說
傳統(tǒng)中國小說中所描繪的舊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日常習俗、道德規(guī)范等以一種文化沉淀的形式滲透到張愛玲的意識中,使其作品無意識地透露出傳統(tǒng)性的復歸懷舊指向。傳統(tǒng)中國小說主要指:《紅樓夢》《海上花列傳》《金瓶梅》等。
尤其是曹雪芹的《紅樓夢》,這部中國古典小說的集大成之作倍受她的推崇和贊賞。八歲時第一次讀《紅樓夢》,十四歲時,張愛玲創(chuàng)作了一篇長篇的鴛鴦蝴蝶派的章回小說《摩登紅樓夢》,直至晚年,她還以十年時間研究《紅樓夢》,1976年這些文字結(jié)集出版,書名叫作《紅樓夢魘》——可見她對此書的瘋狂癡迷。在《紅樓夢》中,曹雪芹用細膩的筆調(diào)勾勒了整個封建大家庭的生活情態(tài),塑造了百余個氣質(zhì)心理鮮明迥異的人物形象。自然,受《紅樓夢》的筆法影響,張愛玲的文章也會出現(xiàn)大量描寫舊式家庭或半新半舊家庭內(nèi)部的生活情態(tài)的片段。在這些片段中,紅樓夢式的人情百態(tài)、情感結(jié)構(gòu)、言行舉止、想法意識,都構(gòu)成了一種舊的場景、舊的氛圍。這種舊的氛圍,無疑是張愛玲最為熟悉和偏愛的。
她曾稱《紅樓夢》和《金瓶梅》“在我是一切的源泉,尤其是《紅樓夢》”,正如《中國人的宗教》有言:“中國文學里彌漫著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質(zhì)的細節(jié)上,它得到歡悅——因此《紅樓夢》《金瓶梅》仔仔細細開出整桌的菜單,毫無倦意,不為什么,就因為喜歡——細節(jié)往往是和美暢快,引人入勝的,而主題永遠悲觀,一切對于人生的籠統(tǒng)觀察都指向虛無。”傳統(tǒng)中國小說所透露的傳統(tǒng)舊式文化的意識已經(jīng)深入其骨髓,她欣賞的是在新時代和新都市中尚且留存的古典美,保有一點凄涼的意味,在懷舊的過程中感傷人生,抒寫對舊時代和舊生活的懷戀,在懷戀中感受蒼涼和空虛。
從心理學來說,懷舊是一種自欺,是人類心理自我平衡、自我調(diào)節(jié)的一種手段。一旦人在眼下的現(xiàn)實生活中沒有快樂,沒有幸福,便會從過去的生活里找尋曾經(jīng)有過,或自以為有過的幸福和快活,以安慰現(xiàn)實生活中的生存難堪與尷尬。張愛玲深深植根于舊式文化中,不遺余力地描述著遺老遺少的舊式生活,明明知道這些舊式的人物、生活未必是好的,甚至處處彌漫著腐爛的氣息,可還是深深陷入其中,無法自拔。這正表現(xiàn)出張愛玲對新舊交替、戰(zhàn)亂頻繁的中國社會現(xiàn)實的“逃離”:她既無法挽留歷史車輪的前進的腳步,又不懂得如何來面對、如何去適應紛繁復雜的現(xiàn)實生活。她是時常被時代所拋棄的不幸兒:1939年以遠東地區(qū)第一名的好成績考上了英國倫敦大學,戰(zhàn)爭打碎了她的出國夢,1942年,香港被日本占領(lǐng),再次戰(zhàn)爭打碎她保送去英國的夢,她在香港大學的好成績也頃刻間變成一堆廢屑。對她所處的時代,她是這樣認識的:“這時代,舊的東西在崩壞,新的在滋長中……人是生活于一個時代里的,可是這時代卻在影子似的沉沒下去,人覺得自己被拋棄了。”[15](P187)在這樣一個時代里,一切都指向虛無,沒有悲壯和博大,只有蒼涼和幽深,張愛玲不得不在過去的舊式生活中尋求慰藉,這也是張愛玲對不公時代的一種“回避式”的反抗。
注釋:
[1][2][3]張愛玲:《金鎖記》,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
[4][5][6][7][8][9][10]張愛玲:《沉香屑·第一爐香》,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
[11]張子靜:《我的姊姊張愛玲》,上海:文匯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頁。
[12][13][15]張愛玲:《流言》,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
[14]張愛玲:《對照記》,廣州: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頁。
(李麗 江蘇南通 南通大學文學院 226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