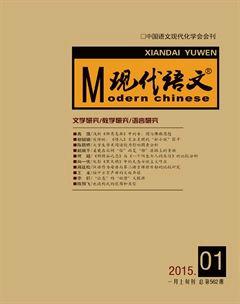黑白交錯之美掩蓋下的女性悲哀
向一優+田密
摘 要:影片《黑天鵝》在電影界、觀眾界及評論界都引起了相當關注,已有諸多影評。結合當下文化語境對影片本身及相關批評進行綜合考察可以看到,影片通過“黑”“白”意象的凄美幻滅突破了傳統一元單向度思維、拋卻了非此即彼二元對立論,從而內隱著一種生態女性主義吁求。只是在真正多元共生的生態時代尚未完全到來之前,影片以黑白交錯之美非常隱晦曲折地傳達了這種生態女性主義吁求。而影片中促進“黑”“白”轉化的“血紅”則深刻地隱喻了當下整個時代普遍存在的生態危機。
關鍵詞:黑天鵝 黑白交錯 生態女性主義 吁求
緒論
2010年末上映的由美國獨立導演達倫·阿羅諾夫斯基執導的《黑天鵝》作為當年第67屆威尼斯電影節開幕影片,其主演女星娜塔莉·波特曼更憑借此片獲得包括金球獎和奧斯卡獎在內的多項最佳女主角獎,該片普遍被定義為一部心理驚悚片。作為一部具有如此影響力的影片,從業界以及整個觀眾群體對它的強烈反應來看,這部影片完全可以作為一個文本進行文化研究。它固然不能完全代表一個時代的精神訴求和文化走向,但卻從某個側面折射出一些重要的時代信息和文化趨向。
就目前對此片進行評論的文章來看,主要分為兩類。一類的主要觀點傾向于認為“黑天鵝”是女主角的完美蛻變:《讀<黑天鵝>中妮娜的三重人格》和《關于個人釋放心魅與本欲的“內斗”》運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對女主角的三重人格進行了清晰地分析,[1]《解讀影片<黑天鵝>主人公的雙重人格》對母權制下的主體人格和后繼人格雙重人格的爭斗進行了分析,[2]《<黑天鵝>:自戀與完美的達成》從女性主義角度認為這部影片精確地展現了主人公從白天鵝向黑天鵝轉變中的掙扎和解脫,[3]《從女性主義角度分析電影<黑天鵝>》對主人公向黑天鵝的蛻變產生了疑惑,[4]《從電影符號學視域解讀<黑天鵝>》運用格雷馬斯符號矩陣對影片的編碼進行了意義解讀。[5]總體來說,上述文章傾向于將“黑”視為解救的方向。另一類觀點進一步對“黑”進行解讀,認為“黑”依然具有他者建構性,由此對“黑”產生懷疑。這類觀點主要有:《淺談獲獎電影<黑天鵝>的精神藝術》用拉康精神分析理論和電影符號學認為此片的現實隱喻為人格的破裂,[6]《電影<黑天鵝>的精神分析美學解讀》運用拉康鏡像理論注意到男性視角的窺視,[7]《看女性難以逃脫的“他者”“被看”地位——從女性主義視角解析電影<黑天鵝>》深刻地認識到女主人公被凝視的地位并將批判的矛頭直指片中芭蕾舞劇的藝術總監托馬斯,[8]《身份與符號的自我:<黑天鵝>關于身份的命題》指出該片展示了從傳統到當代社會競爭機制轉變過程中相悖身份的自我淪落。[9]
以上文獻對《黑天鵝》所展現出的矛盾人格進行了清晰的論述,并對這種矛盾的內在原因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討,若結合電影文本本身并對以上兩種觀點的文章進行綜合考察,可以發現作為“黑”與“白”兩個意象的深層意蘊。任何單一的“白”或者“黑”都非解救之途,電影通過“黑”“白”意象的凄美幻滅拋卻了非此即彼二元論,從而內隱著生態女性主義的吁求,而這似乎正是當今世界整體面臨生態危機的一個深刻隱喻,或許這正是此片叫好又叫座的深層原因。
一、生態女性主義的批評立場
“生態女性主義是婦女解放運動和生態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是女權運動第三次浪潮中的一個重要流派。”[10]整個女性主義“第一次浪潮以19世紀后期到20世紀初期為其時段,以爭取婦女的權利為其目標;而第二次浪潮則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以反對性別歧視為其內涵;從20世紀70年代以后則以與其它各種文化理論交流對話為其特點,衍生出后結構主義女性理論、精神分析女性理論、后殖民女性理論以及生態女性主義等等,成為‘后現代語境下的女性主義理論。1974年,法國女性主義者奧波尼(Franoised Eaubonne)首次提出‘生態女性主義這一術語,目的是將女性運動與生態運動相結合,推動兩者的深入發展。”[10]
作為生態批評的生態女性主義需要堅持文本、文化與哲學批評三者的耦合、整生,關于文化一維需要注意的應該是如何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立場,因“女性”也是在特定歷史語境下的建構。在對電影文本進行分析之前我們需要簡要闡述一下生態女性主義在哲學層面的觀點。[11]
生態女性主義對傳統哲學的批判。美國女性主義哲學家沃倫(K.J.Warren)認為,“在男人對女人的統治和人類對自然的統治之間的聯系,最終是概念聯系,其特征有三:1.價值等級思維,認為處于等級結構上層的價值要優于下層的價值;2.價值二元對立,把事物分成互相對立排斥的雙方,使其中一方比另一方有更高的價值;3.統治邏輯,即對于任何X和Y,若X價值高于Y,則X支配Y被認為是正當的。沃倫認為問題不在于等級思維,甚至也不在于價值等級思維。因為在日常生活中,等級思維對分類資料、比較信息、組織材料都是重要的。價值等級思維在非壓迫的語境(context)下也是可以接受的。例如人們可以說, 因為人有意識能力,所以人比植物或巖石能更好地重組環境。問題在于統治邏輯。這種批判不是拒斥所有理性或接受非理性,而是要批判作為統治形式的理性。”[12]這就為真正趨向多元既指明了方向,又從傳統哲學中吸取了有益成分作為前進動力,它從根本上避免了傳統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弊端,同時又肯定了二元對立思想的有用成分。繼而他指出“二元對立的問題不在于承認對立雙方的差別,而在于它使差別變成等級關系”。由此,“生態女性主義在運用性別分析的工具來批判西方主流哲學中抽象男性化理性、工具理性及其價值方面,有獨到的深刻之處。顯然,它不是要回到性別壓迫更深重的前現代社會,而是向往一種多元化、有差別、但沒有等級壓迫的平等的社會,并提出一套性的價值體系和倫理準則。”[12]
“生態女性主義要建立一種語境倫理學”[12],這種對語境的考察在批評中轉換為對具體文本審美結構的考察,就成為了在堅持尊重文本基礎上與文化、哲學生態審美批評的三者耦合、整生的切入點,[11]從而可以在生態文化批判的同時兼顧到生態審美批評,而不溢出文學批評本體之外。正是在此立場上,筆者展開對電影《黑天鵝》相關批評的再批評。
二、對“由‘白轉‘黑本我釋放”的再批評
道德是維系人類社會正常運行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維度,只是在某種道德信仰異化為“超我”對“本我”實行壓制使人趨向單向度的人時,這種“超我”才值得批判。故而,對緒論中第一類文章關于“黑天鵝”對本我釋放的批評進行進一步考察,我們可以看到不一樣的景觀。
影片講述的是一個芭蕾舞演員為成功出演舞劇《黑天鵝》的領舞而在精神分裂中成功完成了角色但生命走向了毀滅的故事。電影中的舞劇《黑天鵝》是對經典芭蕾舞劇《天鵝湖》的改編,公主被魔鬼施咒白天變為天鵝,晚上才能以人形出現,只有遇見真愛才能解除咒語,王子的出現讓公主有了解救的可能。但在王子與少女再次相遇時公主被魔鬼的女兒掉包(她以和公主同樣的容貌出現,只是身著黑裝),王子被“黑天鵝”引誘,當王子明白真相時,后悔莫及,王子請求公主的原諒,公主也原諒了他,最后在眼看真愛將要實現時,魔鬼掀起巨浪要淹死王子,公主為救王子跳湖身亡。電影中的領舞需要同時兼具白天鵝的純潔、守矩與黑天鵝的誘惑、放縱。妮娜從小在母親的嚴格要求下刻苦訓練,技巧精湛、追求完美,是白天鵝的最佳人選。在前任領舞退出之后,妮娜要完成向黑天鵝的蛻變方能擔當領舞角色,為此她在舞劇藝術總監托馬斯的引導以及和作為誘惑、放縱象征的莉莉的交往中逐步挖掘自身內在的“黑暗”本質,在此過程中出現了精神分裂,并以此為代價成功出演了領舞角色,贏得了觀眾的認可,影片以妮娜最終倒在舞臺仰望舞臺上方絢麗的燈光中結束。
在緒論中提及的第一類文章中通常將“白天鵝”及相關意象群視為“超我”,而將“黑天鵝”及相關意象群視為“本我”,故事主人公即處在這種“超我”與“本我”的撕裂狀態中。用生態女性主義的視角審視這種“黑白”意象,對“黑”或者“白”都不能簡單褒貶。“白”值得批判是因為這種對“白”的塑造是母權制度(這種母權制度并非女性主體性的張揚,而是母親因年輕時生育妮娜而放棄舞蹈事業,從此將導致生育的性愛視為罪惡的淵藪,她并沒在此遭遇下清醒認識到自己的女性角色,反而潛在地將自己男性中心主義化,從而導致對女兒妮娜的控制)下對妮娜的單向度規約。而“白”中所代表的純潔、遵守秩序卻是不能拋棄的,純潔作為人類文明追求的愿望不可或缺,秩序作為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工具同樣至關重要。在此,需要對“白”做歷史唯物主義的審視:《天鵝湖》芭蕾舞劇作為一種經典的古典文化藝術,其古典文化蘊涵的某些文化機制在與當下現代性與后現代語境中的遭遇下出現碰撞,需要剝除的是秩序中作為壓制的“統治邏輯”,但它至今仍能打動觀眾,其中白天鵝(從電影中舞劇的表演最終又變為白天鵝從高處跳下的凄美可見人們對其的復雜情緒)傳達出的純潔之美就有一種超時代意義。
對“白”與“黑”的轉化以歷史主義的角度來看待,它反映的是特定歷史時期精神文化的轉向,只是在當下這種多元文化態勢的語境中,從由“白”向“黑”的轉化過程中可以看到女性本我得以解救的可能,而非女性自我的終極解救。妮娜在托馬斯和莉莉的刺激下激起的久被壓抑的“本我”性欲及對性欲的自我滿足,對于突破作為母權控制下的單向度人生具有積極意義,但作為蘊含著性這種自然欲求的“黑”的意象并非完全蛻變成解救的終極點。由“白”到“黑”轉化過程中爆發出的生命力值得肯定,而這種生命力突出重圍之后又受到更加復雜異化力量的規訓則是下文需要解讀的。
三、對“鏡像塑造下黑色毀滅”的再批評
影片中鏡子的運用無處不在,用拉康鏡像理論透視妮娜在向“黑天鵝”蛻變過程中受到男權話語的凝視,從而淪為他者,這是緒論中第二類文章的主要觀點。在家里,妮娜通過三面鏡子矯正自己的舞姿,母親墻上畫的各種頭像以及妮娜的照片也作為一種潛在的鏡像對妮娜的自我進行塑造,甚至年輕時同為舞者的母親一直以黑衣示人的威嚴的形象也構成了潛在的對妮娜自我塑造的鏡像。在舞蹈團,妮娜更是要在巨大的鏡子面前跳舞,同時接受舞蹈指導及藝術總監托馬斯眼光的凝視,當然也有舞者之間的羨慕、嫉妒等等眼光穿梭交織成的多棱鏡似的對自我的編織。在舞臺,整個舞蹈團的表演受到臺下觀眾目光的凝視。此外,我們還可以通過托馬斯舉辦酒會吸引資金這個細節,看到托馬斯一方面作為男權凝視之眼對妮娜及其他舞者進行凝視,同時他本身又被操控資本背后的贊助商所凝視,批判進行至此,其觸角已經深入到對整個資本主義當代社會的批判,似乎無所遺漏。
但辯證來看,鏡像塑造自我似乎不可避免,在此塑造過程中,既有權力之眼滲入對自我的操控,也有多重鏡像碰撞產生碎片從而對作為“統治邏輯”的突破。妮娜在痛苦地向“黑天鵝”這個角色轉化的過程中,出現精神分裂,將內在放縱、魅惑的自我投射到莉莉身上并在與其的破壞和爭奪中完成了轉化。值得注意的一個細節是,殺死作為幻像的莉莉(其實是妮娜本人)的正是一塊破碎的鏡片,而舞罷“黑天鵝”一段后幻象消失,妮娜清醒過來意識到自己刺中的是自己而留下心酸眼淚時,鏡頭再次對到了這枚破碎的鏡片。清醒之后的妮娜繼續完成了接下來的“白天鵝”部分舞蹈,最后在聚光燈下、在母親滿含的熱淚中、在萬眾矚目中完成了“白天鵝”從高處縱身跳下的一幕,電影在妮娜說出“我終于感同身受……我感受到了完美”之后的強烈聚光燈中結束。
正是在這種塑造與突破之間的轉換中,人性的光輝得以閃現,用生態女性主義的觀點來看,能更好地認識到鏡像塑造的中性價值。比如,對“白天鵝”的塑造表達了對純潔真摯愛情的向往,對“黑天鵝”的塑造表達了對被壓抑的人性本我的張揚,“白”與“黑”作為對立二元是有差別的,我們不能抹殺這種差別,也不能輕易認定一方正確而另一方錯誤,而應該在尊重這種差別的基礎上更全面地對電影進行審美閱讀,而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作為“統治邏輯”的在此鏡像塑造自我過程中對多向度自由主體的單向度化。但無論“黑”“白”均是一種殘缺的美,這是時代隱喻在藝術處理上的客觀態度。而影片仍潛在地透露出一種多元化的時代氣息,雖然這仍是一個歧難,而這正是筆者對此片作一遠觀而聽到的生態吁求。
四、黑白交錯之美掩蓋下的生態訴求
影片以如此交錯斑駁的手法展現出的美既令人感到壓抑、驚悚,又讓人震撼、陶醉難以忘懷,適當對其進行生態女性主義的再造性閱讀或許能讓讀者更好地感受其藝術感染力,而不至于在此撕裂的藝術張力中渙散掉對影片的品味。而此再造性閱讀的依據在于,影片鏡像展現出的狀態并不等于影片本身,鏡像語言背后的動作包括電影結尾處的字幕背景顏色轉換仍然隱隱傳達出一種呼喚。
影片末尾妮娜在舞臺上完美展現了“黑天鵝”的魅力,將壓抑已久的本我激情完全釋放出來,使影片達到了高潮,但影片沒有停留在對“黑”絢麗綻放的展示。在向高潮遞進的過程中,妮娜全身逐漸生出黑色羽毛(這雖然是妮娜的自我幻象,但在影片的第一次展示中給了影片觀眾同樣的逼真的強大藝術震撼),而對羽毛生出的特寫,電影配以了機械變身的“咔嚓咔嚓”聲,這似乎是對機械化時代下人的異化的隱喻。然后妮娜在本我極度壓抑之后的極度爆發中主動強吻了原本心中敬畏的托馬斯,這似乎又是一種貌似女性解放而實質只是男女兩性位置倒錯但內在“統治邏輯”不變的極端女性主義表現。接下來“黑天鵝”更加絢麗的表現贏得臺下雷鳴般的掌聲,鏡頭又配以絢麗的燈光,結合整部電影中托馬斯臺詞中的類似“這正是觀眾們需要看到的”以及最后的“我的小公主”等話語,加之妮娜最后那句復雜的“太完美了……我感同身受”,影片如此諸般的展示隱隱表現出對這種仍然被潛在規訓的女性自我的批判,而最后跳下高臺的天鵝重新變為了“白天鵝”似乎又是對此的中和。影片末尾如此密集的黑白交錯,既凸顯了二者各自的美,又展現了二者的激烈沖突,卻又沒有對二者進行簡單褒貶,這正是生態女性主義內在所希求的多元化、有差別但沒有等級的壓迫內蘊著主體間性哲學的主體建構思想。這種隱喻在篇末的字幕背景顏色變化中同樣表現出來了:在觀眾嘈雜的贊美聲逐漸遠去之后,片尾曲冉冉升起,以白色絨毛為背景飄下一枚孤寂的黑天鵝的羽毛,繼而黑色漸濃,黑羽毛漸多,當黑色變為背景之后從角落卻又飄起一枚同樣孤寂但又倔強的白羽毛。這種黑白彼此對立逐漸變為黑白相互生發類似于中國古代陰陽轉化的思維,正是生態主義中的生生不息的重要思想。影片中還潛含著一種促進黑白相互轉化的重要顏色——紅色——妮娜的血,這也正是對當下整個時代面臨生態危機的一個隱喻,在生態時代尚未完全到來之時,影片即使用藝術方式表現黑白殘缺之美,這種美之下依然帶有血色。
總之,《黑天鵝》這部電影內在蘊含的哲學思想擺脫了傳統一元單向度思維和簡單二元對立非此即彼思維而表現出一種趨向尊重間性主體而進行多元建構的生態主義思想,只是在生態時代尚未到來之時,影片以相當隱晦委婉的黑白交錯之美的形式將這種吁求呼喊出來。
注釋:
[1]黃志梅:《解讀<黑天鵝>中妮娜的三重人格》,電影文學,2013年,第6期。汪秋萍:《<黑天鵝>:關于個人釋放心魅與本欲的“內斗”》,美與時代(下),2011年,第12期。
[2]郝心心,梁娟:《解讀影片<黑天鵝>主人公的雙重人格》,文學教育(中),2012年,第11期。
[3]夏惠文:《<黑天鵝>:自戀與完美的達成》,戲劇之家(上半月),2011年,第9期。
[4]張夢娜:《從女性主義角度分析電影<黑天鵝>》,群文天地,2012年,第6期。
[5]溫慶航:《從電影符號學視域解讀<黑天鵝>》,青年記者,2011年,第32期。
[6]楊濟如:《淺談獲獎電影<黑天鵝>的精神藝術》,電影評介,2011年,第21期。
[7]郝新莉:《電影<黑天鵝>的精神分析美學解讀》,美與時代(下),2011年,第11期。
[8]陳曉穎:《看女性難以逃脫的“他者”“被看”地位》,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
[9]文一茗:《身份與符號自我:<黑天鵝>關于身份的命題》,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0期。
[10]曾繁仁:《生態女性主義與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藝術百家,2009年,第5期。
[11]曹南燕,劉兵:《生態女性主義及其意義》,哲學研究,1996年,第5期。(注:后文凡提到“統治邏輯”均參此出處,不另作標注。)
[12]袁鼎生:《超循環:生態方法論》,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464頁。
(向一優,田密 廣西民族大學文學院 53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