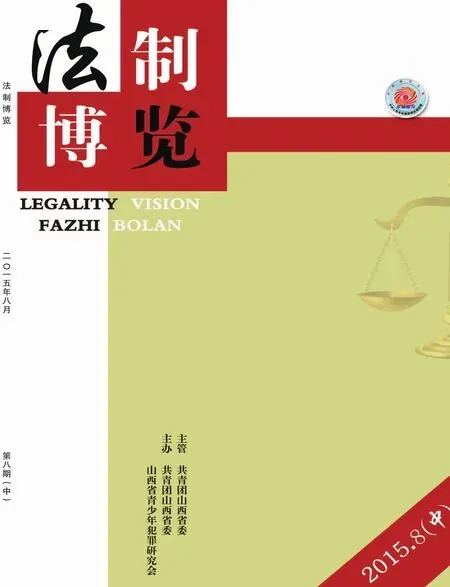胎兒利益的民法保護問題之研究
張凱璇
1.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 100102;2.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總隊,北京100007
胎兒階段是人類生命形態存在的一個基本性的必經階段,就法學的考量意義上講,胎兒的概念與自然人的概念有著不可分割的必然性聯系。在現有的世界法學事業的客觀性開展路徑中,各國現有的有效性的法律文本往往都對胎兒利益的保護工作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法條性約束規定,但是,基于法理以及實踐性考量角度,世界各個獨立性的主權國家往往都在胎兒利益的民法保護工作的過程中展示出了較為鮮明的客觀性的差異特征。
法學意義上的胎兒概念,指涉的往往都是從受孕到出生這一時間區間內人類生命所經歷的客觀過程,相對應地,我們將處于哺乳期的生命形態描述成嬰兒。伴隨著當代科學技術的不間斷的深化發展以及社會形態的不斷變革,出生前的胎兒在其母體子宮內遭遇不法侵害的可能性也相應地表現出了不斷增加的客觀態勢。由于我國現行條件下的民法文本將自然人公民的民法權益的獲取時間現實性地給定為其出生時點,間接性地導致胎兒被規定成了潛在性的生命存在形態,進而導致胎兒生命形態的民法權益可能遭受來自與法律制度實踐背景的現實性限制,而且,對現有的我國民法體系文本實施具體性的考量,我們可以比較真切地客觀感知到現行法律文本在保護胎兒合法性實踐權益的客觀視角之上所客觀表現出的缺位性實踐工作特征。筆者深切地以為,我國現行的民法體系中關于胎兒基本性法學權益以及利益性內容的保護性條款亟待完善和增補,接下來,筆者將會圍繞胎兒利益的民法保護及其相關問題展開簡要性的論述過程,僅供參考。
一、我國現有的民法體系中的胎兒權益保護問題的立法工作開展狀況
基于嚴格性的民法制度的開展視角,我們可以比較充分地認為,在現有的發展條件下,我國針對胎兒生命對象的立法實踐工作尚且階段性地處于初始性的發展階段,相關工作在開展路徑中具有著大量的工作空白狀況,提升空間極其明顯且充分,而想要對胎兒生命形態的民法意義保護工作展開系統而又深入的客觀討論,我們必須相應性地開展胎兒生命對象的學理性屬性確定實踐工作的客觀過程,成年人類個體所具有的生殖細胞,在我國民法視野中被劃分為特殊物,其所有權歸屬與其實際制造者。在生物學的研究意義視角下,胎兒被定義為一定的生命發育階段的現實性產物,一般為受孕之后的8周。在母體懷孕的生理性流程中,胎兒被界定為母體生命的組成部分,其實際的生命存在于延續表現出了對母體生命極其強烈而且是充分的依賴性特征,在這一工作視角下,胎兒往往不能脫離母體的生命環境而單獨地存在。在這個視角下,胎兒的界定工作本質上被界定為一種時間性的問題。
在法學意義的研究視角下,我們應當對胎兒的定性進行更加充分的探討,這樣的實踐行為過程將會現實性具有更加重要的現實意義,在法學意義上,我們不能將醫學意義上的胎兒定義的界定簡單地予以機械化的借用,而是應當扎扎實實地結合我國當代法學研究事業的具象化開展情況,制定出具有充分的實踐意義的法學視角下的胎兒定義。但是,在實踐意義的開展視角下,我國法學界在實施胎兒定義的界定過程中,表現出了比較明顯的各家爭鳴性的實踐特征,因為在現行的中國法律體系中尚且還不承認胎兒生命形態的主體地位,胎兒階段的侵害性實踐行為缺乏條文約制。
二、關于胎兒民法權益保護的改良建議
(一)賦予胎兒生命形態以民事權利能力
賦予胎兒生命形態以民事權利能力是完成胎兒生命形態的確立行為的重要基礎。我國現行的民事法律制度在實施胎兒權利的保護工作過程中選取的是“絕對主義”的思想取向。出了在繼承權的法條表述中給予了一定程度的法條保護之外,幾乎將胎兒的民事權利主體地位予以幾乎完全性的否定,也就是說,我國現有條件下的胎兒群體的民事權利遭遇了較大程度的漠視。所以在這樣的背景條件下,我們應當相對充分地日漸性地加強對胎兒群體的民事性權益給予比較充分的客觀關注,要在今后一段時間的民事法律制度的建制與改良工作的過程中逐步引入對胎兒的生命健康權以及其他權益的現實關照。
(二)扎實明確胎兒基本權益的保護工作范圍
盡管我國現行的民事法律制度中尚且還不存在對胎兒民事權利的保護性法條,但是,我們依然有必要對胎兒生命形態應當具備的民事權力實施一個簡要性的界定。下面我們結合對日本以及德國等國家已經成型的法律文本實施一定程度的參照,對相關的內容展開簡要的論述。
1.胎兒的健康權
伴隨著當代中國社會建設事業的不斷發展,威脅胎兒個體的健康狀況的客觀因素越來越向著復雜多樣的客觀方向現實地發展著,環境污染、劣質食品藥品、醫療事故等因素都現實性地表現出了逐漸增多的客觀性趨勢,不難理解,健康權將成為胎兒權益中的一個重要的組成成分,胎兒是否能夠正常而且健康穩定地在母體環境中完成發育過程,對其出生之后的自然人成長過程具有著重要的前在性制約作用,所以,在一定的實踐意義上,賦予胎兒個體相對充分的健康權是一項基本性的權利保障行為。
2.胎兒的受撫養權
“受撫養權”,就法學的實踐意義開展路徑而言,指涉的是胎兒出生后應當扎實而真切地享有的接受其監護人良好的撫養的現實權利,是我國現有的民事法律制度扎實賦予我國所有的未成年人的最最基本的民事行為權利。而在這個學理性背景之下,胎兒這種生命形態作為人類生長發育過程中的一個必經性的客觀階段,自然性地也應當獲取受撫養權的客觀權利;在胎兒尚未出生的時候,如果撫養義務人因他人的侵權行為而導致了勞動能力的喪失結果,侵權人必須相應地支付必要的法律代價。
3.胎兒的受遺贈權以及受贈與權
“受遺贈權以及受贈與權”,在這里現實指涉的是獨立的行為人主體所現實具備的接受被遺贈人遺贈或者是被贈與人贈與一定形式的財產或者其他資源的現實性實踐權利。對于這種權利性實踐對象類型,全世界范圍內的最早的立法性表述文本緣起于法國。法國民法典在法條的表述工作的開展過程中規定:“僅需在贈與行為人在生前實施贈與實踐行為的客觀時點已經完成受孕過程的胎兒,也就是有實際能力接受生前贈與行為的生命性實體,在遺囑創立人死亡事件行為發生時已經完成受孕行為的胎兒切實而且充分地具有依照遺囑表述來實施遺產接受行為的能力以及權力。但是這種法條規定僅在嬰兒出生時是生存者,贈與或者是遺囑文本才會現實性地產生相應程度的法律效力。”
在這個工作開展領域中,我國法律則客觀性地表現出了比較明顯的缺位性特征,我國現行的民事法律制度在法條表述的實踐過程中對受遺贈權利客觀性地實施了比較充分的表述;但是當受遺贈人是胎兒生命形態時,相關的法條表述則展現出了比較明顯的缺位性特征,在我國的法律制度之下,胎兒生命形態如何接受遺贈、而又該如何保護其應得的權益呢?在我國的法律工作的實踐性開展場域中,如果我國現有的法律文本并不加以相應的規定,胎兒的法定代理人將無法獲得代為行使受遺贈權的客觀性實踐工作權力,所以我們應當扎實地為胎兒群體的民事權益獲取行為建制相對成型的客觀性實踐制度。
三、結語
本文圍繞胎兒利益的民法保護工作的實踐性意義的相關問題展開了簡要的研究以及實踐性討論工作過程,僅供有關領域的讀者朋友實踐參考。
[1]祁秀霞.論胎兒利益的民法保護[D].鄭州大學,2004-05-01.
[2]成繼平.論胎兒利益的民法保護[D].華中師范大學,2008-04-01.
[3]高琳.胎兒利益的民法保護[D].山西大學,2005-06-01.
[4]曾廣賢.胎兒利益民法保護研究[D].上海社會科學院,2013-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