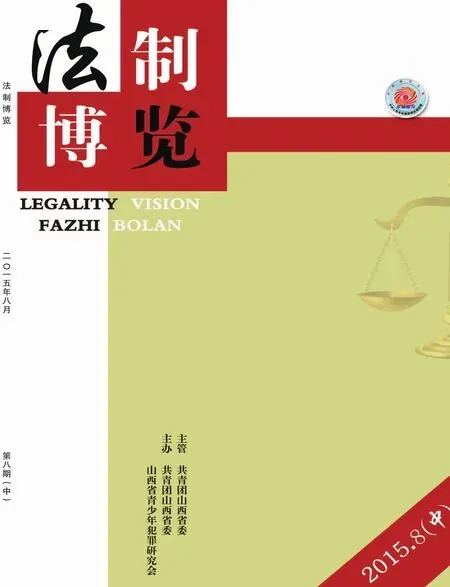“禮治”思想下的中國鄉(xiāng)土刑事司法問題
徐崢瓊 孫 杰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湖北 武漢 430000
費孝通先生在《鄉(xiāng)土中國》的“無訟”一章中曾經提出了這樣的一個案例:有個人因妻子偷了漢子打傷了奸夫,和奸無罪,毆傷有罪。司法者陷入一個困境:善良的鄉(xiāng)下人做了壞事絕對不會到衙門里來的。反而憑借一點法律知識點敗類,卻會在鄉(xiāng)間為非作惡起來,法律還要去保護他。費孝通先生針對該案例指出:先行的司法制度在鄉(xiāng)間發(fā)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壞了原有的禮制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因此費先生認為:在社會結構和思想觀念上還得有一番改革,單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鄉(xiāng),結果法治秩序的好處未得,而破壞禮治秩序的弊病卻已先發(fā)生了。[1]上面例子是發(fā)生在民國時期的中國,對于現(xiàn)在的中國是否還是一個問題呢?梁治平先生指出“法律必須被信仰”,而建國以來的制度改革和法制教育,是否起到了費孝通先生所說的“社會結構和思想觀念上的改革”呢?我想這還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
一、問題的提出
目前我國民事案件,民事案件的調撤率居高不下,這當然存在很大的問題。但至少從一個角度來說,對于民事案件我國司法實踐并不是嚴格遵照法律主義來實行的。而禮制與法制更大的沖突,依然存在與刑事案件之中。就像“秋菊打官司”中提出的那個問題,秋菊的“說法”到底是怎么樣的訴求,法院將村長判刑,就是秋菊所討的一個說法么?在不涉及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的私權侵害的刑事案件中,這些案件的處理是否是禮制與法治的沖突呢?如果存在這種沖突,我們應當在何種范圍去處理這種問題?而面對這樣的沖突,我們應當堅持一種怎樣的方式去處理這些問題呢?我們下面主要從這幾個方面來闡述這個問題。
二、“禮治”與“法治”
“禮治”與“法治”從中國先秦時期就開始成為百家爭論的主要問題,其中以“法家”與“儒家”兩派的觀點最具有代表性。而改革開放后的農村城鎮(zhèn)化時期,“禮治”與“法治”的沖突又呈現(xiàn)了嶄新的特點。而我們很清晰的認識到,我國傳統(tǒng)的法治思想與現(xiàn)代法治思想在內核上存在根本性的差異,現(xiàn)實層面也存在的一定的沖突。
(一)中國傳統(tǒng)“禮治”與“法治”的沖突與統(tǒng)一
我國傳統(tǒng)思想關于兩者的沖突,主要集中在“人性”的問題之上。如有的學者就指出:中國古代的儒、法兩家將人性問題簡單化,各自強調其中的一個方面,并以此作為制定政策的依據,于是就產生了禮治與法治的沖突。[2]在此我們不對其理論內涵進行詳盡的闡述,但古代法治認為人的本性為“惡”,認為人“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也就是說人性本惡,追逐利益,法應當對不正當的利益進行規(guī)制。在古代法治僅僅是一種統(tǒng)治手段,而并不是作為一種根本原則存在的,可以說中國古代的法為“術”非“道”。這是與現(xiàn)代法治一個重要的區(qū)別之一。
隨著兩者學說的發(fā)展,由漢朝學者董仲舒將其兩者進行了一次統(tǒng)一,他指出“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總結出來就是“禮主刑輔”,這也成為了我國古代關于“禮法”關系的基本思想。
(二)“禮主刑輔”思想在傳統(tǒng)鄉(xiāng)土中國的體現(xiàn)
禮主刑輔思想在傳統(tǒng)鄉(xiāng)土中國,就集中體現(xiàn)在“無訟”思想上。對于“無訟”我贊同梁治平老師的觀點,及“天道本和諧,因此人道亦平和。倘有人涉身于沖突,那必是偏離了人道,偏離了人道之所本的天道。政府乃至整個社會的責任,就是通過教化,通過勸說,也通過儆戒,使他們返‘人道之正’,以便維持好社會的和諧。……在社會關系領域,中國古代的和諧觀念演化為一個具體原則,那就是無訟”[3]
從中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禮就是順應天道,而禮治就是企圖通過對于人“禮”的教化以及維護,以使其返回正道,維持社會和諧,而“訟”其實就是社會矛盾無法通過“禮”調節(jié)的體現(xiàn),因此古代先賢都推崇圣人的“無訟”思想。具體到鄉(xiāng)土社會,就形成了“家長、組長、鄉(xiāng)紳、里正”等人的一整系列的調解或禮法制度。但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無訟”應是“禮治”的最高形態(tài),或者說是其理想形態(tài),而現(xiàn)實中這種情況很難達到,因此就需要“刑”輔助。以此,構成了我國傳統(tǒng)鄉(xiāng)土社會的基本訴訟制度。在刑事案件領域,“禮主刑輔”的理念也是一以貫之的,下面我就從刑事案件領域對“禮治”思想與現(xiàn)代“法治”思想的沖突進行探究。
三、新鄉(xiāng)土社會刑事司法中禮治和法治的沖突
我們通過上面的探究,我們發(fā)現(xiàn)了“禮治”的基本特點,而在傳統(tǒng)鄉(xiāng)土社會的刑事訴訟中,對于侵犯私權的較輕刑事案件,多為采取“家長、組長、鄉(xiāng)紳、里正”自行解決的局面,僅對于嚴重的刑事案件,或侵犯公權的刑事案件才上升到公權力機關進行審判。本文接下來通過對費孝通書中案例的推演,分析在新舊鄉(xiāng)土社會中刑事司法實踐中所突出“禮治”與“法治”的矛盾。
(一)傳統(tǒng)鄉(xiāng)土社會的處理模式
在傳統(tǒng)的鄉(xiāng)土社會,對于該案件處理基本上就是教育兼處罰的模式。如《鄉(xiāng)土中國》中指出的那種“調解”的方式,當事被稱為“評理”。基本的模式是,由鄉(xiāng)里面幾位具有威望的鄉(xiāng)紳或者長老,其中一名鄉(xiāng)紳先行對雙方進行說教,將雙方都罵一頓,說明這件事情是一件很丟人的事情,然后教育雙方,雙方各自道歉。然后由鄉(xiāng)中最有威望的長老宣布處罰決定,一般打人者和被打者各自認錯,打人者付出些財物治病了事。這樣的處理,一般情況下就起到了緩和矛盾的作用,一方面對打人者是一個懲戒,同時對于和奸者也是一個教訓。在多人聚集的“評理”會議上,礙于面子或是真心悔過,都會表現(xiàn)出一副和解的樣子,這就是傳統(tǒng)鄉(xiāng)土社會的輕微刑事案件一個處理模式。
(二)新鄉(xiāng)土社會的處理模式
如果在新鄉(xiāng)土社會,那么這件案子可能就會轉化為普通的刑事案件,由公安機關進行處理,或者轉化為自訴案件,由法院進行審理。在這種情況下,“打人”這個情節(jié)就是案件的主體,而“和奸”便基本不會作為案件的主要問題來處理,由此得出的判決往往就是對“打人者”判刑而對“和奸者”并沒有任何的處罰,這樣的判決幾乎肯定會對當地的社會風氣產生不良的影響。
當然,實踐中這種案子多由公安機關或法院主持下調解結案。在公權力機關主持下的“和解”看似取代了以前鄉(xiāng)紳的和解,但是通過進一步的考量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在很大程度上,公權力機關并不能很好的替代鄉(xiāng)紳的作用。因為警察或法官并不當然擁有鄉(xiāng)紳的“權威”,我們也不可能要求我們所有的公務人員都能在鄉(xiāng)土社會中處于“有威信”的地位,而我們在傳統(tǒng)的鄉(xiāng)土社會中我們發(fā)現(xiàn)當時的行政管理機關代表“保長”或“里正”基本不發(fā)言,發(fā)言的主要是鄉(xiāng)里有威信的老人或有文化的“鄉(xiāng)紳”。因此,在這種環(huán)境下,公權力機關主導的“和解”所能起到的化解糾紛的作用將要打一個很大的折扣。
四、結論的總結與再分析
(一)一個基本的結論——沖突是存在的
通過上面一系列的分析,我們發(fā)現(xiàn)在新鄉(xiāng)土社會,“禮治”與“法治”之間的沖突是存在的。目前法治的一些手段,如“刑事和解”制度,在本質上不能夠替代之前傳統(tǒng)鄉(xiāng)土刑事司法實踐的一些做法。現(xiàn)代的法治以“規(guī)范”與“法律主義”為基本原則,與我國傳統(tǒng)“禮治”中的“禮主刑法”理念有著本質的區(qū)別。同時現(xiàn)代社會的健訴傾向,于我國傳統(tǒng)社會的“無訟”操作有著沖突。雖然我國傳統(tǒng)農村經濟已經瓦解,但從文化論角度來說,一個民族文化習慣的變化總有一定的滯后性,“市場經濟”在新鄉(xiāng)土社會中的影響并不像我們想象中的那么根本。就像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指出的那樣,“在原有的封建制度崩潰之時,因并未帶來革命預期的結果,而致使執(zhí)政者與民眾間的矛盾公開化,社會動蕩愈演愈烈”[4]新鄉(xiāng)土中國刑事司法制度中的這一層面問題,也是這種矛盾激烈化的一種體現(xiàn)。
(二)結論的再思考——沖突的范圍
本文所考察的沖突更多的體現(xiàn)在侵犯私權的輕微刑事案件上,在傳統(tǒng)鄉(xiāng)土社會中,“和解”或官府主持的“調解”也僅僅局限在輕微刑事案件上。[5]那么對于侵犯公權力的案件,如“十惡”中的“謀反”“謀大逆”“謀叛”等嚴重侵犯公權力的罪名,并且對于嚴重侵犯個人人事財產安全的罪名,如故意殺人、搶劫、綁架等罪,并不是傳統(tǒng)鄉(xiāng)土社會能夠解決的刑事案件的范圍。但不可否認的是,傳統(tǒng)的“禮法”對于上述重罪的處理也有著本質上的影響,但是本文不作為主要研究方向。
(三)結論的再思考——沖突的化解
對于這種沖突的化解方式,費孝通先生期望在社會結構和思想觀念上進行一番改革,以使得其與法治秩序相配套,這樣才能保證法治與禮治秩序的對接。其中最大的問題在于思想觀念的改革。尤其是對于農村“普法”的問題,農村普法僅僅是對法條的普及,而對法治精神的本質的普及工作,效果甚微。如果說解放前的民國時期的農民法治意識淡薄是由于政府沒有進行充分的普法工作的話,在建國后經過多年普法的中國農村是否就具有了較強的法制意識呢?我想這個結論肯定是否定的。那么既然如此,只有兩個理由,一是普法的手段不對,之前幾十年的普法的手段是錯誤的。二是我國農村有一種傳統(tǒng)的力量抵消了法治宣傳的效果。我更傾向于后一個理由,而這個與我國法治宣傳想抵消的東西,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禮治”的思想,以及它所派生出來的各種各樣的傳統(tǒng)觀念。
如此看來,費氏的進路似乎很難得到一個質的飛躍。那么對與現(xiàn)在來說,在新鄉(xiāng)土社會中,就不能過于一廂情愿的貫徹所謂的法治精神了,在社會主義法治的大框架下,如何更多的結合傳統(tǒng)的一些做法,保證傳統(tǒng)禮治不至于猛然崩塌,就成了我們現(xiàn)在必須深入考慮的一個問題。對于刑法的思考不再是一種單純思辨或者一種德日刑法理論的引入,更多的是一種實踐操作的思考,這樣的做法對于我國社會所基本秉持的“正義”是否相符,而這種正義的來源,如果逃脫我國幾千年的歷史傳統(tǒng)來談也是不作數的。
[1]費孝通.鄉(xiāng)土中國[M].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54-55.
[2]史建群,葉桐.中國古代禮治與法治的沖突與互補[J].鄭州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997(11).
[3]梁治平.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中國傳統(tǒng)法律文化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20.
[4]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5]胡旭最,夏新華.中國傳統(tǒng)調解研究——一種傳統(tǒng)文化的透視[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報,2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