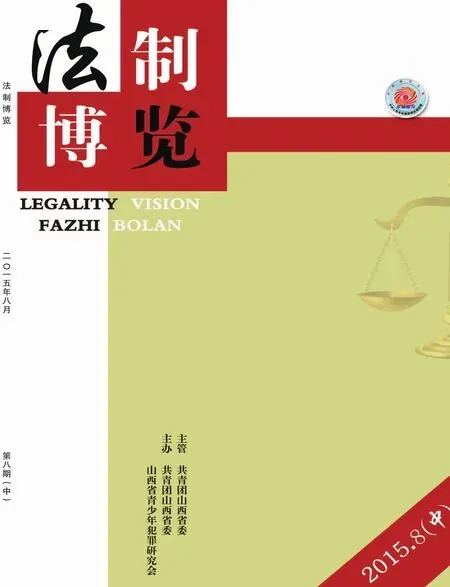美國辯訴交易制度研究
趙廷凱
貴州大學法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一、美國辯訴交易制度概述
(一)美國辯訴交易制度的概念與特征
1.概念
辯訴交易制度(plea bargain),也可翻譯為認罪辯訴協議,是指在美國刑事訴訟中作為控方的檢察官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圍繞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所犯罪行通過談判、協商檢察官欲提起的指控而達成的一紙自由合同。
2.特征
(1)協商性。辯訴交易制度中認罪辯訴協議的達成是擁有檢察權的檢察官與刑事訴訟中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通常是被告人的辯護人作代表)通過自由協商、討價還價后一種“妥協”的產物或者說是一種“軟博弈”的產品。
(2)契約性。Plea bargain 中的bargain 翻譯成中文就是“交易”、“契約”的意思。從這個詞中我們可以看出辯訴交易制度的核心在于契約,換句話而言就是,辯訴交易制度是指作為控方的檢察官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罪名或量刑建議上形成了一種雙方當事人都自愿認可的合同。達成了此合同后,檢察官必須履行其在此合同締結時所答應的事項,也就是減少指控或降低指控;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也應完成自己應盡的義務,即是認罪。此時,公法案件司法化。
(3)平等性。在刑事訴訟辯訴交易中,檢察官與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雙方當事人,二者在此時是基于契約平等的理念自由、無脅迫的進行談判、協商,而非隸屬關系。
(二)美國辯訴交易制度的內容
1.辯訴交易制度的主體
美國的辯訴交易制度中辯訴交易的主體,筆者從plea bargain 的英文詞源及概念出發認為是只包含兩造,即控方與辯方。作為中立裁判者的法院不涉其中,法院只需按照辯方與檢察官的合同經過簡單審議后作出判決即可。
2.辯訴交易制度的種類
一般意義上來說,辯訴交易制度中辯訴交易的種類有兩種:一是定罪交易,在定罪交易中檢察官在獲得對方的有罪答辯承諾后應當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減少指控或降低指控;二是量刑交易,在量刑交易中檢察官與對方達成協議,在指控中對被告人在定罪上不作處理,但是在此犯罪中的量刑上以認罪態度好等名義采取從輕或減輕的措施。
(三)美國辯訴交易制度中控辯審三方的地位
1.公訴方
作為公訴方的檢察官在辯訴交易中由于“手握重權”而處于重要地位,之所以是說其處于重要地位是因為很多時候美國的檢察官在主導著刑事案件的走向、定性,且是辯訴交易不可或缺的一方。
2.辯方
辯方(包括被告人)是刑事訴訟辯訴交易中必須存在的另一造,在辯護方中,一般情況下是辯護律師代表被告人與公訴方進行協商、交易,促成辯訴協議的達成,辯訴交易制度是否得以實現某種程度上取決于此方。
3.法院
法院在辯訴交易程序的適用過程中更多的扮演的是一種守門人的角色,起次要作用,主要是監督審核達成的辯訴協議是否自愿,辯訴協議是否違法,它不會主動去介入辯訴協議的博弈之中,其消極、中立的性質在此得到彰顯。
(四)美國辯訴交易制度的歷史沿革
1.產生與發展
辯訴交易制度起源于美國,有文章或書中指出辯訴交易制度起源于英國,發展于美國的說法無依據,屬錯誤。嚴格來說辯訴交易制度分為隱性的辯訴交易制度與顯性的辯訴交易制度。法律史學家Lawrence M.Friedman 指出,美國本義上的辯訴交易制度(即顯性的辯訴交易制度)在19世紀就已經存在了,由此可見,隱性的辯訴交易制度(默示的辯訴交易制度)存在的歷史應該更長,因為許多事物的發展往往是從隱性到顯性。可能大家對顯性與隱性的辯訴交易制度的稱呼感覺較難以理解,筆者在此對這兩種稱呼換種說法,即是直接接觸性的辯訴交易制度與默示性的辯訴交易制度。在19世紀,享有刑事控告權的美國的檢察官就已經嘗試在與被告人協商,希望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辯,以換取某種形式上的利益。后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的劇烈變動,刑事案件越來越多,辯訴交易程序在美國各州逐漸普及,不過正式得到合法性地位卻是在1980 的聯邦最高法裁決Brady v.U.S 一案中。其后,此程序被快速運用于各種刑事案件中。
2.現狀
目前,辯訴交易制度已被眾多美國普通民眾所接受,它已經成為美國刑事訴訟制度中一個不能缺失的部分。由于簡化了訴訟程序,提高了訴訟效率,降低了訴訟成本,在美國的刑事訴訟中百分之九十的案子是通過辯訴交易制度解決的,從中看其重要性可見一斑。
3.未來
盡管辯訴交易制度從其誕生之初就一直伴隨著爭議,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它的生命力變得越發強大,由此可以推測,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其仍會保持較強的生命力。當然,這不排除此程序未來會面臨“小修小補”,比如在案件適用范圍、使用方式等方面進行調整。
二、美國辯訴交易制度的生存基礎
(一)思想基礎
美國是一個只有二百多年歷史的國家,這個年輕國家的人民來自世界各地,他們以前有著不同的歷史、文化、價值觀...正是在各種因素匯聚于此的情況下,美國缺少一種統一傳統的羈絆,形成了一種只要能快速解決問題就是好辦法的思維方式,由此實用主義的哲學觀走上美國法制的舞臺。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杜威曾這樣精辟的概括:思想、概念和理念只不過是人為了達到某種目的的工具,只要它們對集體適應環境有用,它們就是真理。美國辯訴交易制度得以生存的思想基礎源于此。
(二)文化基礎
自由契約理念在美國民眾的心里可謂由來已久、根深蒂固。按照合同辦事是他們通常的做法,私法領域中合同無處不在。辯訴交易是公法中的概念,但這個概念卻是私法領域中的合同“入侵”公法領域的一個表現,使得一定程度上公法私法化。之所以得以從私法“入侵公法成功”,在于美國民眾思維中梅因的“從身份到契約”民約思想的牢固。
(三)經濟基礎
辯訴交易制度之所以得以出現,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伴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中的矛盾愈發突出,刑事犯罪案件保持高發態勢。但是一個國家的司法資源有限,對抗式的訴訟構造也往往使得訴訟效率不高,在此基礎上,司法領域急需設置一種程序來節省司法資源,提高訴訟效率。辯訴交易正是在此背景下從幕后走到了前臺。
(四)共生基礎
1.證據開示
美國第一個關于證據開示的案例出現在1935年,這就是有名的Mooney v.Holohan.案件,此案標志著證據開示制度成為美國法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所謂證據開示,也就是證據展示,掌握證據的辯方和控方彼此向對方展示己有證據。在此情況下,控方怕承擔敗訴風險,被告人則通過了解控方的證據盤算勝算的幾率。雙方的心理態度在證據開示后走向辯訴交易就成了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2.米蘭達規則——沉默權
美國在1966年通過了“米蘭達規則”,在此規則中,其最主要內容就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享有的沉默權。當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享有沉默權并在案件中行使沉默權,這無疑是訴訟中的一件較為棘手的問題,如果沒有其他措施來對此進行適當制約,這將會大大降低訴訟案件的進程,提高訴訟成本。在此情況下,幾年后辯訴交易制度應運而生。在辯訴交易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放棄沉默權以此換取控方的從輕指控。
(五)制度基礎
當事人主義的訴訟模式為辯訴交易制度的誕生提供了制度保障。在當事人主義的訴訟模式下,被告人與控方作為訴訟中的兩造,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被告人可以通過公開審判在整個訴訟過程中充分的享有訴訟權利,被告人享有并行使權利越充分,在一定程度上訴訟效率會越低,訴訟效率越低會導致結案率越低,由此惡性循環,形成冗案。遲來的正義非正義,在此亟需解決之道,辯訴交易制度作為一種解決方案納入其中。
三、美國辯訴交易制度的爭論
(一)侵犯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
對于有學者指出辯訴交易侵犯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侵犯沉默權,辯訴交易制度使得米蘭達規則的用武之地被極大限制,沉默權一定程度上變成擺設,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為人是理性的,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絕大多數理性人在通常情況下的選擇,當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在權衡利弊得失之后,往往會被迫選擇放棄,雖然這種放棄是他們自己選擇的,并且這種選擇是在外人看來是自愿的;二是侵犯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通過正常訴訟程序進行審判,因為在美國刑事訴訟法中規定了如果控辯雙方選擇了辯訴交易,被告人便不能獲得陪審團的審判,直接由法院按照控辯雙方達成的協議,經過簡單了解后直接作出裁判。
(二)容易導致檢察權濫用
在辯訴交易程序中,檢察官享有極大的權力,這種權力表現在減少或降低指控、量刑裁決中。可能會有人疑惑,量刑裁量是法院的事情,檢察官只能提建議,如果有檢察官掌握量刑裁量,豈不導致司法不獨立,確切的來說,這里的量刑裁決是建議,不過此時的建議是強制性的,如果法院在審查后是合法的,法院就必須按照檢方的建議來判決。
(三)有違社會正義理念
不少人認為辯訴交易是對社會正義理念的褻瀆,扭曲了社會正義體系,因為從社會正義的角度來看問題時,當一個人犯了罪,他就必須按照他所犯的罪接受懲罰,法檢也必須按照法律規定懲處此犯罪人,妥協的罪行是一種非正義。
(四)有違程序正義理念
法律程序設置的初衷,是為了更好地實現正義,當一個法律程序是“壞的”,在運行中,這個程序就會出現負面效果,有損法律的尊嚴。辯訴交易程序被一些學者劃到這種壞的程序當中去,認為刑事訴訟法中的辯訴交易制度這種程序是為“惡法”,須廢止。
四、辯訴交易制度的意義
(一)提高刑事訴訟效率
通過在刑事犯罪案件中實行辯訴交易制度,大量案件在短時間內得以解決,時間的縮短,使得訴訟成本得到控制,訴訟效率得以提高,使得司法機關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裁決更多的案件。
(二)控方減少敗訴風險
檢察機關通過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達成辯訴協議,在辯訴協議下,被告人作有罪答辯,在此情況下,檢察機關的證據無需絕對充分,還可以一定程度上防止被告人翻供,以此,控方承擔敗訴風險最小化。
(三)減少刑訊逼供
在辯訴交易制度下,控方與辯方是平等自愿協商的來達成辯訴協議的,達成辯訴協議,對雙方來講是一種共贏,檢察機關在不違法犯罪的情況下或者說是在沒有違法犯罪成本的情況下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在此情境下,理性的檢察機關就不會再不擇手段的去逼供被告人。
(四)更利于保護被害人的權益
“遲來的正義非正義”,一件案件久拖不決是對被害人的二次傷害,長時間的訴訟會使被害人承受巨大的精神壓力,通過控辯的交易,案件可以更加快的得到解決,使得正義來的更快些,這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利于保護被害人的權益。
五、美國辯訴交易制度對我國刑事訴訟法的啟示
(一)辯訴交易制度在我國是否有生存土壤
從目前來看,我國現行法律體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但在許多規范上、制度上更加傾向于大陸法系。在訴訟模式上,我國同樣采取同大陸法系許多國家一樣的職權主義訴訟模式,這與英美法系的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有著較大差異。而辯訴交易制度是深深植根于當事人主義的訴訟模式下的產物,從這似乎看出,辯訴交易制度在我國好像沒有適合其生存的土壤。但是事情并不必然,我們從接下來這一部分談一下構建辯訴交易制度的可能性。
(二)構建辯訴交易制度的可能性
1.訴訟模式的轉變
在上面的論述中,筆者提到,我國是職權主義訴訟模式。但是由于這些年法系的交融,不管在程序法,還是在實體法上,各國都存在一些借鑒與移植。我國是一個兼容并蓄的國家,在發展中國特色法律體系的過程中,吸收、借鑒了不少同時期國外的優秀規則,在訴訟模式上,我國職權主義的色彩已經不是太明顯。按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張衛平的觀點來說,我國目前實行的是“亞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這種模式是介于職權主義訴訟模式與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之間,但較傾向于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這邊。
2.刑事法律基礎
目前來說,按照我國《刑法》的相關規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自首、立功等情形的,可以分情況從輕、減輕或者免除對他們的刑事處罰,這里由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良好表現”,得到了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也屬于某種意義上的交易。不過這種交易在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未從事違法犯罪行為之前就已經存在,但從實質上來說與美國的辯訴交易制度有異曲同工之處。這些法律規定對我國構建辯訴交易制度提供了法律支持。
3.刑事政策基礎
在刑事法律政策上來說,我們歷來實行“抗拒從嚴,坦白從寬”的政策,從中可以看出,我國刑事政策上對案件的態度與美國的辯訴交易制度的初衷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這為我國構建辯訴交易制度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
(三)構建辯訴交易制度的必要性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取得了空前的大發展、國家法制也得以不斷健全,但目前的現狀是我國司法資源相對不足,難以支持全部的案件全部按照程序規則全部走完,引進辯訴交易制度,可以簡化訴訟程序,使一部分刑事案件得以分流,從而提高訴訟效率,緩解司法資源不足的現狀。
[1]陳瑞華.比較刑事訴訟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2]張夢夢.探尋辯訴交易生存的土壤[J].經法視點,2015(01).
[3]宋冰.程序、正義與現代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
[4]汪建成.辯訴交易的理論基礎[J].政法論壇,2002.
[5]陳瑞華.刑事訴訟的前沿問題(第四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