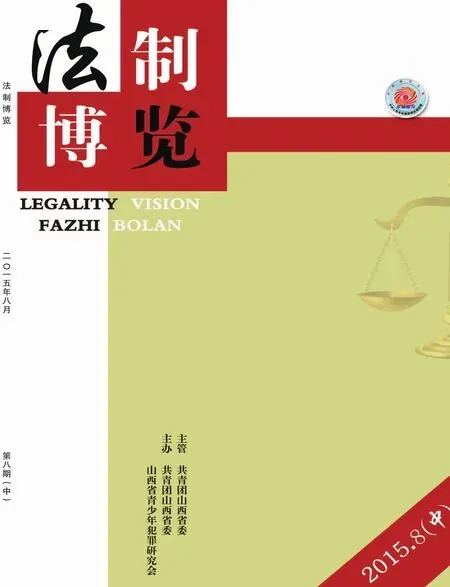淺議我國的限制減刑制度
閆春麗
信陽師范學院華銳學院,河南 信陽464000
一、限制減刑制度概述
(一)概念
所謂限制減刑是指對于主觀惡性極嚴重的特殊的犯罪分子,符合減刑條件時有所限制對其減刑的一種制度。隨著刑法修正案(八)的公布實施,限制減刑制度成為理論界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根據相關立法及司法解釋的規定,限制減刑是指因為下列情形被判處死緩的,人民法院在宣告刑罰的同時可以決定有所限制的對被告人減刑的制度。這些情形包括:累犯和因故意殺人、強奸、搶劫、綁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或者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而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犯罪分子。此類犯罪分子在死緩考驗期內如果沒有再故意犯罪的,依法減為無期徒刑的,后無論經過多少次減刑,實際執行刑期不得少于25年,另外加上2年的死緩考驗期,實際在監獄時間不得少于27年;被宣告限制減刑的死緩犯罪分子,在死緩考驗期內沒有再故意犯罪的,并且有重大立功表現,依法被減為25年有期徒刑的,后無論經過多少次減刑,有期徒刑實際執行刑期不得少于20年,加上2年死緩考驗期,實際在監獄時間不得少于22年。所以這三類人限制減刑的實際服刑期限分別為27年或者22年。在罪刑法定原則及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下設立限制減刑的目的是通過延長罪犯的改造期,降低其對社會的危害。
(二)限制減刑的作用
作為我國重要的刑罰執行制度,限制減刑制度在司法實踐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首先,減刑制度可避免刑期過剩,節約司法資源。現代刑罰建立在教育刑理論的基礎上,經過過在監獄中一定期限的服刑后,有的罪犯的社會危害性已經有所減退甚至喪失,此時如果繼續服刑,則刑罰失去了教育的價值,也是浪費國家的司法資源。其次,減刑具有調動和促進罪犯積極改造的作用。罪犯為了爭取能夠達到減刑條件而積極努力改造,所以減刑具有調動和促進罪犯積極改造的作用。最后,減刑對于穩定監管改造秩序起著促進作用。監獄的良好秩序不僅靠嚴密警戒和嚴格管理,更靠罪犯自覺服從管理。
(三)限制減刑的對象
《刑法修正案(八)》第五十條第二款規定了對死緩犯限制減刑的三種情形:(1)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累犯;(2)因實施故意殺人等七種具體犯罪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累犯;(3)因實施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被判處死緩的罪犯。根據我國刑法67的規定,被判處拘役或者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符合緩刑條件的可以宣告緩刑。我國刑法第74條又規定,累犯和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不適用緩刑。所以累犯、嚴重的暴力犯罪和犯罪集團首要分子如果被判處死緩的話就不適用緩刑。同時根據我國刑法第81條規定,累犯以及因暴力性犯罪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釋。綜上可知,此三類罪犯既不能假釋也不能緩刑,所以對該類罪犯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一項有力的改造措施就只有減刑。但是又由于法律的規定不甚明了,導致限制減刑在司法實踐中并沒有充分發揮其改造罪犯的作用。
二、限制減刑制度中存在的問題及完善
(一)減刑標準沒有與罪犯的人身危險性相聯系
從刑法50條可以看出,限制減刑是在以減刑為基礎,即在殺人、強奸等暴力犯罪的情形下可以在一定期限內嚴格適用第一款減刑的規定。減刑的標準就是罪犯在服刑期間有重大立功表現。但是重大立功表現并不能真實的反映出罪犯的人身危險性,刑罰執行的主要目的是通過改造罪犯降低甚至消除其人身危險性,使其不再危害社會。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就是人身危險性降低的主要標準,但是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與重大立功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司法實踐中也可能存在罪犯“不認真遵守監規、不接受教育改造”而有重大立功表現,這種情況下只要罪犯具備了重大立功的表現,司法機關就必須對其減刑。但是重大立功者不一定是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者。這樣,單純因為重大立功就對其進行減刑,而不考慮罪犯的人身危險性不符合刑罰的目的,不利于罪犯的改造。
筆者認為,減刑實際上是根據罪犯的人身危險性的變化而作的相適應的變化,因此,減刑的必要前提條件是人身危險的減少。具體實踐中應當綜合考慮罪犯的重大立功表現和人身危險性的減退來最終決定減刑的幅度,減刑制度的大前提是確有悔改表現,在此基礎上可以將減刑標準分為三個不同的等級:(1)確有悔改表現適用最低幅度減刑;(2)確有悔改表現并有立功表現適用中級幅度減刑;(3)確有悔改表現并有重大立功表現適用最高幅度減刑。這樣,針對不同種類的罪犯設置相應的減刑標準,能夠更好的實現刑罰特殊預防的目的。
(二)減刑制度沒有設立減刑考驗期和缺乏善后制度,應設立減刑考驗期和減刑撤銷制度
減刑制度作為一種懲罰和寬大相結合的刑事獎勵制度,罪犯的人身危險性減少或消除是減刑的前提條件。即罪犯只有在人身危險性變少或消除的時候才能減輕其刑罰。人身危險性并不是一瞬間就能表現出來,而是罪犯在長期的改造過程中表現出來的。不可否認,有些罪犯為獲得減刑的權利,而一時表現得非常好,一旦獲得了減刑就不再遵紀守法和認真改造。所以我們不能僅僅根據罪犯以前的一時或短期時期內的表現而減刑,也不能在罪犯獲得減刑后就不再理會,這樣罪犯很容易就會重走犯罪之路。
筆者認為,我國應設立減刑考驗期和減刑撤銷制度,即將罪犯原判刑罰未執行完的刑期設為減刑考驗期,繼續對罪犯進行觀察,以確定其人身危險性是否減小甚至消除了。在減刑考驗期內,罪犯表現好的話,減刑就有效;如果罪犯在減刑考驗期內,有違法亂紀的行為,甚至出現犯罪行為,說明該罪犯人身危險性并沒有消除,喪失了減刑的前提條件,則對其之前減刑的決定予以撤銷。
(三)檢察院監督作用沒有充分發揮,應完善檢察機關的監督權
按照我國憲法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檢察院對我國的刑事訴訟活動有法律監督的權力,刑罰執行屬于訴訟活動的最終環節,但是在減刑過程中,監獄和法院擁有最終的裁定權,檢察機關對監獄及法院的不當行為只有提出糾正意見的權力而沒有強制處分權。這樣的法律監督遠遠不夠制約法院的濫用權力行為。沒有強制力做后盾的法律監督形同虛設。
筆者認為,應當強化檢察院在減刑工作中的監督作用,法院在裁定對某個罪犯減刑之前先聽取駐檢監察室的意見,這樣,只有賦予檢察機關實質性的監察監督權利,使檢察機關在減刑全過程中發揮其起真正的監督作用,才能對法院的減刑裁定工作進行監督,防止法院濫用權力。另外,針對檢察院只有建議權的現實可以規定,對駐監獄檢察室提出的合理性意見監獄方面不配合時,檢察院可以強制監獄執行檢察室的決定。當然,監獄對檢察院的決定有申請復議復核的權力,只有賦予檢察機關一定的檢察監督處分權,才能最大限度的保證減刑監督的效果。
三、結語
限制減刑制度是教育刑的產物,根據受刑人在行刑期間人身危險性的消長情況,可以予以減刑,從而作為對受刑人的悔改表現的一種肯定與鼓勵,是尊重與保障人權的重要體現。然而,由于立法的滯后性,法律的漏洞是必然存在的,這就需要我們通過各種途徑來完善它,以使立法更好的為司法服務。
[1][美]羅斯科·龐德.法理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2]宋英輝.刑事訴訟法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3]趙秉志.刑法修正案(八)理解與適用[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
[4]陳敏.減刑制度比較研究[M].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1.
[5]高銘暄.刑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6]劉媛媛.減刑的限制問題研究[D].安徽大學,2012.
[7]陳菂.被害人諒解影響死刑適用研究[D].湖南師范大學,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