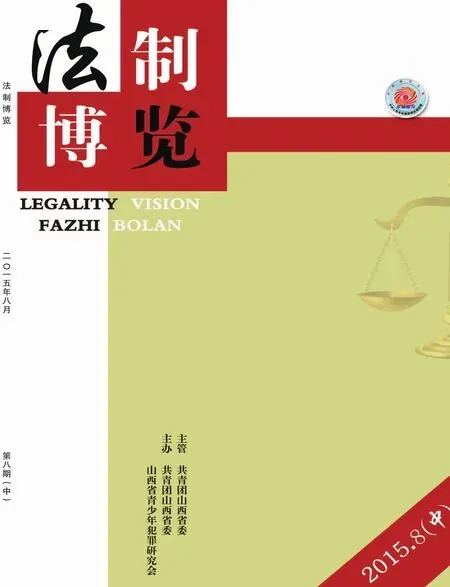禮與刑強制性的表現——以馮小青和王氏為視角分析
禮與刑強制性的表現——以馮小青和王氏為視角分析
商小偉
青島大學法學院,山東青島266100
摘要:刑罰使人畏懼,從而束縛人們的行為;而禮通過教化使人從內心感到認同,而自覺的遵從,表現為一種內在的強制性。本文以潘光旦先生的《馮小青——一件影戀之研究》和史景遷先生的《王氏之死》為基礎,以馮小青和王氏兩位婦人為例,簡要分析禮與刑強制性的表現。
關鍵詞:禮與刑;禮的內化;強制性
中圖分類號:D923
作者簡介:商小偉,青島大學法學院法律史專業。
刑罰使人畏懼而不爭,但不能消除欲爭之心;“禮教使民不爭且能化之與無形”①。刑罰通過外在強制力使人們迫于法的威嚴而不敢有所逾越;禮對人的束縛更多的是通過教化,使人們從內心認同,自愿的遵從,表現為一種內在的強制性。馮小青和王氏同為明清時期的婦女,面對婚姻生活的不幸,一個克己復禮,一個背離禮俗,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選擇,卻都難逃一死。本文主要通過分析比較馮小青和王氏的行為差異及其原因,對禮與刑強制性的表現做簡要分析。
一、禮的內在強制性:馮小青的命運及原因分析
馮小青是一位世家女,自幼體弱,后父死家敗,十六歲嫁給馮生為妾,喜好文辭,頗有才情。面對大婦的妒忌,馮小青忍辱避讓,后被趕到孤山獨居。馮小青久居身閨,雖不用為生計奔波,但婚姻生活的不幸使其飽受精神的折磨。楊夫人勸其改嫁,小青回答“婦人休矣…夙業未了,又生他想,彼冥曹姻緣薄非吾如意珠”。②面對生活的不幸,馮小青沒有改嫁他人,也沒有做出有違倫常之事,而是恪守禮教,最終郁郁而終。
馮小青做出這樣的選擇原因是復雜的,可能是她衷于自己的愛情。《馮小青傳》中記載到,馮小青和馮生之間是有感情的,兩情相悅情投意合,只是馮生軟弱,大婦強勢,又礙于大婦家族的財力,馮生放棄小青。馮小青忠貞于自己的愛情,然而在明清社會中的貞節女子并非指那些執著于丈夫愛情的女子,而是指那些執著于婚姻和家庭名分與榮譽的女子。在明清社會一個女子執著于情愛是會使家門蒙羞的。③如《紅樓夢》中賈母知道了黛玉為什么臥病不起時說的“她要是有這個心,便是我白疼他一場了”。馮小青的愛情并不被社會禮教所認同。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出于對現實處境的失望。馮小青作為馮家的小妾,在馮家的地位是極其低下的。面對大婦的欺辱不能為力。在這樣一個禮教森嚴的社會,馮小青改嫁與否都已經不能改變其作為妾的命運。
馮小青受過怎樣的教育我們不得而知,但是作為明清社會的名門家族,家訓是必不可少的。明清時期貞節觀念盛行,《列女傳》作為道德模板廣為流傳。馮小青成長在男尊女卑,夫為妻綱的禮教熏染下,已經深陷其中。發乎情,止乎禮,禮教的烙印已經深深的印刻在馮小青的身心。④“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⑤馮小青已經變為禮教的擁護者。規則不可怕,可怕的是深受其害的人卻變成它衷心的捍衛者。深受禮教的迫害而不自知反而身體力行的維護禮教,這正是禮內在強制性的表現。馮小青的愛情不被社會主流觀念所認同,作為女子的也不被社會所諒解,在禮教和現實中苦苦掙扎,郁郁而終。其根本原因在于自己對自己的否定,禮教已經深深根植于其內心。禮通過不斷的教化,使人內心認同,將其內在強制性發揮的淋漓盡致。
二、出禮則入刑:王氏的命運及原因分析
馮小青和王氏是兩個階級的人,王氏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婦女,對她來說生存是最重要的。王氏自幼孤苦,生活貧困,他的丈夫對她很不好,她與人私奔,很大程度上是幻想一個更好的生活,受了這樣的鼓動。當然,王氏只是一部分典型,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女子。《烈女傳》中記錄過很多視貞節如命的女子。但是我們也應看到,對于王氏而言,她所處的社會環境,一個偏遠的郯城,社會對于她給予的關注是很少的。社會對于節婦烈女的要求是很高的“她們大多是很年輕就開始守節,時間長達幾十年,具有常人難以想象的毅力和勇氣。那些衣食豐足、三十歲以后才守寡的婦女是不會被選入這個行列的。更何況還有不少下層的節婦烈女由于無人替她們申報而被漏載。”⑥蒲松齡也對所謂鄉紳編纂的賢良傳記抱著不置可否的態度,甚至嘲笑那些鄉紳假公濟私。
這樣,我們可以對王氏的行為選擇有了一定的認識,一個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婦女,為生活而奔波,拋頭露面,接觸形形色色的人,她并不是社會所關注的焦點,同樣她也不奢求能著碑立傳,她要的是實實在在的生活。王氏與馮小青是不同的,一個孤女連父母是誰都無從知曉,更沒有讀過什么書,連生存都難以保障,又如何要求她恪守禮教。倉廩食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正如梁治平先生所言:“理想都是美好的,但是他所遇到的第一個問題總是生存,生存是現實的,所以人首先也是現實的。”⑦對于王氏來說,讓她甘心遵從禮教是不現實的,禮內在強制性顯然對她不起作用。這時刑法的外在強制力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夫禮者民之防,刑者禮之表,二者相須猶口與舌然。禮禁未萌之前,刑制已然之后。”這便是出禮則入刑的道理。
《大清律》規定“如果丈夫當場捉到通奸雙方,并在氣頭上把他們殺了,在法律上都被認為是正當的”。王氏與情人私奔已經觸犯了刑罰,王氏如果不回到自己的家里可能不會死去。但是古代社會,對于一個逃亡在外的婦女來說,想
要生存是不容易的。《大清律例》規定“若收留在逃女子(不送官府),而賣為奴婢者,杖九十,徒二年半;為妻妾子孫者,杖八十,徒二年”,在郯城周邊的鄉村,王氏這樣私奔在逃的女人,想要找到謀生的方法幾乎是不可能。史景遷也寫到:“如果趕路對他們兩個來說已經不容易了,那么對于不久后被情人拋棄而孤獨留在路上的王氏來說更是一場噩夢。”按照法律王氏應該與丈夫離婚,但是王氏又符合“三不去”中“無所歸”,屬于不能離婚的情況。可作為一個私奔的女人《大清律》規定,即使回到家里丈夫也要把她送走。刑罰對此做了層層的規定,一步步的將王氏逼上絕路。
三、禮與刑兩種強制性表現的意義
馮小青和王氏的選擇不同,結局卻是相同的。馮小青是死于禮教的束縛,而王氏沖破禮教卻被刑罰一步步逼上絕路。禮與刑發揮作用的方式不同,禮是通過內化,讓人們自愿去遵守;刑罰則是通過畏懼或者懲罰來被動的規制人們的行為。但另一方面,禮與刑又是互為表里的,相輔相成。“刑律乃道德之器械”正是這個道理。對于諸如馮小青們來說,通過禮的作用就能達到約束她們行為的目的,因為她們從小到大所受到的教育已經使她們早已被禮所內化,禮的強制性深深的束縛她們。但是社會總是多方面的,存在馮小青之類的上層人士,就會有諸如王氏這樣的社會底層,她們沒有受過什么教育,是禮教沒有內化到的,或者可以說她們并不是禮教所關注的階層。這時就需要刑罰的輔助作用,用刑的外在強制力對她們進行約束。
禮與刑強制性的表現方式不同,產生的效果也是不同的。正如馮小青和王氏雖然結局相同,但是死后所產生的影響是不同的。馮小青作為禮教的信奉者,其生前不被社會所諒解,但死后卻傳為佳話,生前被禮教束縛,死后仍為禮教所利用,著碑立傳,成為禮內在強制性的宣傳工具。而王氏生前沒有能力傷害任何人,死后卻產生極大的影響。作為厲鬼報復的傳言,在村里傳了幾十年,甚至成為寡婦對抗外界強迫其改嫁或爭取自由的武器,值得我們的深思。禮的作用在于自律,通過教化使人們自愿的服從,從而達到其內在強制性的作用;而法的作用在于他律,通過外在強制力使人們畏懼而約束自己的行為。禮與刑的強制性相輔相成,對穩定當時的社會秩序具有重要意義。
[注釋]
①梁治平.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203-204.
②潘光旦.馮小青——一件影戀之研究[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5.
③吳存存.明清社會性愛風氣[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
④李瀾瀾.試論明清文人對馮小青及其生存環境的解讀[J].廣西師范學院學報,2009,1,30(1).
⑤班昭.女誡.
⑥吳存存.明清社會性愛風氣[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
⑦梁治平.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
[參考文獻]
[1]潘光旦.馮小青——一件影戀之研究[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5.
[2]史景遷.王氏之死[M].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5.
[3]吳存存.明清社會性愛風氣[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
[4]梁治平.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
[5]龐樸.儒家辯證法研究[M].北京:中國出版集團,中華書局,2009.
[6]班昭.女誡.
[7]<大清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