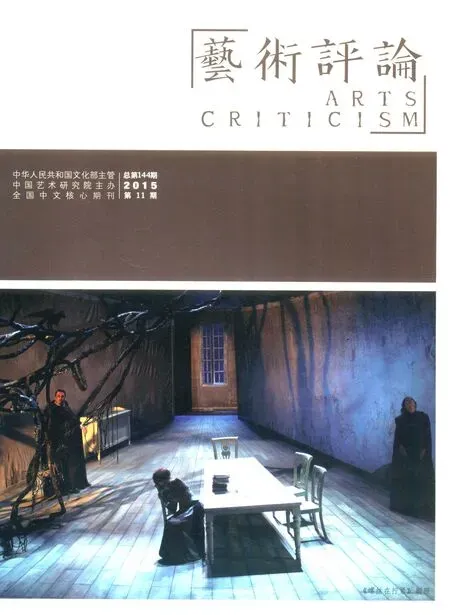《床畔》的漏洞及其觀念問題
白 草

嚴歌苓似乎特別善于抓題材,而且迄今為止她的大部分小說作品存在著一種過于明顯的模式,即一個被著力刻畫的女性,加上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或現實主題,后者甚至不能說是某種背景因素,僅僅起到調味作用。如《一個女人的史詩》與革命,《第九個寡婦》與土改運動,《陸犯焉識》與知識分子改造,《媽閣是座城》與賭城等。植物人題材顯然是嚴歌苓的又一個新“抓點”:上世紀70年代中期,護校畢業生萬紅被選拔出來,擔任一個英雄連長的“特別護士”,這位英雄在排除啞炮時為保護戰友被炸成了植物人。在所有的人包括主治醫生、英雄的妻子等都不抱希望時,萬紅卻從植物人眼皮閃動上,自以為找到了一個強硬的證據,此后她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來證明那個眼皮跳動的重大意義:英雄不是植物人。這就是嚴歌苓最新長篇小說《床畔》要告訴給我們的故事。
《床畔》初名《護士萬紅》(原載《收獲》2015年第2期)。不管有多少讀者喜歡嚴歌苓,也不說批評者怎樣急切地為一部發表時間只有數月的小說叫好,都無法掩飾其中一處過于明顯的、致命的漏洞。全書凡十八節,還有一個“尾聲”,情節發展到一半時,護士萬紅已經被寫成了一個忠實的情人。其時她給植物人張谷雨念了幾封書信,然后揭開他身上的床單,尋找被蚊子叮咬過的部位以便及時排毒,否則皮膚上的疹塊會潰爛:
她見他的身體比幾年前高大偉岸,肌肉仍然棱角分明,只是上面覆蓋的脂肪比過去厚實。兩片扇形的胸大肌向肩膀展開。似乎這個軀體從來沒有完全松弛過,筋絡和肌肉始終在運動,剛剛放下肩上的一部鉆孔槍,或剛剛吹完一聲長長的哨子。
這是1979年的6月份,外面下著大雨,眼見一場洪災即將降臨,護士萬紅或者說情人萬紅正給她的“谷米哥”左胯傷口涂抹藥膏,此時距1976年初夏英雄張谷雨入住醫院的時間,已經過去了整整三年。一個植物人不言不笑,不能自主吃喝,大小便失禁,完全依賴護理才可維持生命,臥床三年之后其身體依然“高大偉岸”,肌肉“棱角分明”;如果說這種違反醫學科學常識的描寫讓人吃驚不已,那么,更讓人感到困惑不解的是,敘事者通過護士的眼睛再度見證,這個植物人不僅僅現在身體健壯、似乎完全沒有松弛過,而且比三年前還要“高大偉岸”。這個情節漏洞當然是極為低級的錯誤,屬于典型的硬傷,一望便知。
王蒙先生于四十年前就指出過,一個細節上的失誤會引起整個藝術世界的垮塌,他的這段話值得摘引出來:
如果你稍不小心,如果你在日期上、年齡上、季節上、地點上、場合上、日月星辰上、服裝道具上、一個臉色或一根頭發上有一點粗疏,有一點錯亂,有一點任意“亂點鴛鴦譜”,有一點不鄭重、不嚴肅、不負責,就會使乾坤逆轉、日月顛倒,就會引起你的那個藝術世界的地震、雪崩、泥石流,甚至天塌地陷,使你的那個藝術世界像淋了雨的紙房子一樣地垮成一攤爛泥。
有經驗的、優秀的作家,一般不會出現帶有硬傷性質的情節失誤,自不待言。情節上的漏洞往往與小說的主旨或作家的情懷有關,也即小說觀念或作家情懷在某些方面出了問題,才導致諸種失誤或矛盾出現,而作者卻渾然不覺,竟還自以為得計。《床畔》寫的是植物人,它的主旨卻在用力證明一個結論:植物人不是植物人。護士萬紅無私地投入了自己的青春、生命,就是證明這個植物人被“冤枉”了,他不是植物人:因為他的脈搏在跳動,他的眼皮在微閃,他的血液在循環,特別是他能以外人不察的方式撞倒輸液架以“報警”,這一行為便成了一個過硬的證據,“戴了這么多年的植物人的帽子,終于在今天晚上摘掉了——因為他打翻了輸液架”。小說關于植物人癥狀的描寫,不出媒體所傳播或大眾日常所接受的知識范圍,只是以形象的方式演繹了一遍目前對植物人的一般認識或印象。匯集種種信息,足可見出小說的反科學主題,在科學與人情之間存在著一種隱性的對立關系:足夠的人情關懷是植物人恢復正常狀態的主導因素。而這種對立關系則限制了小說的想象空間,不可能提供哪怕高出于一般社會常識的、多少有點新意的認識。與此相對應,小說在細節層面和形象層面上,必然要把護士寫成情人,除此以外,別無他途。
對1976年的中國少女來說,多年灌輸的英雄崇拜觀念,可以使她毫無心理障礙地接受僅具生物學意義而毫無情感交流能力的植物人。但是,別忘了,英雄的光環終究會褪色,所以在第五節中,英雄角色悄然地被置換為“好人”——“那么好一個人,你怎么忍心讓他受那樣的痛苦呢”。然而,“好人”植物人并不足以構成足夠的說服力。還有職業信念,問題在于,護士的職業責任僅限于日常護理,護理一個看起來永遠都無法醒過來的植物人,任何飽滿的信念也會一點點地被磨損殆盡。那么,最終只剩下了情感維系,護士和植物人被描寫成了情人關系。現在,我們終于知道了,《床畔》表面上描寫植物人,其實是在寫愛情故事;愛情故事被寫濫了,要另辟蹊徑,寫得他人未曾道、此前不曾有,和植物人的曲折愛情故事,有哪個當代中國作家寫過呢?
情人、戀人,至少需要二者間調動特殊的敏感、激動。年輕的少女面對此前從未晤面、目前不能交流、此后更不知會出現何種前景的植物人,由于英雄崇拜觀念和職業信念的驅使,將內心莫名的力量轉化為濃烈的情意而愛上植物人不是不可能的。但此種關系絕對有盡頭和限度,不論少女的愛有多強烈,她終日面對的只是一個眼皮間或一閃、嘴角偶爾冒出小泡的植物人,他比玩具更單調、乏味,他們之間沒有交流,而交流才是人與人之間產生關系的基本因素;植物人,事實上是對活人耐心的嚴酷考驗。可是,《床畔》不僅沒有寫出那種令人絕望的單調、乏味,也根本未觸及那種對相關之人日復一日嚴酷的、近乎于磨折的考驗,反而把少女護士的愛寫得一日濃似一日。那么,我們現在也終于知道了,《床畔》不單寫了一個和植物人的愛情故事,而且寫的是一個畸形、變異、重口味的愛情故事。
小說最出彩的地方,當然是護士萬紅上演獨角戲,第五節末尾,萬紅不能把持地叫了病人一聲“哥”,從而改變了二人此前的醫患關系。此后,該護士一直在輕聲、柔聲、曼聲地呼喊著“谷米哥”,于床畔秀恩愛。或許有些讀者讀至此處,已淚花閃閃,不能自已。深情地呼喚,這不是作家用心想出的細節;不幸而有植物人的家庭,母喚子、妻喚夫的感人事跡,不時見諸報端媒體,作家不過取用了現成的社會題材。有意思的倒是植物人竟然能夠回應一種呼喚,眉心抖動一下,“一層黯然神傷掠過他清澈的眼睛”;更有意思的是,護士萬紅發現植物人不僅有遺精,而且言之鑿鑿地寫道,夜中勃起一二次,“性活力”更接近于一般性欲正常而無配偶的中年男性。一方輕喚,另一方若無回應,則顯見沒有故事可講;為了故事,哪怕他是一個植物人,也必得要他作出反應。據一本出版于十幾年前的醫學著作,植物人對有害刺激會出現哼哼、呻吟等反應,或看到親人及聽到親人聲音時也會流淚,這些表現僅能說明病人開始恢復意識,但他們沒有“情感反應”。以此作為參照,《床畔》把植物人的“意識”活動當做“情感反應”,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缺乏或無視基本的科學知識,以人情作為標準涉足科學所覆蓋的領域,以想當然的心態和對盲目意志力量的迷信,貌似要寫得更具人情味,結果卻是不近情理。沒有情感反應的病人,卻能勃起、遺精,而且其性能力接近一個性欲正常而無配偶的中年男性,這不是反科學,又是什么呢?
究竟是怎樣一種強大的力量,使得少女奉獻出青春,愛了沒有情感反應的植物人?《床畔》中一定會有答案,而且答案不只一個:他是英雄,是好人,還要再加一個道德上的保證,即這位英雄植物人是個被遺棄者,他的結發妻子只要逐月領取他的工資和補助,不愿擔負妻子應盡的照顧義務;更有甚者,該女性竟然和醫院燒鍋爐的工人偷情茍合,成為丑聞。這種寫法雖頗近濫俗,卻以妻子道德上的污點保證了情人角色的合法性、合道德性,向周圍有關的人、亦向讀者顯示,把護士做成了情人實屬出于不得已。為了強化情人角色的合法性,獲得更多道德上的支持,小說不惜以極端歪曲的情節,將主要人物與其周圍人物截然區分:植物人張谷雨追悼會上,只有萬紅一人痛哭流淚,其他人包括親屬、朋友等,無動于衷,有的竟至于笑出聲來。以貶低他人的方式來抬高主要人物,或許也是“三突出”的殘留觀念在作怪,亦未可知。
無論英雄、好人抑或某種道德上的優勢,對愛情而言,所有這些均為外在因素,不能代替愛情本身所需要的力量。在整部小說中,可以找出種種外在理由,卻找尋不出一條內在的、本質的理由,證明護士愛上植物人是應該的、不得不愛的。實際上根本找不出這種理由,因為讓護士愛上此前從未謀面的植物人,本身就屬向下的想象力,是一個站不住腳的臆想。小說第一節末尾,作家卻給出了一條看起來非常充足的理由:有個剎那間的目光相遇。她心跳得咚咚響。能算數嗎?人有時跟畫上的人也有目光相遇的剎那。要到許多年后,當旅游者把萬紅叫做“最后一個嬤嬤”時,她才會肯定,最初跟張谷雨的目光相遇,是他們交流的開始。
就在萬紅直起身時,她看見張谷雨跟她
拿一見鐘情、見了即刻來電的標準,寫護士與植物人的初次相遇,更加印證了我們對小說的判斷,即作家從一開始就要把它寫成愛情故事。然而,她在表面上、在形式上偏偏寫一個植物人,也就是植物人其名,愛情其實,這種標準錯位、價值錯位的寫法,恰如前引王蒙先生所說,是一種錯亂,是一種粗疏,是一種“亂點鴛鴦譜”。總之,就是一種不嚴肅。把一些東西、一些事物人情化、愛情化,在賺取讀者眼淚和同情的同時,必然會粉飾一些嚴酷的現實——植物人大小便失禁問題,這本是其題中應有之義,卻恰是小說回避了的,無一字提及,展現在讀者眼前的,一概為不靠譜的護士恩愛秀。
植物人是越來越受到關注的社會性話題,在報紙、網絡等媒體上,時常可以見到相關的報道和探析。這種報道呈現出較為顯著的特點,即它們并無多大興趣關注醫學科學的前沿成果,以及研究趨勢和走向,而把興趣點集中在一種模式上:用親情喚醒植物人。其實,某個家庭一旦真的有了植物人,他們的家庭結構關系、社會關系可能會發生巨大的改變,尤其在醫療保障體系遠未臻于完善的環境之中,有多少人因此不得不把自己的機會、幸福、命運等砸了進去,賠上半生或一生。有責任心的作家,有良知的作家,嚴肅自律的作家,在沒有做好諸般調查、體驗工作之前,一句話,在沒有做好一切準備工作之前,是不可以輕易觸及此話題的,因為一旦開始寫作,他所見所聞的,將是深深的、言語很難表達的悲傷和哀痛。在某種意義上說,植物人題材本就是一個禁忌。可是,這一禁忌對嚴歌苓這樣的作家來說,是不存在的。嚴歌苓是一個高產作家,同時,也是一個以跟風、迎合為能事的作家,只要社會上出現某種風向,或某種話題引起關注,都會馬上抓住,立即寫來,并迅速給出一個答案。《床畔》即是一個顯例。但是,她所給出的答案,是甜膩而有毒、舒適而有害的:年輕的護士,拼出一生去服侍一個實不相干的英雄,從青絲滿頭的少女熬成了一個白發老嫗,英雄死了,她也老了。而在小說最后一段,又一個英雄的植物人出現時,該護士主動請纓,再次參加醫療隊,且看這里的失誤、漏洞嚴重到了何種程度——護士萬紅刻骨銘心地愛了一個植物人,“這樣的私情沒有旁人的份”,可是其人尸骨未寒,轉眼間又極度亢奮地去追尋另一個植物人。這算什么?無非一具木偶而已,僅僅體現了作家的觀念。所以,真正值得分析的,是小說中處處流露出的觀念:讓普通護士賠盡一生還不夠,還要在其老境已至時再去服侍另一個英雄,然后回贈她一頂廉價的“英雄”牌帽子。鼓動普通人把自己全部地、無私地奉獻給一個英雄,骨子里正是對普通人生命價值、人生權利的蔑視,這種有害觀念又借助了愛情、親情的方式播散開來,不僅不會令人起疑,反而讓人感激涕零。借用尼采說過的話形容此種觀念是再恰當不過了:大毒使人死,小毒則使人感到舒適得像做夢。此之謂也。
注釋:
[1] 嚴歌苓.床畔[I].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5.
[2] 王蒙.王蒙文集·你為什么寫作(第21卷)[I].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175.
[3] 張國瑾主編.持續性植物狀態——植物人[M].南京:南京出版社,1998:24.
[4][德]尼采.尼采著作全集·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第4卷)[M].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