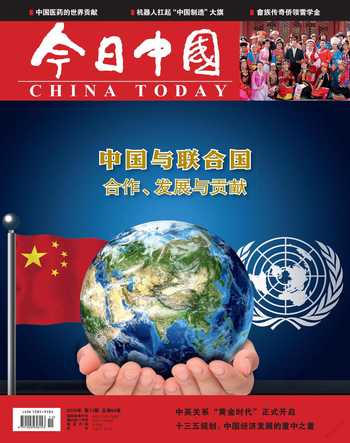蕭寒和他的《喜馬拉雅天梯》
文|
- 人物 -
蕭寒和他的《喜馬拉雅天梯》
文|王 南
80分鐘,講述一僧一寺、一座山、一群人的故事。它紀錄了普通人可能一輩子也無法見到的風景,而這一切在電影院里會獲得最深的感受。

《喜馬拉雅天梯》電影海報
這是第一部把三腳架帶上珠峰峰頂的電影,也是全球第一部完整記錄珠峰北坡登頂過程、第一部在珠峰海拔6800米完成航拍的電影。導演蕭寒,燒掉1300萬,拍了一部震撼人心的紀錄片。80分鐘,講述一僧一寺、一座山、一群人的故事。它紀錄了普通人可能一輩子也無法見到的風景,而這一切在電影院里會獲得最深的感受。
4年磨一劍
他叫蕭寒。一個紀錄片導演。5年前,他過著安穩的生活,但總覺得少了什么。
其實蕭寒是筆名,他本名叫崔涌,是浙江工業大學人文學院播音與主持藝術專業副教授。除了教師這個角色,他還是電臺主持人、電視主持人、戲劇策劃人。
“我之前的職業是做電視傳媒,還做一些戲劇的策劃和在大學教書。2010年,好像一切突然積累到那一刻,我覺得紀錄片是我喜歡的、能夠用來做一個表達的創作形式。”
2010年到2011年,蕭寒拍了一部小型的獨立片《麗江拉夫斯基》,網上點擊量超過600萬。那之后他就在想,尋找一個更大的、更厚重的選題玩兒一把。
有人告訴他,有個故事一定會直指人心。
《喜馬拉雅天梯》片名源于青藏高原巖壁上畫的那些白色小梯子,當地人稱之為“天梯”,并相信它可以承接世人的靈魂通往圣地。
在拉薩有所登山學校,這幾乎是世界上唯一一個以培養高山向導為目的的學校。珠峰腳下的藏族少年在這所學校里接受4年訓練,方可成為一個合格的高山向導,成為“天梯”。
4年前,蕭寒聽說了這樣一個故事。上絨布寺位于珠峰北麓,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寺廟。阿古桑杰是寺中唯一的僧人。他的兒子是一名畢業于西藏登山學校的高山向導。當時阿古桑杰的兒子托清華大學的老師雷建軍給在寺廟里的他帶一本經書。
當雷建軍把這個事情跟蕭寒說了之后,蕭寒頓時覺得非常感動。因為高山向導是最危險的職業之一,他們要成為登山者的梯子、拐杖、背包,有時甚至需要移開路上登山者的尸體。如果一不小心,他們也會成為其中一具。
正是高山向導這樣的精神和信仰,打動了蕭寒。蕭寒說,他們非常平凡,卻有著不平凡的追求和選擇。站在世間最高處,給世人留下了動人的故事。“他們值得被紀錄。”
由此,蕭寒與雷建軍定下了拍攝《喜馬拉雅天梯》的方案。他們想紀錄這些藏族少年的故事,記錄在氧氣稀薄、環境惡劣的情況下,釋放出的溫情、欲望、失望、憤怒、勇氣當然,還有夢想。
“大家的內心呈現,混合在這樣一個時空里,人物、命運、選擇、判斷、糾結、夢想、激動,各種情緒的綜合,也是打動我們要去做這件事情的很重要的原因。”蕭寒說。
開始,蕭寒非常慎重,先做了一年的田野調查。
“當初以為100萬就夠了。但4年追蹤下來,拍攝制作最終花了1300萬。可想而知,我們是在多么無知無畏的情況下就開始干了。”
越往后,蕭寒越覺得,“是這部電影一直在引領著我們走,我們在跟隨它。這個選題本身的巨大能量就在那兒,不是我們賦予它,而是我們向這個能量靠攏。”
4年之后,這部電影圓滿收官。
扛著攝影機攀登珠峰
這是一個龐大的工程。
一開始進入到紀錄片行業,蕭寒帶著一種理想化色彩,后來他發現,“很多紀錄片人都苦哈哈的,在中國影視門類當中,紀錄片的地位其實很可憐。”
“為什么紀錄片不能堂堂正正地在電影院里放,讓大家買電影票進來看呢?”蕭寒還是帶著一種理想。
拍攝團隊在5200米海拔的大本營,經歷著常人難以想象的艱辛。
在高原的紫外線下,登山向導們一水兒黝黑面容,他們是一群藏族少年,普通的牧民孩子,笑起來跟熱情的藏民沒有什么兩樣,然而在生死關頭,蕭寒知道,自己可以用性命相托。
珠峰真得很美。蕭寒的愿望是,一定要把這樣一種美盡可能多地記錄下來。“大本營再往上,那是極少的人可以上去,很多人這一輩子,不可能親眼看到。那就盡可能讓大家知道上面到底長什么樣。”
實際拍攝中存在很多困難:要把電池帶在身上,在寒冷高海拔的地方,如何讓電池多工作一會兒,揣在懷里,用暖寶寶,蕭寒團隊進行了各種嘗試。航拍的飛行器不小心摔壞了如何解決,設備怎么背上去,這都是些磨人的問題。
拍攝過程中的最大困難,莫過于高原反應。為了跟拍登山向導的身影,拍攝組在珠峰大本營駐扎了兩個月,蕭寒的助理患上了中度肺水腫,團隊里的每個人都深切體驗著高原反應。
“甚至有一次要拍星空,攝影師扛著機器爬到了海拔7028米的地方,突然意外摔倒,恰好掉在帳篷上,不然一定會嚴重摔傷。”蕭寒說。
200萬很快花完了,那就賣房子吧,“500萬,夠不夠?”這是拍攝《喜馬拉雅天梯》中發生的對話,蕭寒說,他還是太天真了,500萬,很快又沒了。“沒人在中途停下來,就跟登珠峰一樣,停下來,可能就意味著再也沒有下一次機會。”
“我們把只爬過北京香山的攝影師逼成了登山運動員,扛著機器爬到了海拔7028米,從160斤減到了140斤。”回憶起當時的情景,蕭寒感慨莫名。

蕭寒
向導們的另類人生
普布頓珠是登山學校第一批學員,創造了中國第一個無氧登頂珠峰的記錄。現在他是登山學校的一名教練。他是孩子們眼中的怪叔叔。訓練的時候動不動就照著學生屁股上來一腳,夜里卻偷偷去宿舍看看孩子們的被子夠不夠厚。
巴塔,一個天才的登山者,跟普布頓珠都是第一批的學員,因為登山速度超快,得了一個“猴子”的美名。他既是《喜馬拉雅天梯》紀錄的對象,也是這部紀錄片的高山攝像。是他扛著攝像機一路登上了海拔8848米的珠峰頂。
9次登頂珠峰,再有一次就可以齊平目前的世界記錄。但他真的不愿登山,“想用一天的時間我就登到珠峰的頂端,然后從尼泊爾那邊下去,從此以后再也不爬了!”
索多是家族里第一個去城市謀生的人。2009年3月29日,背著50斤的背包,揣著1000塊錢,坐了8小時車來到拉薩。2013年,他攀上了珠峰海拔8400米,離頂峰只有一步之遙。卻因為搶救一位突發腦水腫的登山者,失去了沖頂機會。
那次回來后,索多很久沒有說話,冰天雪地里,他看到十幾具登山者的遺體,面目模糊,只有登山服在積雪中明亮鮮艷,“離死亡太近了,就幾米遠。”
2014年,他終于登頂成功,非常興奮,不停地發朋友圈,但下撤的時候,他出現了嚴重的雪盲。
在向導們的信仰中,山是神圣的,他們只轉山不登山。但在現實里,他們感謝珠穆朗瑪給了一口飯吃。
從未走出過村子的他們來到拉薩,學習語言(漢語、英語)、急救、攝影投入到最冒險的登山運動當中。
“他們平凡如世界上任何一個年青人,有自己的困惑、苦惱、人生選擇和未來,然而他們也偉大得如同每一位攀登高峰的人,在環境的極限與人類的極限之間,在一步之遙的遺憾與站在世間最高處之間,留下動人的故事。”

《喜馬拉雅天梯》劇照
巨大的檢驗
幾個時間點透露出這部影片的進程:2011年,籌備拍攝;2012年,田野調查;2013年9月,正式開機;2014年10月,拍攝完成,進行后期制作;2015年7月,通過審批;2015年9月,拿到放映許可證。在拿到許可之前,影片還在調整。
45000多分鐘拍攝素材,1300萬元投入,整整4年的時間,一部真實記錄西藏年輕高山向導珠穆朗瑪峰北坡登頂全過程的紀錄片終于殺青。當剪輯師最終停下手中的工作時,“我們所有人的眼中,都有最復雜的情緒。”
片中90%出現的是藏語,觀影需看字幕。蕭寒表示,說他們自己的語言,才有更加自然的狀態流露出來,不做作,不生硬。
在提案階段,影片獲得了中國首屆國際紀錄片提案大會最具“國際傳播潛力”大獎,并以中國區第一名的身份入圍法國陽光紀錄片大會亞洲展,BBC、NHK也都決定購買版權
這部影片的國際推廣策劃中有一位是《西藏一年》的導演蘇影,BBC、NHK等電視臺購買,都緣于他的幫助。他還推薦了《西藏一年》的攝影師—扎西旺家做本片的攝影指導。
在中國,紀錄片是很小眾的電影類型,這意味著《喜馬拉雅天梯》很可能淹沒在商業大片中。對此,蕭寒也有不小的擔憂,10月16日《喜馬拉雅天梯》登陸各大影院公映,用蕭寒的話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檢驗”。然而,令他欣慰的是,點映上座率非常高,80%的觀眾是第一次進電影院看紀錄片。
“能把電影院紀錄片‘處女看’獻給《天梯》,我已經非常感動了。”蕭寒說。
對蕭寒來說,更大的夢想是,借助有力量的一個選題,吸引那些從未看過紀錄片,尤其是從未走進電影院看紀錄片的人,能夠第一次走進電影院看一部紀錄片。
“也許從此以后,你會產生特別奇妙的化學反應,你會愛上紀錄片,愛上這種類型,會慢慢讓這樣一個小眾的類型片,在電影市場中有它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