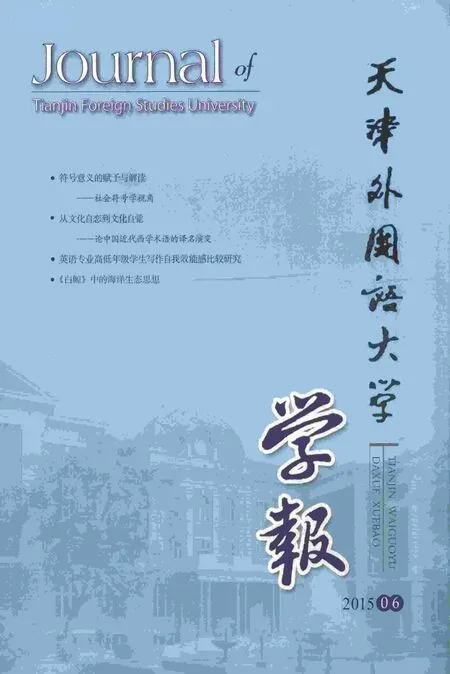“外省人”意象與英格蘭共同體形塑——再讀《米德爾馬契》
趙 婧
(福州大學 外國語學院,福建省跨文化話語研究中心,福建福州 350005)
一、引言
《米德爾馬契》(Middlemarch)是被眾多評論家闡釋過的一部19世紀經典小說,但西方學者對該小說的共同體建構意義存在爭執(zhí)。希利斯·米勒(Joseph Hillis Miller)通過對小說中重復使用的網、河流和光學意象進行分析,認為該小說一方面主張有機社會概念,建構人類行為的普世規(guī)律和客觀可知共同體,另一方面又揭示個人中心主義、主觀性和個人投射等相反內容。這些使小說并不能表達共同體構建的意圖卻展現(xiàn)了作者的矛盾思想。而蘇珊妮·格瑞夫(Suzanne Graver)反對米勒的解讀方式,認為米勒關注個別意象群的差異性,但沒有意識到這些意象個體恰恰展示了喬治·艾略特將碎片和分隔意象一以貫之,以此使小說聯(lián)結成整體,建構出可知共同體的意圖。他們關注小說的個別文本特征和共同體建構的主題,但卻未重視這一主題與小說“外省人”意象的關聯(lián)性,不利于全面把握小說文本共同體建構的目的和途徑。
評論界對小說進步、政治、宗教、倫理、情感、女性、醫(yī)學、音樂等主題和文本形式的關注也層出不窮。國內學者殷企平(2009)認為,小說撲朔迷離的情節(jié)、犬牙交錯的人物關系和廣闊的社會畫面展示了小說反對社會飛速發(fā)展,主張平穩(wěn)發(fā)展的主題思想。高曉玲 (2008)以認識論作為研究重點,在西方認識論的思想史背景中展開對作品情感認知、情感即知識的討論。王海萌(2012)關注了小說對19世紀中葉社會轉型時期中產階級的身份塑造。她強調艾略特小說將中產階級自我塑型再現(xiàn)為“一種建構性的階級文化”,復雜性體現(xiàn)了艾略特“本人身為中產階級成員所固有的文化矛盾”。雷蒙·威 廉斯(Raymond Williams,2013:235)曾經指出,艾略特對英國小說發(fā)展的一個重要貢獻是“看到了農民和工匠,甚至勞工憑他們本身的權利被呈現(xiàn)出來”,也就是說,她的小說改變了傳統(tǒng)小說觀察視角,書寫了農夫、工匠等鄉(xiāng)下底層人民的日常經驗。雖然威廉斯強調的是艾略特早期作品的特征,而且《米德爾馬契》這部鴻篇巨制表現(xiàn)出網狀敘事的多焦點復雜性,但小說副標題“外省生活研究”還是清晰地闡述了艾略特的目的,即研究外省小鎮(zhèn)及其周邊的鄉(xiāng)村社會生活。艾略特(Eliot,1994:795)在作品的開頭和結尾明確表示自己要描寫的是那些躺在“無人問津的墓冢”里的小人物,他們懷著與圣女特蕾莎一樣殉道者的理想和信仰,雖然理想破滅,卻依然認真生活。基于以上爭論,本文擬從“外省人”意象入手,探究小說選擇外省人進行書寫的新歷史觀特征,考察文本對外省人特征的描繪,并對外省人與共同體關系進行闡釋。
二、新歷史主體選擇和書寫
外省(provincial)和外省人概念指首都之外的區(qū)域及其民眾,如英國倫敦、法國巴黎之外的其他區(qū)域及其居民。19世紀中葉的倫敦已經發(fā)展成人口過百萬的世界性大都市,經濟繁榮,各民族文化匯聚,頗具趨向一體化和標準化的現(xiàn)代都市特征。盡管如此,“鄉(xiāng)村人比城鎮(zhèn)人多,小城鎮(zhèn)人比大城市人多”(霍布斯鮑姆,2014:14)。英國其他區(qū)域的城市,尤其是偏遠的小城市里工業(yè)化進程緩慢,受城市化進程的沖擊影響較小。這些外省保留了更多農業(yè)經濟結構和社會傳統(tǒng)以及英格蘭民族文化特征。但也有人對外省概念持不同觀點。福樓拜曾這樣寫道:“愚蠢的真正源頭,最愚蠢的社會,最荒唐的制造者,一堆蠢蛋聚集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呢?在外省地區(qū)。在那里最教人無法忍受的居民是誰呢?一般人,他們一天到晚專注于瑣碎無聊的事情,忙著干些扭曲觀念的工作。”(蓋伊,2006:141)。
19世紀歷史學獲得專門學科地位之前一直都是跟文學和神學相混雜,歷史敘述與文學一樣雜糅了虛構和真實。文學因此也堅稱自己具有歷史的權威性和真實性,有些文學家,如笛福,否認自己作品的虛構性,有的甚至直接自稱歷史學家,如菲爾丁。歷史學家獨立門戶后希望與文學劃分界限,但文學家對歷史的眷戀難以割舍,他們采用現(xiàn)實主義的表現(xiàn)手法創(chuàng)作小說,并鍥而不舍地寫作歷史小說,有意模糊文學與歷史的界限。艾略特被后人稱為文學家和哲學家,因為她的虛構文學作品中充滿了哲思與智慧。而她在作品創(chuàng)作中表現(xiàn)出的社會歷史觀和歷史敘述方法卻并未受到足夠重視。海登·懷特(White,1978:33)甚至認為,《米德爾馬契》否定了歷史知識的社會作用,與代表歷史知識的主人公卡蘇朋相比,威爾代表的藝術更受作者青睞。這樣的結論使文本細節(jié)與整部小說主題脫節(jié),并不可取。
《米德爾馬契》的故事情節(jié)設定早于創(chuàng)作時間40年(故事發(fā)生于1832年議會改革前,故事連載發(fā)表于1871-1872年)。艾略特試圖以自然史的方法書寫議會改革時期的歷史和英國外省處于傳統(tǒng)與進步之間的民俗風情,引領讀者了解普通民眾眼中的社會變革和社會生活,因此,這部小說的副標題為“外省生活研究”。對于自然史寫作方法,艾略特曾在一篇雜文《德國人的自然史》中進行詳細闡述。文中對德國小說家、民俗學者和歷史學家維廉·亨利·黎耳的兩本著述進行評論。書是民俗學和史學交叉研究著作,作者以民俗學研究方法對現(xiàn)實生活展開田野調查和研究,以此描繪德國農民的民族特征。艾略特對這種寫作方法十分推崇,自覺地將小說家的敏銳觀察力和同情心與民俗歷史學家的冷靜理性和事無巨細實的考察方法相結合。《米德爾馬契》的副標題“外省生活研究”醒目地暗示了作者的創(chuàng)作意圖和方法。
在這篇長文中,艾略特表達了文本敘述的三個重要方面:主體選擇、選材途徑和寫作態(tài)度。作家記錄的對象應是社會底層的普通民眾。她認為,要真正了解人類社會關系,需要深入民眾,全面觀察他們的生活習慣、想法和行為動機,不能將人類關系抽象成幾何公式般的機械哲學來闡釋。有人認為沒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會天生具有道德意識,而富裕的貴族卻心猿意馬、遮遮掩掩地想再奪取特權等。這些誤解源于沒有對人民進行深入真實的了解。她希望“一位有深厚道德和廣闊知識修養(yǎng)的人,能擺脫成見,秉持專業(yè)精神潛心研究社會各階層自然史,尤其是要研究那些小店主、工匠和農夫,研究他們受現(xiàn)實條件的影響、他們的原則和習慣、對教士的看法、信奉的宗教信條、不同階級的影響,以及地位分化和發(fā)展狀況等等。經過詳細調查,作品才會有大量細節(jié)事實支撐,可以成為社會改革家的重要資料來源。”(Eliot,1990:118)艾略特強調作家文本的主體人物的身份及其生活細節(jié)的書寫價值。作家的書寫并非只是娛樂大眾,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社會文化現(xiàn)象參與社會服務,讓政治家了解底層民眾的普通生活狀態(tài)和日常需求,更好地為民眾服務。
作家應該像歷史學家一樣地深入生活調查,獲得第一手的可信資料。艾略特指出,很多作家沒有深入生活調查,他們描寫的農民表現(xiàn)出一種模式化的類同,如性情愉悅,一排潔白的牙齒,愛講笑話,房子寬敞明亮,孩子們紅撲撲的臉龐笑意盈盈。藝術家如果沒有在真實生活中尋找創(chuàng)作主題,他們心中的這些固定模式就很難驅散。她還提到真正了解耕夫的人不會認為他們生活愜意快樂。現(xiàn)實中很多農夫眼神遲鈍,言談緩滯,步伐沉重拖沓,像駱駝一樣憂郁,也沒有幽默和靈光一現(xiàn)。“扔在一邊的長襪,紅色外套和帽子才能體現(xiàn)傳統(tǒng)的英國農民。那些曬谷子的人,遠看時,他們揚起的谷子在太陽光的映射下,金燦燦發(fā)光……你會認為這些勞動的伙伴一定像畫里畫的那樣開朗、興奮。但是,走到農夫身邊才會發(fā)現(xiàn),曬谷子時農民最愛開玩笑,有女人在場時,還會發(fā)出陣陣粗俗放浪的笑聲,表達勝利者的奚落,跟我們印象中的歡愉相差甚遠。”(ibid.)艾略特敦促小說家走近民眾,近距離觀察他們的一顰一笑、一滴汗一杯羹,這樣寫出來的作品才能真實可信,脫離對人物形象的定式思維。這種調查方法與史學的研究方法相似,艾略特提倡作家采用歷史學家的方法收集資料,表現(xiàn)現(xiàn)實。
作家敘述應該像歷史學家記錄歷史一樣真實可信。艾略特認為,社會小說就要表現(xiàn)社會現(xiàn)實,不實描述就等于犯罪。偉大的藝術家作品使人們的同情心得以延展。就像司各特、華茲華斯和金斯利的作品那樣 “將上層人與下層人聯(lián)結起來”,消除階級阻礙,“比幾百篇的布道和哲學論文要管用得多”。藝術應該最貼近生活,拓展人們的生活經歷,使他們了解平日生活里接觸不到的人與事。這些是以表現(xiàn)現(xiàn)實為己任的藝術家之神圣職責。藝術家應以歷史學家般的虔誠對現(xiàn)實的描述如同鏡像(ibid.)一般。她痛恨弄虛作假,如果是對時尚或者王公侯爵禮儀性的談話描寫有所偏差,還沒什么關系,但如果是對“背負生活壓力多年的同胞的快樂、掙扎、勞作、悲劇和幽默的認識有了誤差,不真實。這是對歷史的背叛,是藝術家的悲哀和恥辱。”(ibid.:112)這表現(xiàn)了艾略特對普通民眾深切的感情和為民寫史的堅定決心。
在《米德爾馬契》中,艾略特選擇了多羅西亞、利德蓋特兩個主要人物作為線索,以布魯克、文西、卡蘇朋、菲厄布拉澤四個大家庭為主干,對米德爾馬契這個外省社會和外省人的特征進行研究和再現(xiàn)。與前期主要小說家不同,她的作品沒有司各特作品的騎士傳奇和戰(zhàn)斗喧囂,也沒有狄更斯小說跌宕起伏的故事懸念和驚心動魄的場景設置,這部小說聚焦于英國1832年第一次議會改革時期外省地區(qū)的普通生活場景。在她的小說歷史視野中,歷史主體不是叱詫風云的王侯將相,而是一群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喜怒哀樂休戚相關,有些房產土地、技術手藝或親朋好友的普通民眾,如從小失去父母由叔父監(jiān)管長大、善良坦誠的布魯克姐妹,學究氣十足、刻板無趣、一生致力于一本沒有意義也無力完成的神話索引的牧師卡蘇朋,開始豪情萬丈立志推進醫(yī)學事業(yè)改革,但終難抵制家庭生活壓力的醫(yī)生利德蓋特,極力宣揚宗教教義,誓為社會樹立慈善楷模形象,但難逃不光彩發(fā)家史折磨的銀行家布爾斯特羅德,以人為本、踏實誠懇的中年牧師菲厄布拉澤,依靠勤奮、技術、頭腦和信念安身立命的高斯一家等。其中有些人物生活富足,受過良好教育(如卡蘇朋、布魯克先生等),有些人物一度陷于貧困拮據甚至破產的邊緣(如利德蓋特、高斯一家等)。在艾略特的敘述中,他們的社會身份概念被弱化,沒有尊貴低下,內心豐富,充滿對真善美和親情、友情的渴求,每個人都只是“不求聞達,忠誠地度過一生,然后安息在無人憑吊的墳墓中”(艾略特,1987:783)的鄉(xiāng)鎮(zhèn)小人物,生存于同一片英格蘭土地,享受各自人生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交織成同一幅歷史畫卷。
跟19世紀超級大都市倫敦中現(xiàn)金聯(lián)結的市民相比,外省人更多地承載著傳統(tǒng)與過去,不論教育程度、財產數量、社會階層的差異,他們似乎無法左右歷史車輪行進的方向,無力改變或引領社會風潮,但卻是一群體驗歷史行進中最常見的喜怒哀樂、最普通悲歡離合的大眾。年鑒學派認為,如果把人類歷史進程當作奔騰不息的水流,傳統(tǒng)歷史學關注最引人注目的水流之上的泡沫,因為它們能指示水流的流速和方向,但是真正影響水流的卻是更深層的潛流。特定地域的地理氣候條件、物質生產和人類交往模式等結構性因素才會真正決定人類生活面貌。有些社會變化和群體日常生活悄無聲息,甚至沒有人注意到,卻對后世產生莫大影響。
如果按照有些學者的觀點,統(tǒng)一用廣義的中產階級來簽注小說的人物和情節(jié),概括作者和作品中大部分人物的階級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強調了維多利亞時期中產階級崛起這一時代特征。但露絲·利維賽(Ruth Livesey,2013:96-97)對此并不贊同,雖然維多利亞時期是自覺的階級意識形成的時期,但艾略特作品很少描述階級意識和階級沖突。她的興趣在于使用自然史的具象特征而非抽象概念來再現(xiàn)人物、遺傳和環(huán)境之間的關聯(lián)性。跟中產階級這一社會經濟地位標簽相比,人物的鄉(xiāng)土特征更應受重視。艾略特小說人物的塑造著重描繪外省人的心理動機,強調人類共同體不能忽視眾多小人物,是他們推動人類歷史不斷行進。
三、“外省人”意象的形塑
從18世紀末英國小說興起到19世紀小說作為最重要文體出現(xiàn)在公眾面前,再到19世紀中后期艾略特的小說風行英國,小說描寫的人物以及故事形式多樣,各有側重。笛福的小說塑造了不畏困難、積極進取的個人主義,理查遜以求婚為線索講述都市人物與家庭,菲爾丁以滑稽史詩的方式描述18世紀社會萬象,司各特的歷史小說將騎士、國王與平民交織在一起,簡·奧斯丁關注鄉(xiāng)紳家庭中女性的婚姻生活,狄更斯揭露大城市中底層人民生活的困苦。《米德爾馬契》描繪了生活在與倫敦迥異的小鎮(zhèn)和周邊鄉(xiāng)村的人物生活情況。對于1950年歐洲最大都市、人口過百萬的倫敦來說,他們都是外省人。利德蓋特和威爾是白手起家、曾見過些世面的專業(yè)人士,布爾斯特羅德是靠投機起家的士紳,徹泰姆是位富裕的從男爵,卡蘇朋是有地位的神職人員,多羅西亞一家無爵位,卻也是有聲望、土地和房產的士紳家庭。他們共同生活在遠離倫敦的外省小鎮(zhèn)周邊,各自的社會境遇和個人經歷迥然相異。小說敘述者從不同社會角色進入人物內心,褪去身份和階級的外衣,停留在人類共同的情感區(qū)域剖析心理活動,精細描繪在社會外力作用下的個人理想、期盼、情感、認知、掙扎、幻滅與妥協(xié)的軌跡。
《米德爾馬契》從以下三方面表現(xiàn)了外省人的特點。首先是外省人思想之狹隘和平庸。雖然小說描寫了多羅西亞、卡蘇朋、利德蓋特和布魯克先生的崇高理想,如成為圣人特蕾莎,寫一部傳世名作,建一座新興醫(yī)院或成為政治風云人物。但這些理想無一不受人譏諷或遭遇失敗。多羅西亞憧憬殉道者般的婚姻生活,希冀為宗教或人類事業(yè)奉獻全部,鄰居卻都覺得她不如妹妹莉西亞通達世故人情。她嚴苛律己,連佩戴首飾、騎馬都覺得是對自己的放縱及對宗教的不恭。這些描述使一位18歲的年輕女子顯得荒唐可笑。經過了第一次婚姻失敗后,她認清感情,嫁給了年輕的威爾,雖然沒有實現(xiàn)照顧彌爾頓、休謨等大師級人物的夢想,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輔佐了丈夫從事政治,為人類福祉兢兢業(yè)業(yè)。而卡蘇朋的悲劇更具諷刺意味,他一生埋頭苦干,立志完成神話索引,但后來被證明重復且無用,使多年的投入顯得悲涼可笑。利德蓋特為了妻子兒女放棄夢想,養(yǎng)家糊口,英年早逝。布魯克先生信誓旦旦參加議員競選,卻被人扔雞蛋起哄,狼狽不堪。這些人物沒有經歷轟轟烈烈的傳奇,沒有機會參與決定民族未來的戰(zhàn)爭,也沒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浪漫。他們有各自的夢想,但也都是局限在外省小鎮(zhèn)的空間之中。在殘酷的現(xiàn)實遭遇中,夢想或淪為每日的柴米油鹽,或成為心中隱隱之痛。這些小人物的經歷在作者的全知視角下顯得狹隘和平庸,但卻構成了真實的人生體驗。
其次是人物心理之細微復雜。外省人活動區(qū)域小,與周圍鄰里相互熟悉,交往過程中的心理活動會更復雜。小說中的人物心理描寫堪稱英國文學史上的航標,勞倫斯曾指出,艾略特“首先將所有行動內化”(Ford,1955:182)。艾略特通過心理勾畫描寫了人物的幼稚無知、單純執(zhí)著、懵懂冒進,如多羅西亞、利德蓋特和弗萊德;表現(xiàn)了人物的冷酷、自私、多疑,如卡蘇朋、費勒斯通和布爾斯特羅德;刻畫了人物的誠實、善良、溫柔,如瑪麗和菲厄布拉澤;也再現(xiàn)了人物的虛榮、淺薄和世故,如羅莎蒙德和文西太太。艾略特不僅刻畫人物的典型心理特征,還擅長表現(xiàn)心理刻畫的立體性和多元性。卡蘇朋自私、冷酷、多疑,但他對婚姻的憧憬和對多羅西亞最初的欣賞和喜愛并非偽裝。多羅西亞最初幼稚、單純、無知,婚后體認到了丈夫的可悲、刻板和無奈后還盡可能地包容、關心、愛護他。利德蓋特雖愿為醫(yī)療改革奉獻一生,表現(xiàn)出正直、誠懇、激進,但他也曾為了實現(xiàn)理想不惜犧牲朋友的利益。精細的心理描寫支撐起一個個豐滿的人物形象,這些心理的盤根錯節(jié)構成了大千世界最堅實的社會網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坐標,但又倏忽萬變。與狄更斯式的外部世界跌宕起伏、引人入勝相比,艾略特成熟的心理描寫與社會背景相得益彰,被伍爾夫(Woolf,1966:183)贊為“為數不多的為成人寫的小說”。
再次,作者精心設計了很多微不足道的外省小人物,略施筆墨便使這些人物個性凸顯。菲厄布拉澤的姨媽便是其中之一,作者對這位諾布爾小姐的描述只有三次,每次不足百字,但她與拉迪斯拉夫先生的真摯友情、兩人挽著手在街上走過的快樂身影、海貍叫似的嗓音、永遠不離身、為窮人裝面包的小籃子都成了她的獨特符號。對微不足道小人物的觀察和書寫體現(xiàn)了艾略特對小人物的深切感情和對非英雄歷史主體的體認。其他角色的精心配置還包括自私、吝嗇、衰老、多疑的費勒斯通、意外繼承產業(yè)的冰冷傲慢的李格等。這些鄉(xiāng)下小人物或展現(xiàn)個性魅力,散發(fā)人性光芒,或展現(xiàn)人性丑陋,為世界的紛繁復雜增添音符,構成真實、立體的現(xiàn)實世界。
評論界普遍認為,與早期作品相比,《米德爾馬契》的人物刻畫與敘述方式都更加成熟(ibid.)。艾略特提倡文學的道德教化作用,希望文學作品延展讀者的同情心,加深對人性的理解。因此,作家的道德立場、情感作用和主觀認識與再現(xiàn)的客觀世界之間處于時時妥協(xié)狀態(tài),經常會產生有意回避某些問題或過于強化某些問題的現(xiàn)象,造成文本想象與現(xiàn)實真實的錯位。
艾略特(Eliot,1990:111)認為,某些政治經濟學理論過于機械化地強調經濟在社會生活中的主導作用,而人類的情感狀況才是人類交往中最重要的因素。從文本表面看來,作家花費大量筆墨描述多羅西亞的兩次婚姻與她個人的選擇動機,一是與清教殉道者的教義有關,二是與真實情感有關,與經濟基礎無礙。但事實并非如此,首先,第一次婚姻的不幸與經濟密切相關。雖然他們并沒有得到婚前設想的幸福,但多羅西亞還是尊重卡蘇朋,堅守做妻子的責任。而卡蘇朋在遺囑中以有條件繼承財產的方式對多羅西亞進行限制,防止她與威爾結合。這樣的經濟手段對多羅西亞的名譽是一種侮辱,因此多羅西亞也不再留戀與前夫的感情。其次,第二次婚姻的幸福與經濟的關系也不可割舍。多羅西亞和威爾的婚姻生活是有基本經濟保障的。雖然沒有了卡蘇朋的大筆遺產,她還享有父母留下的每年七百鎊,足以維持基本家庭開支。她的兒子是布魯克先生的繼承人,每年會有三千英鎊收入。以威爾的才華和熱情自然也可以賺錢養(yǎng)家。作品對經濟收入只是簡單提及,表現(xiàn)得無關緊要,而大部分篇幅都用來描繪作者認為重要的人物心理動機、宗教、社會風俗等現(xiàn)實狀況。但對一位普通人來說,經濟保障是生存、保持尊嚴、追求自我的基本因素之一。艾略特將多數人物設置于通過勤勞努力即可溫飽無憂的狀態(tài),將政治經濟學問題被排除在外。
四、外省人構筑的英格蘭共同體
艾略特的文學作品,尤其是表現(xiàn)英格蘭鄉(xiāng)村田園生活的幾部作品,如《亞當·貝得》、《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和《織工馬南》被認為是英國文學史上的經典,描述的鄉(xiāng)村(蘭姆郡、圣奧格、拉維羅)與哈代的威塞克斯一起構成了英格蘭特性(Englishness)的現(xiàn)實空間,生活其中的鄉(xiāng)村民眾也成了代表人物。威廉斯(2013:239)曾評論道:“根據任何標準看,這些民眾都不是記錄或研究或關注的對象,但他們卻是地地道道我們自己的家人”,而艾略特的獨特之處在于她“是第一個使這一問題變得明顯的重要小說家”。她通過“精心挑選的視角精心挑選出來的社會”,為讀者建構了一個“可知社群”(威廉斯,2013:249)。作為艾略特的成熟作品,《米德爾馬契》以更全面、復雜的外省平民生活場景豐富了英格蘭共同體及其價值體系。
熱爾韋在《文學英格蘭:現(xiàn)代作品中“英格蘭特性”的不同版本》中稱艾略特作為華茲華斯的追隨者正面描繪了英格蘭理想化的田園畫卷,將深植于作者自己經歷的故事與具有高度文學性的英格蘭相結合,作品中呈現(xiàn)出社會歷史和故事在情感上不相容的狀態(tài),她的小說充滿了有意識的懷舊情緒,筆下的鄉(xiāng)村生活既甜美香醇又具體而微妙(Gervais,1993)。《米德爾馬契》少了奶酪的香甜和藍天碧野的淳樸,以更嫻熟的筆墨描繪了人性價值和更錯綜復雜的英格蘭共同體。
殷企平(2013)認為,狄更斯曾塑造了波德斯納普及由寄生蟲和假朋友所組成的偽共同體。而約翰領銜的共同體成員,像麗齊和珍妮這樣的小人物,被排除在波德斯納普等人的共同體之外及當時的官方話語之外,屬于“漏洞與邊角里的英格蘭”。通過這一作品,狄更斯向世人傳達了任何共同體的建構都不能忘記生活在漏洞和邊角里的共同朋友。與狄更斯注重描寫人物行為、社會環(huán)境等外在特征不同,艾略特傾向于剖析普通鄉(xiāng)下人的行為動機和心理特征,一定程度上豐富了共同體的主體內涵。
艾略特(1984:190)曾在《亞當·貝德》中闡述了這些鄉(xiāng)下人在文學中存在的事實和意義:“不要強加給我們任何美學的條條框框,從藝術領域中,排斥掉那些用粗活磨損了的手擦洗著紅蘿卜的老婦人,那些在暗黑的小酒店里休息的粗苯的鄉(xiāng)下人,那些俯在鐵鍬上,干人間粗活的圓寬的背和風吹雨打的遲鈍的臉……世界上有這么多普通的粗俗的人,他們沒有詩情畫意、多愁善感的苦惱!……世界上沒有幾個先知、英雄和絕色美人,我不能把我全部的愛戴與崇敬都獻給這些罕見的人物,我要把大量的這種感情交付給平平常常的人類同胞……詩情的流浪漢和浪漫氣息的罪人,也沒有普通勞動人民一半那么常見……”
19世紀中葉英國共同體的內涵通過知識分子的多元闡釋得到豐富。狄更斯通過精彩的故事情節(jié)揭露日不落帝國的陰影,但也通過改良思想給予人們希望。卡萊爾激情四射地批駁社會現(xiàn)金聯(lián)結的極端實用主義,呼喚歷史英雄的出現(xiàn)。阿諾德用“我們處于兩個世界之間,舊世界已經死去,而新世界卻無力誕生,我的心無處依靠”這一經典詩句來表達惆悵和憂慮。艾略特沒有大聲呼喚英雄從天而降,沒有在大都市紛擾復雜之中駐足,沒有吶喊自己的苦楚,轉而關注普通民眾,描寫幾十年前外省小人物在歷史變遷中平庸和微不足道的傳統(tǒng)繼承和日常行為,為讀者塑造了人類綿延相傳中最容易被忽視的英國鄉(xiāng)村日常生活與情感體驗的主體人物。盧卡奇(2013:59)曾說:“史詩中的英雄絕不是一個個人……史詩的對象并不是個人的命運,而是共同體的命運。”艾略特在《米德爾馬契》中建構了一曲外省平民生活史詩,他們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英雄,沒有創(chuàng)建英雄偉業(yè),但他們相互關聯(lián)成一個有機共同體,推動歷史前行。
工業(yè)革命、民主改革、城市化給維多利亞社會帶來了一系列變革。維多利亞時期的普通讀者經歷了印刷業(yè)發(fā)展、圖書館普及和報刊小說連載形式市場化。借助這些渠道小說得以廣為流傳,讀者獲得共同身份認同,確定了社會歷史主體的精神基石。雖然社會巨變造成了心理落差和彷徨,但鄉(xiāng)村的普通民眾在傳統(tǒng)傳承過程中為英國民族共同體提供了賴以存在的基石,即社會前進的基礎物質條件和隱于日常小事之中的認同感和可依賴性。小說為讀者提供了消遣娛樂、社會鏡像和不同的社會體驗,這些都有利于小說理念的傳播、作者觀念的傳遞及民族文化共同體的構筑。
英國沒有像美國那樣的成文憲法和業(yè)已成型的民族意識形態(tài),“直到19世紀末才形成一種具有共識的民族性”(Kumar,2003:17)。英國主島分成幾個民族,也各有自己的政治文化差異,但英國人已經習慣于這種差異性和求同存異的英國民族特征(Parrinder,2006:1)。英國的民主憲政、宗教寬容和多元價值觀念的發(fā)展都為19世紀開始形成的多聲部民族共同體提供了必要準備。艾略特身處其中,既傳承了傳統(tǒng)英國文化和浪漫主義情懷,也滿懷對現(xiàn)代社會變異的憂慮,但是她拒絕像羅斯金那樣將社會碎片化,而是極力維持道德、公益和傳統(tǒng)美德,力圖維系民族共同體的大廈。雖則文本的批判性或碎片化等負面情感具有深刻的揭示意義,但艾略特既了解生活的苦難(在雜文和信件中經常表達出對人生精神和身體苦楚、社會矛盾和無奈的敏感,甚至在雜文中用犀利的筆觸予以揭示和批判,如《法國的女性》、《德國生活的自然史》和《愚蠢的女小說家》等),又充滿智慧,在小說中面對普通讀者,用虛構與真實重塑一個文本世界來想象英格蘭共同體。這是個充滿矛盾和沖突卻終能給人希望和溫情的透明的“可知社群”。
五、結語
艾略特的小說以主流意識形態(tài)為核心建構民族共同體,抵抗社會現(xiàn)代性碎片化解構傾向,是她豪邁、睿智和強烈的知識分子責任感的體現(xiàn)。她的作品并非集中表現(xiàn)中產階級文化與自身的局限性,她的文學表現(xiàn)不能用階級單一概念來框定。艾略特通過這部作品,運用理性的現(xiàn)實感和感性的同情心向世人揭示19世紀上半葉普通外省民眾的平庸、理想破滅、忍受生活、享受關愛、默默無聞。他們是非英雄人物,但卻承載了英格蘭文化傳統(tǒng),凝聚了民族意識。他們是歷史發(fā)展的主體,書寫了真正的民族歷史。通過文本對“外省人”意象的建構,艾略特強調民族共同體的建構離不開默默無聞的外省小人物。
[1] Eliot, G. 1994. Middlemarch[M]. London: Penguin Popular Classics.
[2] Eliot, G. 1990. The Natural History of German Life[A]. In A. Byatt & N. Warren (eds.) George Eliot: Selected Essays, Poems and Other Writings[C].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3] Ford, G. 1955. Dickens and His Readers: Aspects of Novel Criticism Since 1836[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 Gervais, D. 1993. Literary Englands: Versions of “Englishness” in Modern Writing[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 Graver, S. 1984. George Eliot and Community[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6] Kumar, K. 2003. The Making of English National Identit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 Livesey, R. 2013. Class[A]. In M. Harris (ed.) George Eliot in Context[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 Miller, J. 1974. Narrative in History[J].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41): 455-473.
[9] Parrinder, P. 2006. Nation and Novel: The English Novel from its origin to the Present Da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0] 艾瑞克·霍布斯鮑姆. 2014.資本的時代:1848-1875 [M].張曉華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
[11] 彼得·蓋伊. 2006.歷史學家的三堂小說課[M].劉森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2] 高曉玲. 2008.情感也是一種知識[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13] 雷蒙·威廉斯. 2013.鄉(xiāng)村與城市[M].韓子滿,劉戈,徐珊珊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14] 盧卡奇. 2013.小說理論[M].燕宏遠,李懷濤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15] 喬治·艾略特. 1984.亞當·貝德[M].周定之譯.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6] 喬治·艾略特. 1987.米德爾馬契[M].項星耀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7] 殷企平. 2013.朋友意象與共同體形塑[J].外國文學研究, (4): 41-49.
[18] 殷企平. 2009.推敲“進步”話語[M].北京:商務印書館.
[19] 王海萌. 2012.建構文化[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