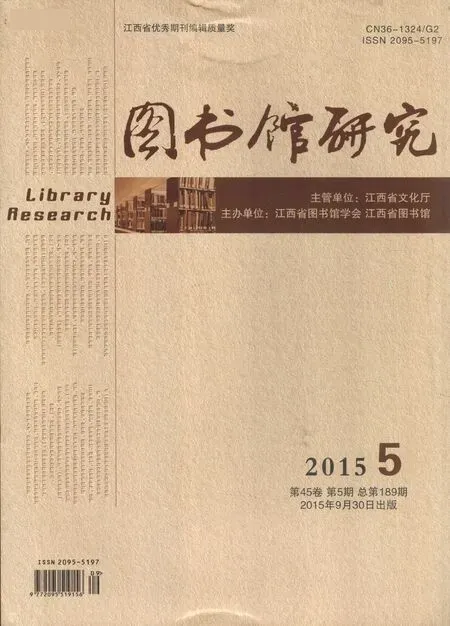基于“公共空間”視角對中國圖書館發展的探究
郭平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北京 1 0 0875)
1 “公共空間”在中國近代的興起
中國近代是一個由舊世界向新世界過渡并經歷了數千年未有之過的大變局的時代。它從晚清政府到北洋軍政府,一直控制能力都比較弱。政府衰弱,再加之這時政黨勢力還未發育起來,就使得介于個人、家庭和國家之間的自主性社會領域有了向上發展的空間。這時鴉片戰爭、甲午戰爭、馬關條約等的一系列國恥的刺激之下,使得以康有為、梁啟超和譚嗣同等為代表的新型士大夫與知識分子士人企圖借助學堂、報紙和學會等所發揮的社會影響,重新擔當起救亡圖存的使命。這些具有自覺自發的愛國意識和批判精神的仁人志士聚集在一起,面對面地相互交流,以對話、討論、閱讀、思考、集會、演說,甚至是戲劇演出的形式,表達著對于時政的關注、國家的關懷和現實社會不合理秩序的批判。在這一過程當中,他們出于一種自覺意識,自發地聚集在一起,這種自覺自發是源于國破家亡的危機感和迫切改革的現實感,是由強烈的政治意愿作為相互搭建公共交往與公共輿論平臺的橋梁。這就使得中國近代的公共領域(公共空間)一開始就不自覺的帶了鮮明的政治色彩。
哈貝馬斯所構建歐洲式的公共領域是與資產階級和市民社會等密切相關的,是在具備了資產階級與市民社會等土壤的條件下才產生的,并且經歷了從文學領域向政治領域的過渡。中國近代的公共領域則由于其特殊的國情與歷史環境,從一開始就由傳統的士大夫與新型知識分子為挑大梁搭臺以及吶喊助威推動的,作為公共領域重要標志的政論性報刊卻借助晚清帝國內憂外患的危機率先亮相登場。從1895年的公車上書到1898年的戊戌維新,由這些新型士大夫所組成的維新派利用報刊(比如《時務報》《國聞報》等)、學會(如強學會、南學會等)公開議論國是和對社會變革進行呼吁,使得中國近代公共領域內的第一次高潮形成。
在實際上由報刊、學會等推動所形成的第一次公共領域的高潮,也并非全是新鮮血液注入的結果,在其背后往往能看到中國傳統的影子。在中國近代以前,中國就已經有類似的公共交往與公共輿論網絡。從東漢時候的以太學和以地方大名士為中心的士大夫交往網絡,到明朝時的東林黨人及其組織東林書院與復社等以及當時的邸報所織成的士大夫公共交往與公共輿論網絡,就是中國傳統上的公共領域。再加之晚明時期黃宗羲設想把“學校”作為“獨立于皇權和官僚的公眾輿論機構,是‘天下是非’的仲裁之地”[1]15的思想,使得中國近代公共領域(公共空間)的思想更有受先天影響的可能。因而可以說,公共空間或公共領域盡管為外來概念,但并不是說中國在國門未開之前就沒有這些事物。只是正如雷頤所說:“在傳統中國,公共空間畢竟非常有限,更不‘自覺’”[2]。例如在傳統的中國,如此大的一個國家,有的是出名的私人藏書樓(閣)或宏大的皇家館藏等,卻很難找到一家帶有公共性的圖書館。但是也存在公共空間,比如街頭巷尾、集市廟會和茶樓酒肆等,這種公共空間并不像現在人們通常所說的公園、公共圖書館、博物館等。
從傳統上的公共空間(公共領域)到近代的公共領域(空間)的興起是需要一過程過渡的,近代意義上公共空間的萌芽階段則充當了二者不可或缺的過渡環節。中國近代由康有為、梁啟超等所掀起的第一次公共領域高潮,盡管有晚明遺產的存在,但是它也需要一個串聯環節。到了“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龔自珍和魏源出于對當時中國政治積弊的亟待改革以及對民眾生存的熱切關注,發出了尊重個性與平等的微弱呼聲,這一帶有鮮明公共性色彩的呼聲成為近代價值觀念一以貫之的主題,并成為公共空間形成的主要推動力”[3]。盡管這一呼聲具有很大的時代局限性,但是“他們建構新的政治文化(公共空間)的努力以及他們的理論探索卻不自覺地促進了洋務運動時期的文化轉型為戊戌維新時期中國公共空間的初步生成做了必要的理論鋪墊。”[3]因而正是在這個推動力的串聯下,晚清的第一次公共領域高潮與晚明傳統的公共領域遺產得以銜接。
中國近代公共領域是在國家面臨內憂外患的特殊環境下,移植傳統遺產基礎上所產生并且發展起來的,所以它一產生就帶有了先天的歷史獨特性與后天的環境現實性。這就使得其在產生之后能夠繼續沿著這條中國特色式的公共領域道路毅然前行,對中國近代后來的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等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
2 圖書館與“公共空間”的“結緣”與“失落”
筆者這里的“結緣”是指圖書館為何屬于公共空間,圖書館在中國何時發展成為公共空間;“失落”是指圖書館這一公共空間為何又往往被忽略。
從哈貝馬斯、許紀霖(前面一節已有論述)、查爾斯·泰勒[1]19以及同濟大學趙民教授[4]等人對于”公共空間“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不管從側重于政治的角度來講,還是從建筑學的角度講,圖書館都屬于公共空間的范疇。在中國近代的圖書館里,也像大學一樣聚集著中國的大批精英人士,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并且不自覺地進行一種自我邊緣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的同時,他們也組成一個以某一紐帶為基礎的公共交往的空間網絡。從這些來看,圖書館也應該歸屬于許紀霖先生所說的公共領域,是一稍不同于哈貝馬斯所認為的那種“從市民社會中產生的、在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具有鮮明政治批判功能的,所產生的是社會公共輿論,并以此成為政治合法性的淵源的公共空間”[5],而是指在“社會與國家之間實現社會交往和文化互動的場所,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所建構和賴以生存的都市空間”[5]。但是由于圖書館沒有大學、報刊和社團等那么在政治領域凸顯,所以往往不引人注意,被人給忽略。在中國近代公共空間產生的時候,已經有救國救民志向的中國知識分子開始關注并考察西方的圖書館事業的發展。他們除了通過翻譯書報來擴充見聞,還身體力行,走出國門,進行實地考察,用自己所見所聞來介紹傳播有關西方圖書館的知識。如被稱為中國近代“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則徐,在他所翻譯和編著的《四洲志》中,對西方一些國家的圖書館有過較為詳盡的介紹,尤其是對于美國圖書館。這向國人較早地呈現出不同于私人藏書樓和官府皇家館藏等的帶有 “公共性”的西方式圖書館的情況。隨后魏源在《海國圖志》中也有對西方多國圖書館的較為詳細介紹,并提出:“西方的學校、新聞紙和圖書館等也是長技,同樣應該學習”[6]。這使得當時中國知識分子開闊了視野,注意到了不同于中國傳統藏書樓式的西方圖書館的存在,并且也關注到其對社會發展的推動意義。到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后,一部分中國進步人士已開始把目光轉向國外,身體力行走到歐美等西方先進國家去尋找救國良藥。同治六年(1867年)王韜參觀英國大英博物院圖書館時并記述到:“男女觀書者日有百數十人,晨入暮歸,書任檢讀,惟不令攜去。”[7]102后其又在倫敦地區圖書館參觀時,記述到:“都中藏書之庫林立,咸許人入而覽觀。……都中人士,無論貧富,入而披覽誦讀者,日有數百人。然只許在其中翻閱,不得攜一卷一篇外出,其例綦嚴。”[7]113從王韜當年的記述中也可以看出,中國人已經不滿足于私人或官家獨占的藏書樓或官家藏書,開始向往帶有公共性的西式圖書館了。那時期除了王韜對此有過這方面的論述外,李圭、志剛、郭嵩燾、薛福成和張德彝等也在國外參觀圖書館時,也有過類似于王韜的記述。中國人除了已經開始考察西方圖書館事業外,一些人已經在中國開始傳播西方圖書館的理念,如光緒十八年(1892年)鄭觀應就曾著文論西方圖書事業并宣揚其理念,“泰西各國均有藏書院、博物院,而英國之書藉尤多,自漢唐以來,無所不備。凡本國有新刊之書,例以二份送院收儲。如有益于國計民生者,必膺朝廷重賞,并給予獨刊之權若干年。咸豐四年(1854年)間,于院中筑一大廈,名曰:讀書堂,可容三百人,中設幾案筆墨。有志讀書者先向本地紳士領有憑單,開列姓名、住址,持送院中董事,換給執照,準其入院觀書,限六閱月更換一次。······倘有損失,責令賠償。特設總管一員,司理其事,執事數百人。每年經費三十萬金。”[8]“果能認真經理,數十年后,賢哲誕生,兼文武之資,務將相之略;或鉤元摘秘,著古今未有之奇書,或達化窮神,造中外所無之利器,以范圍天地,籠罩華夷,開一統之宏觀,復三王之舊制。”[9]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李端棻曾上折論述西方圖書館相關理念,“……泰西諸國頗得此法,都會之地皆有藏書,其尤富者至千萬卷,許人入觀,成學之眾,亦由于此。”[8]從這些可以看出,西方公共圖書館的思想理念在中國近代第一次公共領域掀起前及掀起時,就已經在中國開始傳播,并把興辦西式圖書館提高到富國強兵的高度,再加上西方傳教士早已在中國開辦了圖書館,這使得中國近代第一次公共領域高潮起來后,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人士有了對西式圖書館這一個公共空間(公共領域)的借鑒與應用的理念與實體模式。
這一時期,標志著中國近代公共領域第一次高潮的戊戌維新運動,在借助學會、報刊等作為公共交往與公共輿論的工具的同時,并沒有忽視圖書館這一公共空間。他們不僅在思想理念上認識到了西式圖書館對于啟迪民智、培養人才和促進改革等的作用,并作了相應的闡述。如康有為在1895年的《公車上書》當中就提出的“教民之法”中就包括成立圖書館,這為其第一次向清政府提出“設藏書”的建議。梁啟超在1896年曾著文以藏書備覽為學會要務之一,“今欲振中國,在廣人才,欲廣人才,在興學會。諸學分會,未能驟立,則先設總會。 設會之目,·······七曰咨取官局群籍,概題全份,以備儲藏。八曰盡購已翻西書,收庋會中,以便借讀。九曰擇購西文各書,分門別類,以資翻譯。十曰廣翻地球各報,散布行省,以新耳目。十一曰精搜中外地圖,懸張會堂,以備流覽。十二曰大陳各種儀器,開博物院,以助試驗。十三曰編纂有用書籍,廣印廉售,以啟風氣。十四曰嚴定會友功課,各執專門,以勵實學。”[10]從中可以看出康梁二人對于圖書館事業的重視,尤其是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一書中,把‘開大圖書館’作為強學會的五件大事之一”[11],還身體力行參與了大量的圖書館工作,直到其臨終前。
“據統計,戊戌維新運動時期,維新派在北京、上海、長沙等全國各地共建立學會87個,學堂131所,報館91家。”[12]“其中設立藏書樓的達51所。”[13]這些學會、學堂和報館等大多注重廣購圖書儀器和設立藏書樓。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上海強學會制定章程規定:“今設此會,聚天下之圖書器物,集天下之心思耳目,略仿古者學校之規及各家專門之法,以廣見聞而開風氣,上以廣先圣孔子之教,下以成國家有用之才。最要者四事,條例于下,其局章附焉:(一)譯印圖書 (略),二刊布報紙(略),(三)開大書藏:……今合中國四庫圖書,購抄一份,而先搜其經世有用者。西人政教及各種學術圖書,皆旁搜購采,以廣考鏡而備研求。其各省書局之書,皆存局代售。(四)、開博物院(略)。”[8]100-101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金陵開勸學會,曾記述道:“蓋以閣地寬敞,可容百余人團坐觀書之故。又因此舉志在勸學而起,故名之曰勸學會。”[8]103作為戊戌維新運動重要成果之一的京師大學堂在其章程中則寫道:“京師大學堂為各省表率,體制尤當崇閎,今設一大藏書樓,廣集中西要集,以供士林瀏覽而廣天下風氣。”[8]106從上面這些學會、學堂和藏書樓的設立宗旨和購書目的等可以看出,盡管這時期的這些不成形的圖書館還不夠正規,但有的已經開始向公眾開放,讀者對象不再是限定的少數人,而是一般知識分子和部分市民,顯示出其公共性。同時有些藏書樓如蘇學會的“看書七條”,制定出了相應的較為完備的關于圖書的購置、分類、編目、流通、借閱以及賠償等各個環節的具體規定[8]101-103。因此“這時期的部分藏書樓具備了近代圖書館突出的社會教育的功能和服務于讀者的開放性特點。”[14]從近代圖書館的歷程來看,它是中國近代公共領域的第一次高潮中的參與者與經歷者,是與中國近代的公共領域相伴而生的。
“圖書館不僅僅是存放書籍和閱讀的地方,它還是學習和社交的場所。”[15]其作為一種對于承載知識信息的書籍的儲藏與傳播場所、一個讀者跟作者進行交相互動的平臺,承載知識的圖書只有被閱讀才可體現其價值,才能讓使其被人所了解與認可,正是圖書館使得以往封閉性的讀者圈走向了開放,這本身就是民主的體現與詮釋;另外也在傳播著關于啟蒙、自由、民主、博愛和共和等方面的思想理念和增進人們獲取財富能力、社會交往、提高個人修養以及充實人生等各方面的知識,使得一些涉及公眾性的公共問題能夠被盡可能多的大眾所理性的了解,并被拿到公眾當中去進行討論。這樣在圖書館知識的海洋里,逐漸地形成一個有文化的公民群體。“一個有文化的公民群體的發展壯大,導致了對知識的渴求、刺激了新書的創作、出版和發行,這些書又反過來宣揚了國民識字的理念以及國民獲取知識的權力”[16]104。在中國近代史許多的著名學者如陳垣、魯迅、老舍、曹禺、吳晗和姚雪垠等,革命家李大釗、毛澤東等都從圖書館獲益甚多,跟圖書館結下了不解之緣。這些人又對中國社會的發展產生過重要影響。“圖書館對于使那些無力擁有書籍的人能夠看到書,起了很關鍵的作用。”[16]172這些對中國近代發展產生過重要影響的人正是得益于圖書館普遍與均等的公共性追求。這些圖書館的出現與增長也正是建立在人們對于知識的渴求與書籍的旺盛需求之上。在這種共享平臺上會通過相同的興趣與喜好以及理性討論、求同存異所達成的共識而自然地形成所謂的公眾意見,“公眾意見一旦形成,便極為強大,因為贊成者眾多;其能量也驚人,因為決定它的動因會影響到所有的人,哪怕是千萬里之外的人”[17]。所以圖書館有利于推動個人的提升、國家的變革和社會的整體進步。
圖書館,從其在中國近代的產生發展歷程與所起到的實際功效來看,它應該是公共空間(公共領域)的一部分。但是在學術界提到的公共空間(公共領域)往往是報刊、報社、雜志社、大學、學會、社團和街道以及茶館等,圖書館被作為公共空間的不多見。這一方面與圖書館在中國近代并不像報刊、學會和社團以及大學等公共空間(公共領域)那樣在社會運動浪潮中沖鋒陷陣,保持著其一貫的隱忍有關;另一方面圖書館在中國近代也并不像街道、茶館和戲院等公共空間(公共領域)那么自由和大眾化,所以人們對圖書館的公共空間屬性的關注就遠遜于街道、茶館和戲院等公共空間。另外再加上當前電子媒體和讀物等的普遍增加,使得近年來的圖書館讀者數量有下降的趨勢,書店和書商也在謀求轉型,這就造成了一些地方政府對公共圖書館服務的支持力度下降,這種趨勢很容易造成公共圖書館事業發展的惡性循環,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人們對于圖書館這一公共空間的關注程度降低。
3 圖書館應如何在新時代承擔起作為公共空間所應有的責任
圖書館,作為知識的倉庫和思想的寶藏,人們學習和提升的平臺,也是公眾吸取滋養和達成共識的公共空間。因此,“國家可能需要越來越多地介入,以促進和保護書籍的閱讀,就像它為被視為公民社會中的積極資產的其他活動所做的那樣”[16]211。除國家以外,個人和社會也應該積極參與到促進圖書館事業的發展當中來,進而推動圖書館這個公共空間(公共領域)在新時代下承擔起其所應承擔的責任。
首先,圖書館的公共空間(公共領域)的屬性,決定了圖書館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投資。國家政府應基于圖書館在保存文獻典籍、傳播科學文化和啟迪大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可以借鑒歐美各國的以國家資本扶持圖書館并與時俱進的改進資本融入圖書館事業的方式,以幫助圖書館事業應對當前所面臨的挑戰以及發展的瓶頸。
其次,圖書館自身應加強其綜合能力,以便適應時代發展的需求。由于在知識經濟與網絡化飛速發展的信息時代,圖書館事業一方面在“緩慢的跟進過程中,圖書館價值趨于迷失”[18]11和圖書館服務偏離了其均等和普遍宗旨,因此在一些地方產生對圖書館事業發展重視不夠、經費撥付不足、讀者滿意度下降和圖書館工作者流失等一系列問題;另一方面,一些地方的圖書館在發展的過程當中,“存在著自輕和他輕現象,一些館員因圖書館社會地位不高、收入菲薄而離職時有發生”[18]12。即使是不離職,工作人員的這種不良思想情緒也會影響他們的工作狀態,從而在不經意間影響圖書館的服務和工作效率,造成圖書館工作績效和服務的下降,從而引起圖書館整體有效運行的不佳和讀者的不滿意等。這使得國家對于圖書館事業除了在加大資本投入與改進投資方式以外,還需要盡快清晰對于圖書館的職責定位及達成其核心價值的共識,并在圖書館的管理和服務過程當中把普遍、均等等公共性真正融入進去,使圖書館管理者和工作人員能夠切實履行與堅持圖書館服務社會的公共性。并在資本投入過程的同時,適當考慮提高圖書館工作人員的待遇以及其福利水平,進而相應地提高其服務水平和工作效率,樹立工作人員以人為本的工作服務理念,全方位和多角度地把“讀者第一,服務至上”的圖書館口號從形式到內容融入工作實踐當中。還需要建立相應的圖書館職業道德制度、服務規范體系、工作績效考核機制、圖書館互動交流網絡和服務檢查監督制度以及面向社會的公共服務評價系統等,以便更好地體現其核心價值和宗旨,為社會服務,為讀者服務。
再次,圖書館服務于社會公眾的宗旨決定了其良好運行是離不開社會公眾的大力支持的。圖書館是“保證社會成員獲取信息機會的平等,保障公民求知的自由與權力的制度安排”[18]548。公眾就應該對圖書館給予適度的關注,并考慮自己在參與圖書館活動的過程當中應該如何扮演好自己的公共人角色,如何與圖書館閱讀環境這個氛圍相協調。也就是公眾一方面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給予圖書館這種公共空間(公共領域)應有的贊助與支持,可以是物質方面的捐助,也可以是自覺的宣傳;另一反面公眾應該提前適當充實與豐富圖書館相關方面的常識,培養起自己良好的文明習慣:遵守公共秩序、愛護圖書館器物、珍愛圖書資料、不大聲喧嘩與吃食、不亂扔垃圾等。同時,公眾也應該在接受圖書館的公共服務時保持與圖書館的持續良性互動,對他們的工作服務和事業的發展給予寶貴的建議和應有的支持。
第四,學術界應該加大對于圖書館這一公共空間(公共領域)的關注,尤其是除圖書館學以外的學科,如歷史學、社會學、管理學、建筑空間學和政治學等,也應該多關注圖書館這一公共空間。“作為文化公共空間的圖書館除了物理條件之外,更是人們進行精神交流的公共場所,它應該為人們提供科學合理、高效便捷、舒適清新的公共空間環境,滿足人們生理和心理的需求,創造符合人們進行各種社會生活行為所需的空間環境,并保障人們的安全、無障礙,有利于人們的身心健康以及精神上的舒適度,為讀者用戶提供一個更人性化的服務。”[19]“圖書館是公共知識空間的一種重要形式,它不僅承擔了公共空間的永恒意義和價值,同時與其他公共知識空間形式(如學校、博物館等)有著不同的特質。”[20]“公共圖書館最能夠促進社會包容的功能在于圖書館作為一個公共空間的價值。”[21]從上面的這些觀點可以看出,具有公共性的圖書館是一個伴隨著中國歷史進程而誕生并將繼續伴隨歷史浪潮而前進,可以共享、共融、眾議和醞釀民主制度的空間,因此這就需要學術界不僅僅把其看作只是圖書館學所涵蓋的內容,它對于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建筑空間學和管理學等都是具有重要研究價值的。只有通過多學科、全方位的對其進行探討研究,才能使圖書館更為全面的展現出它“真實”的一面,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出其公共空間效用。
著名的圖書館學家魯夫斯曾說:“一本書,只不過是一本書,而一所圖書館卻是人類文化進步的重心”[22]。圖書館是現代化文明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其不僅是儲藏知識與傳播知識的場所,還是為國家、社會和公眾提供相關各方面信息的信息中心。在這樣一個信息化的時代里,獲取信息的能力凸顯得更為重要,“一個人獲取知識信息的多寡決定其生存地位和社會地位”[23],獲取信息的能力成為人們謀生存和求發展的必需手段與途徑,人們只有先通過滿足了最起碼的生存和發展的權利以后,才能為更好地實行民主權利、實現自身價值創造條件。因此具有普惠和均等公共性特點的圖書館就應該被重視起來,尤其是其因普及知識、啟迪民智和施惠大眾的特性而使得其成了“‘民主與自由社會’必要的基礎性設施,是‘民主與自由信念’的教育工具,擁有了‘圖書館是一座沒有圍墻的大學’之稱”[23]。所以,不管是學界,還是政府、社會公眾與個人,都應該把往日被忽略的圖書館這一公共空間給“抬到”它應有的位置上去,積極利用現代的信息網絡技術來武裝圖書館以便讓它發揮更大的公共效力。
[1]許紀霖.公共空間中的知識分子[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2]雷頤.近代中國的公共空間[N].經濟觀察報,2007-07-20(42).
[3]姜昱子.近代中國公共空間的生成歷程 [J].學術交流,2010(6):44-46.
[4]錢才云,周揚.空間按鏈——復合型的城市公共空間與城市交通[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10.
[5]許紀霖.啟蒙如何起死回[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6]胡俊榮.晚清知識分子創建中國近代圖書館的歷程[J].四川圖書館學報,2000(5):61-66.
[7]王韜.漫游隨錄[M].長沙:岳麓書社,1985:102-113.
[8]李希泌,張椒華.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M].北京:中華書局,1982:97-106.
[9]鄭觀應.盛世危言[M].曹岡,譯.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40.
[10]梁啟超.梁啟超全集:1[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8.
[11]李曉新.普遍·均等:中國公共圖書館的百年追求[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7:6-27.
[12]謝灼華.維新派與近代中國圖書館[J].圖書館雜志,1982(3):70-73.
[13]胡俊榮.晚清西方圖書館觀念輸入中國考[J].圖書與情報,1999(4):77.
[14]龔書鐸.中國近代文化概論[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2010:267.
[15]讓·馬里·古勒莫.圖書館之戀[M].孫圣英,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
[16]戴維·芬克爾斯坦,阿利斯泰爾·麥克利里.書史導論[M].何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104-211.
[17]羅杰·夏蒂埃.書籍的秩序[M].吳泓緲,張璐,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13-14.
[18]李洪峰.文化責任[C].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9:11-548.
[19]萬愛雯,夏海燕.關于公共圖書館公共空間發展的思考[J].農業圖書情報學刊,2012(6):128.
[20]王子舟.論歷史文化名城與圖書館[J].新世紀圖書館,2006(1):21-23.
[21]范并思,周吉.公共圖書館與社會包容[J].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10(2).70-74.
[22]蔡家園.去圖書館約會[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
[23]楊敬.圖書館里風光無限[N].中國信息報,2011-03-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