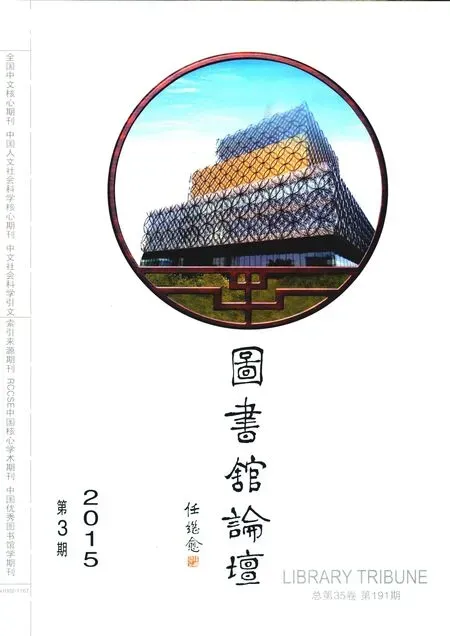風尚與渠徑:明代江南“書香門第”的構建及啟示*
王安功
風尚與渠徑:明代江南“書香門第”的構建及啟示*
王安功
在中國文化史中,具有讀書、治學、入世傳統并傳之久遠的書香門第成為一種文化符號。明代江南書香門第形成的社會氛圍有兩個方面:發達的編纂刊刻事業和普遍存在的圖書藏抄風尚,書香門第的形成以修齊治平理念為內生動力。梳理書香門第的發展經驗,使書香規避空洞的社會價值觀引導,讓書香融化功利的家庭教育的缺失。
書香門第 藏書文化 江南 明代
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中,具有詩禮傳家、文化學術內涵豐富、社會地位尊崇等特征的望族、世家憑借豐厚的讀書底蘊積淀與承繼,經歷前輩后代的共同努力,形成讀書、治學、入世的傳統并傳之久遠,是為“書香門第”。書香門第豐富的意涵使其成為一種文化符號,構成了“一個非常奇特的文化景觀”,書香家族“依靠自己家庭教育的力量,連續幾代甚至幾十代為社會培養出許多杰出的人才”[1]。這種情形在明代江南表現尤著。當時的江南人文薈萃,攜唐宋以來之文脈流韻,書香門第如雨后草原,遍地花開,用學界時髦術語言之即為“泛在”。本文從書香門第泛在的社會氛圍、內生動力等方面分析書香門第的產生發展,以期對古代藏書進路的現代轉化和當今書香門第建設提供參考,祈請方家指正。
1 明代江南“書香門第”形成的社會氛圍
1.1 文獻基礎:江南發達的編纂刊刻事業
首先,繁榮的出版業促進了圖書流通的市場化。明代江南“私家刻書十分繁盛,文化世族是其中的主力軍。文化世族成員具有強烈的家族文化傳承意識,通過刻書活動延續家族文化傳統,甚至使刻書也成為家族文化傳統的一部分,因為文化世族具有人力、財力優勢,刻書活動持續時間長、規模大”[2]。書香家族的圖書出版活動不僅豐富了書香門第所需之質料,而且對官刻有相當影響,即“公家亦聞風興起,廣延學士大夫,設局刊書,與私家事業并行不悖。各地書賈亦競翻舊籍,刊印新書,由是學者皆得人手一編,潛心考索”[3]。明代江南官營出版業在出版市場中占有重要地位,來自南京國子監、司禮監、經廠、行人司等機構的官刻本、私家刻本、坊刻本并行充盈文化市場。李伯重考察明代江南的商業出版活動后指出:明初,政治性和教化性讀物在江南出版產品中占有很高比重;中期以后,以牟利為目的、面向中下層民眾的商業化出版業日益發展,導致明代江南出版業的發展出現外向型趨勢,即生產所需的原料要依賴外地供應源,生產出來的產品(印刷品)則依賴外地市場[4]。各種圖書的市場化使民眾有機會通過購買得以共享文獻資源。
其次,發達的印刷術使高質量圖書印刷快捷化。明代江南出版業出現兩個重要的技術進步,一是活字印刷的推廣,二是彩色印刷技術的出現與改進[5]。明代藏書家胡應麟說:“活板始宋畢升,以藥泥為之,今無以藥泥為之者,惟用木稱活字云。”[6]木活字本在萬歷年間有很多,藩府、書院、書坊、私家都曾采用木活字印書。清代文獻廣泛記載了明人用木活字板印刷書籍的情況,木活字本達一百多種,流播地區極廣,蘇州、杭州、南京、福建等一帶以及四川、云南等地都有[7]。成熟的傳統雕版技藝,加上木活字印刷術的進步,令圖書質量大大提高,也使圖書印刷快捷化。
再次,豐富的出版內容滿足民眾需求的多樣化。明朝“右文成化”,出版產品的教化和宣傳功能特別濃。明初政治性和教化性讀物是江南出版業中的大宗產品,如《御制大誥》、寶訓、鑒戒等政治性書籍,及洪武《大藏》、永樂《北藏》《道藏》等宗教出版物。明代中期以后,商業化出版業興起,大量印制適銷對路的大眾讀物,包括通俗文藝作品、通俗實用讀物、童蒙課本、時文選本、年畫、日歷及祭祀用品。以坊刻書為例,大致包括有醫書、科舉、翰林院館課、八股文、小說戲曲等,囊括了民間日用參考實用書、科舉應試書、通俗文學書等類別[8]。出版物的商業性生產,使大量圖書在市場上流通,滿足了從官員、商人到普通士紳、農耕者等群體的多樣化需求。從政治出版物作主導到大眾通俗讀物的流行,編纂刊刻事業的發展豐富了書香門第建設的文獻基礎。
1.2 技術渠徑:江南普遍以圖書藏抄為風尚
就社會外部環境而言,明代江南普遍存在家族嗜書、爭相藏書之雅尚。由于江南“藏書之風氣盛,讀書之風氣亦因之而興”[9],而且這種藏書之風漸而“被及商販,刊上豪門,廣中洋賈,間亦揮霍多金,購藏典籍,開館延賓,屬以校刊。其用意雖為附庸風雅,自躋士林,然其保存傳布之功,固不可沒也”[10]。可見文人有志藏書的連鎖效應。書是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讀書人嗜書如命,并從中獲得樂趣。發達的出版業直接促進“藏書之家,插架亦因之愈富”[11]。買書、藏書、借書、抄書、讀書之人比比皆是,有些讀書人甚至如癡如瘋,構成了中國閱讀史上的動感篇章。蘇州人楊循吉成化年間曾任禮部主事,身體欠佳,但讀書成癖。《堯山堂外紀》記敘他讀至興時,常常手舞足蹈,被人稱為“顛主事”,其書室積書達十余萬卷。明代祁承爜也說:“余每遇嗜書之癖發不可遏,即取《通考》翻閱一過,亦覺快然。庶幾所謂過屠門而大嚼者乎。”[12]清代藏書家孫從添總結前代藏書之趣說:“訪于坊家,密求于冷鋪,于無心中得一最難得之書籍,不惜典衣,不顧重價,必欲得而后止。其既得之也,勝于拱璧。即覓善工裝訂,置之案頭,手燒妙香,口吃苦茶,然后開卷讀之,豈非人世間一大韻事乎?”[13]從古到今的文人與書都有著與生俱來的關系,他們讀書、買書、著書、藏書,書是陋室孤窗下心靈的慰藉,是可以傾心的伙伴,是一種生活方式,是從未失落的家園。明代常熟人楊儀喜好藏書,在他看來,藏書不是目的,不是為了裝潢門面,而是心靈的寄托。他日以讀書、著述為事,收藏之富,堪稱雅博[14]。太倉人王世貞筑“小酉館”藏書三萬卷,又建“爾雅堂”專藏宋版書,“藏經閣”專貯佛教和道教經籍。以蘇州府常熟縣為例,藏書在明代晚期蔚為風尚,一直波及清代。明末錢謙益的“絳云樓”、毛晉的“汲古閣”兩處藏書所更是知名全國,對當時及后世藏書風氣有推波助瀾的功效。《光緒重修常昭合志》卷三十二更專門設置“藏書家”類目[15],收錄元明清三代常熟縣藏書家,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常熟縣藏書社會風氣之濃郁。
從實際效用看,圖書傳抄起到了珍品備份、互通有無、豐富品種的作用。袁同禮撰文揭示:“明人好鈔書,頗重手鈔本。藏書家均手自繕錄,至老不厭。”[16]明宣宗朱瞻基時,官府藏書仍以抄本為主。據《明史·藝文志》載:“是時,秘閣貯書約二萬余部,近百萬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17]吳晗說:在明代“好學敏求之士往往跋陟千里,登門借讀,或則輾轉請托,漁錄副本,甚或節衣縮食,恣意置書,每有室如懸磬而奔書充棟者;亦有畢生以鈔誦秘籍為事,蔚成藏家者。”[18]一直以來,文人就好抄書,抄書成為讀書與學習的重要方法。楊儀亦愛好抄書,并抄出了名堂。《藏書紀要》“鈔錄”篇在介紹到明人鈔本時,“楊鈔”即是其中地位十分重要的一種[19]。所以說精心抄錄秘籍是明清以來藏書家所普遍看重的增益藏本的方式。昆山人葉盛,在英宗、憲宗時任官數十年,所到之處總是帶著抄書吏,訪書抄書,并親加校勘,藏書數萬卷,其《菉竹堂書目》盡載私藏精華,奇書秘本僅次于宮中所藏。明代大多數藏書家都曾參與抄書,且抄書的數量達到驚人的程度,從數卷以至數萬卷的都有[20]。在吳地甚至出現結社傳抄交流書籍的組織,如范欽“與吳門王鳳洲家,歲以書目取較,各鈔所未見相易”[21]。梅鼎祚“嘗與焦弱侯、馮開之,暨虞山趙元度訂約搜訪,期三年一會于金陵,各書其所得異書遺典,互相讎寫”[22]。明末浙江《寧海縣志》卷九“文籍”載:寧海人陳舜時曾專著《抄書臆見》一書[23],對抄書之法進行詳細總結。足見當時抄書熱情之高、風尚之盛。
從不斷優化的藏書環境看,形成了以藏書樓營建為代表的家族藏書樓文化。明代藏書家以“萬卷樓”命名其藏書樓者非常多,如項篤壽、豐坊、楊儀、吳自新、范欽等。這些藏書家往往“插架至富”“牙簽萬軸(圖書數量很多)”。至于蕓編(書籍)、蕓帳(書卷)、蕓閣(藏書閣)、蕓署(藏書室)、蕓香吏(校書郎)等專有名稱則頻繁出現在時人詩文集中,構成了江南藏書文化的核心詞匯。其他著名的藏書樓還有很多,如明初童伯禮“石鏡精舍”、胡萬陽“南國書院”、袁忠徹“瞻袞堂”、張瑞“甬州書莊”、范欽“天一閣”、陳朝輔“四香居”、陸寶“南軒”、余有丁“五柳莊”、朱勛“五岳軒”、朱獻臣“小五岳軒”、諸來聘“昌古齋”。這些藏書樓無不打上家族式烙印,歷時而傳承;不少藏書樓還在社會文化的變遷中重新組合,融入到醇厚的文化積淀中去。可以說,藏書樓成為明代書香門第的重要標志。
2 明代江南“書香門第”建設的內生動力
明代江南人文薈萃,崇尚書香。每個世家、望族莫不以讀書以修身,修身而科舉齊家,齊家乃求入世治國、平天下。可以說當時處處充滿著讀書上進、光耀門楣、報效國家的風氣。
2.1 普遍存在開卷修身的讀書風氣和閱讀心態
對讀書的倡導,歷代有之。究竟何書可讀,無論官私,皆有弘論。嘉靖時期黃佐撰《南雍志》大倡讀書:“孔門謂何必讀書,然后為學,則學在于讀書亦可見矣。刪述以來,天之牖民,翳書是賴,其可廢邪。”[24]無獨有偶,明末安徽學者吳與箕著《讀書止觀錄》,輯錄中國先秦以來讀書古訓和讀書掌故,尤其對明人讀書故事發明甚多。該書卷三載:“周文安嘗著《經書辨疑錄》,每曰:‘吾為此錄,發經書之蘊,正先儒之失,破千載之疑,雖三公之尊,黃閣之榮,不與易也。’讀書者當觀此。”[25]吳與箕還列舉很多身處逆境仍然苦讀書的人物,如著名政治家、“三楊”之一的楊溥,“在獄中十年,家人供食久,數絕糧,又上命叵測,日與死鄰,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事已如此,讀書何為?’答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述及此,吳與箕點評道:“古人著書讀書,每發憤于窮苦患難之際,今人平時先自廢棄,況患難時乎!若必待患難來而發憤,此其所以終身廢棄也,此其所以終世偷生也。朝聞夕死,吾深有慕于楊公。”[26]最后他指出,讀書的人應當從這里得到啟迪。于今人而言,何嘗不是如此。古人常說士必以詩書為性命,富不肯讀書,貴不肯積德,必然走向衰落。家中縱使貧寒,也必須留下讀書種子。習讀書之業,便當知讀書之樂。明代萬歷年間福建人徐孛力,其“紅雨樓”不但藏書7萬卷,而且著述頗豐。他在《筆精》“觀書三益”條中對讀書之益有很深的體會:“客來觀書,病懶時頗厭其煩。然有三益,不可以厭煩而廢:賤性善忘,經目輒忽,獨對客搜尋之事,雖閱年能記,一益也。覽所不及,庋床便蠧,因客披,二益也。習懶成病,偶因客至,整書忘疲,亦古人運甓之意,三益也。夫學求益也,一益尚可,況三益乎?”[27]他還說:“人生之樂莫過閉戶讀書,得一僻書、識一奇字、遇一異事、見一佳句,不覺踴躍,雖絲竹滿前,綺羅盈目,不足踰其快也。六一公有云:至哉天下樂,終日在幾案。余友陳履吉云:居常無事,飽暖讀古人書,即人間三島皆旨哉言也。”[28]這種讀書有益并以此作為人生一大樂事的心態,在明代非常典型,讀書問學,坦坦蕩蕩,非常值得今人學習。清代讀書人王永彬就用淺顯白話總結了前代讀書的經驗:“讀《論語·公子荊》一章,富者可以為法;讀《論語·齊景公》一章,貧者可以自興;讀書無論資性高低,但能勤學好問,凡事思一個所以然,自有義理貫通之日。……清貧,乃讀書人順境。……讀書不下苦功,妄想顯榮,豈有此理?為人全無好處,欲邀福慶,從何得來……”[29]。富延、貧興皆從書中得,正與北宋真宗“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車馬多如簇,六經勤向窗前讀”的詩句異曲同工。明代金圣嘆評點《西廂記》說:“后之人既好讀書,又好友生,則必好彼名山、大河、奇樹、妙花。名山、大河、奇樹、妙花者,其胸中所讀之萬卷之書之副本也。于讀書之時,如入名山,如泛大河,如對奇樹,如拈妙花焉。于如名山、泛大河、對奇樹、拈妙花之時,如又讀其胸中之書焉。”[30]這就是“閱讀欣賞與自然欣賞的互滲”[31],不同形式的閱讀風氣匯成了書香社會的閱讀正能量,而且“閱讀風氣的形成是一個時期政治、學術的綜合體現”,作為一種文化現象,隨著時代而變遷,“又是歷史傳統的延續與繼承”。[32]風清則氣正,良好的閱讀傳統,成為催生書香門第的重要推手。
2.2 官僚世家與文人家庭講究家學淵源的氛圍熏陶與讀書引導
關于古代的家族門風及其內在的精神動力,錢穆指出:“一個大門第,決非全賴于外在之權勢與財力,而能保泰持盈達于數百年之久;更非清虛與奢汰所能使閨門雍睦,子弟循謹,維持此門戶于不衰。”[33]的確,古代世家大族世代累積并一貫遵守了一整套“道德標準、價值準則、處事原則及期望目標,能集中體現一個家族特有的精神風貌,直接關系到家族的榮辱興衰”[34]。明代有很多讀書氛圍引導方面的典型事例,祁承爜為教育子孫繼承愛書讀書的習慣,“親手撰寫了《澹生堂藏書約》,制定了《讀書訓》《聚書訓》《購書訓》和《鑒書訓》,教育子孫如何鑒別圖書、如何購買圖書、如何收藏圖書,以及如何閱讀圖書。”[35]并對如何讀書、為什么要讀書的問題進行指導:“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便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殆為是耳。”[36]他認為要加強子女教育,并以古訓去感染他們:“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之。”[37]祁承爜還以梁朝貴族子弟腐朽的生活方式為例,勸導多讀書,讀書以致用,其言鑿鑿,如雷貫耳。他說,梁朝盛世,貴族子弟不愛讀書,把衣服薰得香香的,把臉刮得白白凈凈的,擦粉涂紅,坐長轅車,穿高跟鞋,座位上墊著軟墊子,背上靠著舒適的“斑絲隱囊”,手邊放有很多寵物。這些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文則提不動筆桿,武則耍不得刀槍,衣冠依然楚楚;但如果他們有知識,怎么會被人恥笑萬世呢?所以說積財千萬不如一技在身。
2.3 科舉入仕成為各個家族鼓勵讀書的首要目標
明代非科舉無以為官,家族要振興,躋身上流社會的主要途徑就是科第成功。這就離不開家族教育,而且科舉成功之后,延續家族社會地位的關鍵還在于教育,所以一般的家族都將家族教育的首要目標鎖定在科舉入仕。為了科舉就必須讀經,“凡讀書須識貨,方不錯用功夫。如四書五經、《性理》、《綱目》,當終身誦讀也;水利、農政、天文、兵法諸書,亦要一一尋究,得其要領。于子史百家,不過觀其大意而已。如欲一一記誦,便是玩物喪志。”“經義之外,視己才力所近,專習一事似為易造,其有才力者,自當務為全學。求放心然后可以讀書,讀書正所以求放心,蓋交相養互相發。”[38]明代大多數的“望族都遵循著‘讀書—科舉—光宗耀祖’的共同模式來規劃著家族教育”,這些家族,“除了重視科舉之外,還注重文學、史學、藝術等其它方面的素質教育”,逐漸形成了“以科舉中試為目標,以其它素質教育為輔助的家族教育體系”,這樣既保證家族世代科甲,也取得了豐碩的文化成就,成為維系文化望族社會地位的重要動力源泉。所以說,科第成功、文化素養的家族式沉淀,“奠定了久負盛名的江南乃至全國文化型望族的社會地位”[39]。
3 明清以來江南書香門第現象的歷史影響
3.1 促進了對傳統社會家國同構機制的反思
通過書香門第的發展演變,可以看到古人對書香的尊崇和摯愛。如何認識傳統中國社會中綿延兩千余年的書香門第的傳統,并從中汲取益世的營養?首先要對傳統社會結構有清醒的認識和洞察。中國傳統社會結構中最重要的是家族制度,而家又是整個社會的核心,“它是‘緊緊結合的團體’,并且是建構化了的,整個社會價值系統都經由家的‘育化’與‘社化’作用以傳遞個人。……在傳統中國,家不只是一個生殖的單元,并且還是一個社會的、經濟的、教育的、政治的乃至宗教、娛樂的單元。它是維系整個社會凝結的基本力量。”[40]現在看來,傳統“家國同構”社會較為形態下,較為單一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理念表現出了邏輯脫節、過于理想化等缺陷,傳統觀點強調道德素養的評價固然無可厚非,而時代要求的科學素養、人文素養則未能充分表達。因此,借用“家國同構”的外殼形式,突出家庭單元的獨立地位,實現兩者雙向互動的良性循環,既有利于保持社會的穩定和活力,又能加強國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具有積極和現實的意義[41]。當前,眾多的書香家庭,脫離了舊式家族式培養的土壤,借助“家國同構”機制,全面推動家庭書香文化涵育,進而為書香社會的發展提供必要的空間。
3.2 推動對歷代藏書文化現代性因素的挖掘
要深入挖掘古代藏書文化發展過程中出現的貴流通、倡捐贈的新思想。明末清初藏書家曹溶的《流通古書約》是藏書文化劃時代的總結性作品,它提出了“互借”主張,對后世藏書事業產生了積極影響。再看捐贈思想的發展,早在北宋時期就出現了把書籍捐給書院之事:“應天書院,宋大中祥符三年,邑士曹誠建,聚書千五百卷。”[42]南宋時期葉適也記載了一則藏書捐贈的事例:“東陽郭君欽正作書院于石洞之下,徙家之藏書以實之。”[43]晚清以后,倡導捐贈的現象更多。咸豐年間岳麓書院藏書盡毀于太平軍攻打長沙一役。戰后院長丁善慶著手恢復藏書,帶頭捐獻典籍862卷,隨后士紳學士紛紛捐獻,曾國荃、李翰章、李恒等捐贈大批典籍,到了同治十七年,私人典籍捐公比例達到65.9%[44],促進了湖湘文化發展,對于開啟民智、助長學風影響深遠。相較之下,固有的藏書在各個家族間的私相授受現象雖可以存文脈、正學風,形成多個書香維系的家族和家庭,然而這種偏狹的藏書私用、吝借風氣不可能產生普惠眾生的社會效用,對讀書的推廣缺乏深層推動力,更無助于普通民眾的知識獲取。對流習已久的書香門第傳統“茍能探源溯流,鉤微掘隱,勒藏家故實為一書,則千數百年來文化之消長,學術之升沉,社會生活之變動,地方經濟之盈虧,固不難一一如示諸掌也。”[45]詳細搜求歷代江南書香門第之故實,不但可以據此窺視江南社會與文化的互動脈絡,亦對當今書香家庭建設不無啟發意義。
3.3 為研究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文化發展中的“江南因素”提供了縱深空間
江南書香門第發展的歷史經驗不斷豐富和改變著我們的歷史認識。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一個后起的重要文化現象,江南書香門第已經具備了眾所公認的“文化隱喻”資格,成為理解傳統文化的一種認知手段,為開展文化研究提供了廣闊的前景。以近代江南出現的無錫錢氏望族為例,從五代十國時期的吳越王錢鏐到清代的錢大昕,到近代的錢玄同、錢鐘書、錢穆,再到當代的錢偉長、錢學森、錢永健,無不為中國學術文化、社會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錢氏家族得以成功延續的重要因素就是其重視藏書、重視讀書、重視教育的門風。無論是從歷史視野中的門第,還是從文化視野下的書香,都可以找到學術研究的靈感。在魏晉六朝就有“士族門閥”,經過長期的發展和演變,明清以后可以說過渡到了“書香門第”,從“文化隱喻”的思維方式出發,這是一種向文化本真狀態的回歸。從“士族門閥”到“書香門第”,這涉及到中國文化認知模式的轉變,可以豐富我們對國家和民族文化發展起到重要作用的“江南因素”的分析和評價的視野。這已經超越了本課題所倡導的藏書文化研究之本意,它也許是一個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需要進一步認真梳理和研究的基礎課題。
當前中國社會的家庭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沖擊和變革,延續了數千年的書香門第這一美好傳統出現斷層,因此,“書香家庭”重建命題必須提到議事日程,“只有當作為現代社會之細胞的家庭真正營造出一種濃郁書香氛圍的時候,讓每一個家庭都認識到所謂‘藏金藏銀不如藏書,花香酒香不如書香’的時候,讓每一個家庭都自覺意識到文化傳承之重大意義的時候,建構書香中國的國家戰略構想才有了一個可靠的基地。”[46]從書香門第到書香家庭,這看似驚人的歷史一躍,實則借助傳統家族式的聚書、讀書等方式,以回應現實對歷史的訴求。展望未來書香門第的建設,只有寄希望于個體家庭書香氛圍的營造和家庭閱讀的健康、良性發展,為家庭書香建設注入靈魂和動力,使書香規避社會價值觀空洞、泛化的惡性引導,讓書香融化冷漠、功利的家庭教育之缺失。惟其如此,書香中國的建設才有幾分實在的意義。
[1]育心累積法.書香門第成功教育的啟示[J].琴童,2013(1):58-59.
[2]姚蓉.明清江南文化世族刻書活動研究[J].思想戰線,2011(1):121-124.
[3][9][10][11][18][45]北京市歷史學會.吳晗史學論著選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08-209.
[4][5]李伯重.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業[J].中國經濟史研究,2001(3):94-107,146.
[6]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M].北京:中華書局,1958:60.
[7]奚椿年.中國書源流[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201.
[8]蕭東發.建陽余氏刻書考略[J].F.文獻,1985(1):236-250.
[12][36][37]祁承爜.澹生堂藏書約[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
[13][19]孫從添.藏書紀要[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96,100.
[14]李玉安,黃正雨.中國藏書家通典[M].香港: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2005:224.
[15]龐鴻文,等.(光緒)重修常昭合志[M]鄭鐘祥,等,修.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2210-2239.
[16]袁同禮.袁同禮文集[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10:84.
[17]張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2343.
[20]趙林平.明代蘇州藏書家抄書活動研究[D].揚州:揚州大學,2010:9.
[21]胡文學.甬上耆舊詩[M]//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
[22]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627.
[23]宋奎光.寧海縣志:卷九[M].崇禎五年刻本.
[24]黃佐.南雍志·經籍考[M]//太學文獻大成:卷十七.北京:學苑出版社,1996.
[25][26]吳與箕.讀書止觀錄[M].合肥:黃山書社,1990:31.
[29]王永彬.圍爐夜話[M].北京:中華書局,2008.
[30]金圣嘆.金圣嘆全集:三[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8-9.
[31]曾祥芹,張維坤,黃果泉.古代閱讀論[M].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2:8.
[32]王余光.關于閱讀史研究的幾個問題[J].圖書情報知識,2001(3):7-11.
[33]錢穆.國史大綱[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310.
[34][39]王曉洋.明清江南文化望族研究——以吳江汾湖葉氏為中心[D].蘇州:蘇州大學,2004.
[35]桑良至.愿光芒永放:名家書趣[M].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52-53.
[38]陸世儀.思辨錄輯要:卷四[M].同治正誼堂本.
[40]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29-30.
[41]舒敏華.“家國同構”觀念的形成、實質及其影響[J].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2):32-35.
[42]查岐昌.歸德府志:卷十一[M]//乾隆十九年刊本.
[43]葉適.水心集[M]//石洞書院記:卷九.北京:中華書局,1936.
[44]楊慎初,朱漢民,鄧洪波.岳麓書院史略[M].長沙:岳麓書社,1986:124.
[46]余小茅.書香中國暢想曲[J].教育研究,2012(1):134-137.
Fashion and Path:Constructing Scholarly Families in South Yangtze River Area of Ming Dynasty and Its Implication
WANG An-gong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scholarly families,as a cultural symbol,have the traditions of reading,learning and engaging in mundane life.There were several reasons for the forming of scholarly families in south Yangtze River area of Ming Dynasty:well-developed compiling and printing industry,prevailing private book libraries and book-copying.This article sorts out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scholarly families,indicating that scholarship should avoid empty social values and utilitarian family education.
scholarly family;library culture;south Yangtze River area;Ming Dynasty
格式化 王安功.風尚與渠徑:明代江南“書香門第”的構建及啟示[J].圖書館論壇,2015(3):41-47.
王安功(1978-),男,碩士,河南師范大學圖書館事業與文化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2014-07—20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近代以來藏書文化嬗變研究——以典籍捐公為中心”(項目編號:14YJC870020)、河南省社科規劃項目“近現代藏書文化嬗變視野下的典籍捐公研究”(項目編號:2014CZH002)、河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項目“近代以來藏書家典籍捐公的社會內涵研究”(項目編號:2014—GH—565)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