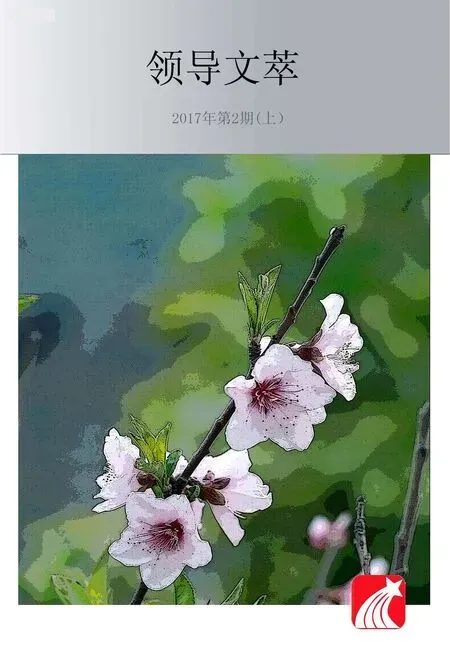中國經濟重回第一的歷史鏡鑒
劉培林

近日一條廣為關注的消息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根據國際比較項目的調查和測算結果推斷,按購買力平價衡量的中國GDP水平,將在2014年超過美國,重回到全球第一的位置。盡管購買力平價換算辦法并非盡善盡美,但在大體數量級的意義上看,是頗有參考價值的。
由盛轉衰再盛的中國經濟
已故的著名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在《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公元960年—2030年》的著作中這樣描寫中國的歷史地位:“中國現在是,而且一直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實體。早在公元10世紀時,中國在人均產出上就已經是世界經濟中的領先國家,而且這個地位一直延續至15世紀。在技術水平上,在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上,以及對遼闊疆域的管理能力上,中國都超過了歐洲。”
按照麥迪森估算的結果,15世紀時中國不僅人均產出水平高于歐洲和印度,人口規模也很大,所以中國經濟總規模相當于30個西歐國家之和的3倍,與另一個文明古國印度基本持平。
但是,15至19世紀初(明朝早期到清朝中晚期),世界東西方經濟增長態勢發生根本性逆轉。中國明朝開始閉關鎖國,人均產出水平徘徊不前。而同期西歐國家人均產出水平得益于一系列條件,幾乎翻了一番。這些條件包括:18世紀中后期發生的第二次農業革命使西方國家徹底擺脫了馬爾薩斯陷阱,農業部門生產率大幅提升到足以養活大量人口專事非農活動的水平,之后人口規模快速增長,人口預期壽命逐步延長,為工業革命鋪平了道路;確立了技術和發明的科學傳統;其他眾所周知的一系列重大制度變革,進一步催生了工業革命。
鴉片戰爭之后,在西方國家人均產出水平一路高歌猛進的同時,中國人均產出卻在下降,甚至低于印度的水平。近代中國人均產出甚至負增長。民國時期雖然1927年—1937年之間曾有過 “黃金十年”的增長,但中國綜合國力仍然非常低。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均產出快速提高,人口穩定增長,經濟總規模也相應快速提升。即使按照官方匯率衡量,中國人均收入水平已經于1999年和2010年先后跨入下中等和上中等收入行列;經濟總規模也早已躍升為全球第二。不少研究認為,即使按照匯率法衡量,中國在未來十年左右,也將成為全球第一經濟體。
中國GDP水平重新回到世界第一,當然是了不起的成就。因為伴隨著經濟總規模的增長,中國人均收入水平快速提升,人民生活質量明顯改善。40年前全球70%的人口生活在低收入國家行列,今天則有70%的人口生活在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中國把13億人口帶入上中等收入行列,可以說極大地改變了人類的收入分布格局。
這成就了不起,因為還有大量的發展中國家遠遠沒有達到中國目前的發展水平。這成就了不起,還表現在這一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后,發達國家增長乏力,而中國經濟保持了較快的增長勢頭。
兩個值得銘記的歷史教訓
大而不強并不能讓人高枕無憂。按照麥迪森收集的數據,1840年前后,中國在GDP四倍于英國的前提下,我們在家門口和越洋而來的英國艦隊進行的鴉片戰爭中敗北;1895年前后,在GDP五倍于日本的前提下輸掉甲午戰爭;1936年在GDP兩倍于日本的前提下遭到后者全面侵略。之所以如此,除了清朝政府和國民黨政府腐敗、軍隊戰斗力渙散的直接原因之外,恐怕一個更重要的因素是,未實現工業化的中國的GDP,都是由糧食、絲綢和瓷器構成的,而列強們的GDP則是由鋼鐵構成的。今天的中國早已成為世界制造和貿易大國,GDP構成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并不遜色。但歷史教訓仍然啟示我們,決不能妄自尊大、固步自封,與GDP的規模比起來,GDP的技術含量的重要性更大。
歷史也表明,國際力量格局變化猶如逆水行舟。雖然1870年時中國經濟總規模仍然為全球最大,比排名第二的印度高出40%,接近排名第三的英國和排名第四的美國的兩倍,相當于當時日本的7.5倍,但是之后短短20年左右的時間內,美國經濟總規模因為人均產出快速增長和人口規模的擴大而直線上升,中國經濟總規模因為人均產出降低和人口減少而絕對下降。中國全球經濟規模第一的地位在短短20年內被美國取代,用“其衰也忽焉”來形容中國經濟當時的情形并不為過。
如果說繼續保持相對于發達國家更快的GDP增速,堅持不懈地提升GDP的技術含量,是以往歷史提供的明確啟示的話,那么,中國未來發展進程中還有一個課題,是過去幾個世紀歷史上沒有可參照經驗的。歷史上全球領導國家位次更迭的共同特點是,GDP總量和人均水平大體同步。1820年作為世界領先國家的英國,GDP為世界第三(比中國和印度低),同時,其人均GDP為全球第二(略低于荷蘭)。1890年美國GDP為世界第一,其人均GDP水平處在全球第二的位置(僅次于英國)。隨著中國經濟總規模重回世界第一,無論是國際社會還是中國自身,都希望中國在全球治理和全球公共產品提供方面,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這也有一定的客觀性。但是,目前乃至今后10年至20年左右,中國人均GDP在世界上的相對水平,將遠遠低于英國和美國先后成為世界領導力量時情形。
這意味著,在世界東西方力量對比格局巨大變化的背景下,中國要從發展中國家的視角出發,帶著發展中國家的關切,在全球治理和全球公共產品的提供中,承擔相應義務,發揮相應作用。這需要發達國家和中國之間形成良性互動的關系,相互適應,共同探索。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這不僅是中國的新課題,也是世界的新課題。
(摘自《改革內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