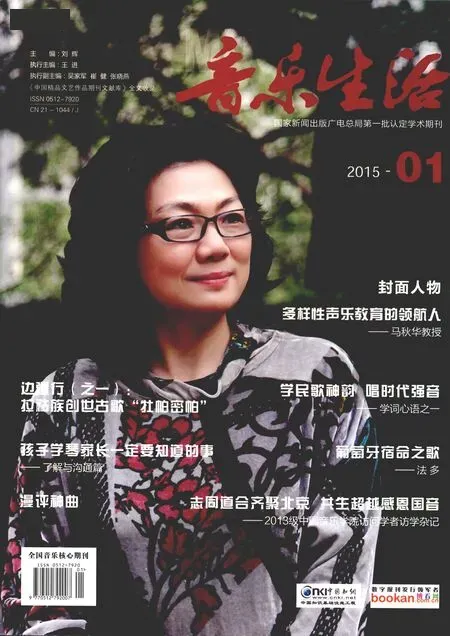20世紀西方音樂概覽(之十一)序列音樂
編/張寶華
20世紀西方音樂概覽(之十一)序列音樂
編/張寶華
序列音樂(serial music)又稱序列主義,是20世紀西方音樂的重要流派。序列音樂是指將音樂的各項要素(稱為參數)事先按數學的排列組合編成序列,再按此規定創作音樂。序列音樂的技法摒棄了傳統音樂的各種結構因素(如主題、樂句、樂段、音樂邏輯等),是20世紀50年代以后西方重要的作曲技法之一。
最早最簡單的序列音樂,應屬勛伯格所創立的十二音音樂。十二音音樂的音列,就是將音高排列成一定的序列。進一步走向序列音樂的是勛伯格的弟子韋伯恩,他在1936年所寫的《鋼琴變奏曲》第二樂章中使用了音高在各音區分布的序列以及發聲與休止交替的序列。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布列茲、梅西安、施托克豪森、諾諾等一批作曲家逐步將韋伯恩的方法加以擴展,使節奏、時值、力度、密度、音色、起奏法、速度等都形成一定的序列,產生了“整體序列主義”或“全序列主義”。在這方面進行理論探討的人還有巴比特(1916~2011)等作曲家。序列主義的創作方法在西方相當受重視,如斯特拉文斯基晚年也應用了一些序列主義的手法,但比較自由。序列主義在電子音樂中也得到進一步的運用,各種參數常被編成序列通過電子計算機輸入到電子合成器中。
一、二戰之后法國的“序列主義”

梅西安

梅西安與夫人洛里奧
作為一位在二戰結束時作曲家地位已經得到確立的重要人物,奧利維埃·梅西安(Olivier Messiaen 1908-1992)對歐洲年輕一代的序列主義作曲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包括施托克豪森和布列茲兩位序列音樂作曲家都出自梅西安門下。在梅西安早期創作中,就體現出一種嚴格且客觀的作曲技術,他把這種客觀理性的作曲技
術理論寫入了《我的音樂語言技術》(1944)一書中。在這本書中,梅西安把音高、力度、節奏、音色、節奏等單個音響元素均作為獨立分離的部分。梅西安認為每一個獨立的音響元素都有自己獨特的結構特性,它們應當被毫無保留地展現出來。盡管梅西安最初崇拜德彪西并從模仿德彪西開始起步,從其橫向音高材料關系是建立在各種人造音階,其中包括八聲音階和全音階等等。我們依稀可見德彪西的痕跡,但梅西安對音階的使用卻體現出一種不同尋常的系統化處理方式。這本書可以說是走進梅西安早期音樂創作不可跨越的界線。書中對于節奏處理的全新理念,可以說是全面序列主義中,節奏序列運用的理性化進程標志。如用一個“短小時值(如十六分音符)和它的各種自由變體所產生的節奏律動感來代替人們對于‘小節線’和‘節拍’的感知”。梅西安在此基礎上逐步形成了一種本質上無節拍的概念。另外,“附加時值”(added values)的概念作為梅西安節奏概念的核心,使那些規則的節奏形態獲得無限大的“節奏彈性”。如在1935年創作的《救世主的誕生》(管風琴曲),梅西安創造了復雜卻張弛自如的節奏運動模式,與以往按照節拍規律寫成的音樂中的那些節奏運動完全不同,給人以全新聽覺盛宴的“節奏序列”模式下的節奏律動感覺。與“附加時值”理念同等重要的是“不可逆節奏”(nonretrogradable rhythm),即一組節奏型無論從前至后或從后至前演奏均保持不變的時值順序。對于這種對稱的節奏結構,以及那些只允許有限移位數目的音高模式,梅西安稱之為“不可能之事之魅力”(the charm of impossibilities),《時間終結四重奏》(1940)的第六樂章即顯示出了這種不可逆節奏的藝術魅力。這種節奏材料本身所帶有的內在限制對于梅西安來說是技術源泉和審美價值取向的根源所在。
除了節奏序列和上述提到的全新節奏理念,梅西安對于西方現代音樂相距較遠的音樂材料也采取吸納借鑒的方式融入自己的音樂創作中,其中,“棱鏡”意識的材料運用理念使梅西安音樂中不僅吸收了印度音樂中獨特節奏型的運用,還使“格里高利圣詠”中旋律建構的獨特形式時空穿梭般地在他創作的20世紀音樂作品中再次得以重生般的復蘇。
在1948年創作的《圖郎加利拉交響曲》和1949年創作的鋼琴曲《坎泰諾達亞》《四首節奏練習曲》和《管風琴曲集》(1951)中,梅西安又在嘗試著“預制作曲”理論的有效方式。盡管當時的年輕一代作曲家將《四首節奏練習曲》當做整體序列主義的先例,但從中可以發現,梅西安遵循的是自己獨特音樂理念下完全不同的作曲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皮埃爾·布列茲(Pierre Boulez,1925— )還是個20歲的年輕人。由于具備和音樂一樣出色的數學基礎,布列茲完全傾向于一種純邏輯理性而非感性表現的視角來進行音樂創作。布列茲心中堅信無調性的歷史必然性,因此他將作曲視為一種意識作用下的“嚴格有序組合結構模式”。1946年完成的《小奏鳴曲》和《第一鋼琴奏鳴曲》在首演時曾引起強烈反響,其中,嚴密的結構手法、織體密度與戲劇性形式的并置,明顯受韋伯恩與勛伯格的影響。與此同時,傳統的主題處理痕跡又蘊藏著布列茲深厚的作曲功底。在隨后的作品中,布列茲繼續向著嚴格序列音樂的道路邁進,如《第二鋼琴奏鳴曲》(1948)、《四重奏篇》(1949)、《復調X》(1951)和《結構I》(1952)。

布列茲
二、德國序列主義——施托克豪森

施托克豪森
卡爾海因茨·施托克豪森(1928—2007)幾乎與布列茲齊名,是二戰之后整體序列主義音樂發展中最有影響的歐洲作曲家之一。施托克豪森在1951年達姆施塔特新音樂節夏季課程班聽到了梅西安《四首節奏練習曲》之后,便全面轉向了整體序列音樂的創作。離開達姆施塔特之后,施托克豪森便創作了為雙簧管、低音單簧管、鋼琴和三件打擊樂而作的《十字形游戲》。這部作品與他之前創作的一些具有傳統傾向的作品形成強烈反差。1952年,施托克豪森跟隨梅西安學習,與正在創作《結構I》的布列茲結為好友。與此同時,施托克豪森進行著《對位》和《鋼琴曲》I-IV的創作。《對位》顯示出一種類似對大規模過程的關注,花樣多變
的、在織體音色上有所區分的開始部分音樂,由時間樂器以主要是點描式演奏并帶有音區、力度等突然的對比,漸次轉化為連續和色彩單一的結束部分的音樂。而《鋼琴曲》則體現出施托克豪森更加富有彈性和變化的半音序列原則。以較大結構單位而并非以單個的組成因素來考慮音樂的傾向,使施托克豪森在1950年代中期從嚴格的序列主義中脫離出來,并對二戰之后的“先鋒派”音樂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例如,他發展了“參數”(又稱“音響度數”)理論,并把這種理論命名為“音群作曲法”。這種作曲技法拓寬了音樂的表現形式和演奏方法,增大了音樂作品中的機遇和偶然因素,也意味著同一首作品不可能會有兩場完全相同的演奏。另外,在電子音樂領域,施托克豪森也有突出貢獻。
三、美國序列主義——巴比特
如果說布列茲、施托克豪森是出于對20世紀早期音樂發展和美學原則的不滿而轉向序列主義,那么美國的作曲家米爾頓·巴比特(1916-2011)則完全從傳統的角度出發,把序列音樂作曲原則看作是“古典”十二音音樂寫作原則的一個直接結果和擴展。巴比特甚至比歐洲同時代作曲家還要更早開始研究把序列控制擴展到其它音樂元素的美國人,他更多的是把勛伯格而韋伯恩看作是他音樂的先例。巴比特創作于1947年的《三首鋼琴曲》是將音高與非音高因素通過序列化處理來進行嚴格結構安排的最早作品。巴比特曾經說:“我希望一首音樂作品應該真正做到盡可能豐滿”。他在每一部作品中都創造出音樂關系的最大數(maximum number),從他的材料中獲得盡可能多的“內容”,即“派生序列”原則。
巴比特與歐洲同時代作曲家的序列音樂創作不一樣,他始終保持著對序列主義的忠誠。首先,他轉向序列主義并不是把他作為一種避免音樂結構傳統概念的方法,而是把它當做是對這一概念的擴充和延伸;另外,在他的序列音樂中,音高這個傳統西方音樂的主要結構手段,保持著優先的地位;除此之外,巴比特的方法一直在不斷地發展和完善。他不斷地擴充著他那“陣型”創作概念,并引入新的類型。作為一名作曲家、教師、音樂理論家和作家,巴比特對20世紀美國音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創作的《返始詠嘆調》(1974)、《釋義曲》(1979)、《第五弦樂四重奏》(1982)和《卡農形式》(1983)盡管都帶有深奧的邏輯和復雜的序列原則,但音樂所表現出的優雅細膩似乎掩飾了它在結構設計上的刻板。巴比特開創性的理論文章徹底改變了十二音音樂的研究視角,并對美國年輕一代作曲家產生了深遠影響。
雖然全面序列主義在歐洲很快便證明是一條行不通的路,但不可否認,序列音樂幾乎影響到二戰之后歐美的整整一代作曲家,它開啟了20世紀下半葉更為激進的音樂革命風暴,其影響直到今天依然存在。

巴比特
(責任編輯 姜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