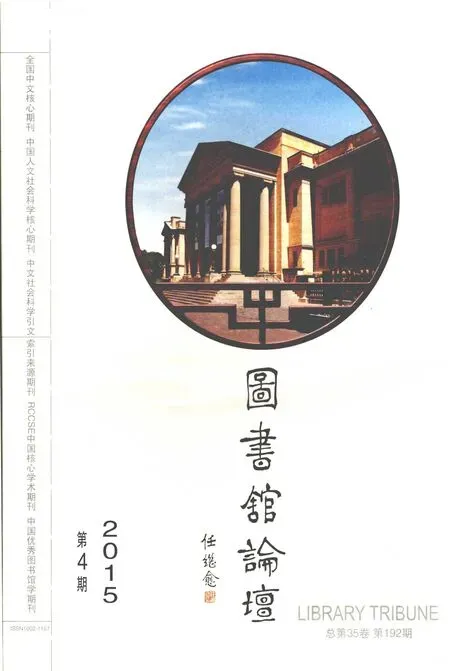試論中國圖書館學(xué)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
王余光
1 關(guān)于中國“古代圖書館學(xué)”的稱謂問題
中國古代有十分豐富的藏書管理理論與實踐,并有著數(shù)量眾多的圖書整理理論與著作,這些研究是我國圖書館學(xué)的基礎(chǔ)與重要組成部分。對于這一領(lǐng)域的研究,我們是否可稱之“圖書館學(xué)”?
中國古代是否有“圖書館學(xué)”?這個問題的爭論在我國圖書館學(xué)界由來已久。筆者在開展“中國圖書館學(xué)史”的課題項目研究時,無法回避該問題,因此進一步梳理和明確“古代圖書館學(xué)”的稱謂問題在研究工作中顯得尤為重要。
1985年,謝灼華在《中國圖書館學(xué)史序論》中指出:“中國古代能否產(chǎn)生圖書館學(xué)?或者說,古代關(guān)于藏書管理的知識(經(jīng)驗)能否稱作圖書館學(xué)的范圍?回答是肯定的。”[1]顯然,謝先生是肯定中國古代已形成圖書館學(xué),他還進一步提出了自己的學(xué)理依據(jù),并明確提出了“古代圖書館學(xué)”這一概念。他說:“人類的一切知識都來源于實踐,人們在實踐過程中直接所取得的經(jīng)驗,以及繼承、吸收、分析、批判前人積累的各種經(jīng)驗(即知識的積累),逐步形成對某一種事物的規(guī)律性的認(rèn)識,那么,這種認(rèn)識就是一種知識體系。圖書館學(xué)的形成正是經(jīng)歷了這種科學(xué)發(fā)展的一般過程。所以,如果承認(rèn)古代圖書館工作內(nèi)容是一種社會實踐活動,而這種社會實踐活動是不斷發(fā)展和不斷豐富的。漫長的封建社會中,豐富的圖書館工作內(nèi)容必然逐步促進了圖書館工作知識和經(jīng)驗的積累,因此,也就逐步孕育了古代圖書館學(xué)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2]在此基礎(chǔ)上,謝先生將古代圖書館學(xué)進一步劃分為四個階段:(1)古代圖書館學(xué)思想的醞釀時期(漢魏六朝);(2)古代圖書館學(xué)思想的形成時期(隋唐五代);(3)古代圖書館學(xué)體系建立時期(宋元);(4)古代圖書館學(xué)體系完善時期(明清)。[3]
然而,謝先生的觀點并沒有在學(xué)術(shù)界取得共識。不少學(xué)者認(rèn)為,“圖書館學(xué)”是舶來品,古代相關(guān)研究與今日的圖書館學(xué)研究有著“巨大的性質(zhì)差異”,因而稱為“圖書館學(xué)”是不合適的。比如,李剛、倪波認(rèn)為:“中國圖書館學(xué)是指基于現(xiàn)代西方圖書館學(xué)學(xué)理,作為中國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現(xiàn)代建制化結(jié)果的一門社會科學(xué)學(xué)科。中國古代并不存在一門叫‘圖書館學(xué)’的專門學(xué)科,‘圖書館學(xué)’這個概念本身就是現(xiàn)代性的一部分。當(dāng)然,中國古代存在著與今天圖書館學(xué)某些類似的整理文獻的專門學(xué)問,傳統(tǒng)學(xué)人稱之為目錄、版本、校讎之學(xué)。這些學(xué)問在學(xué)理上和現(xiàn)代圖書館學(xué)有著巨大的性質(zhì)差異。”[4]其實,用“現(xiàn)代性”概念來研究古代學(xué)問是很正常的,如中國哲學(xué)史、中國邏輯學(xué)史等。而該文認(rèn)為的古代整理文獻的專門學(xué)問與現(xiàn)代圖書館學(xué)有著巨大的性質(zhì)差異,但并未加以論證,難以成立。
有些學(xué)者不用“古代圖書館學(xué)”這一稱謂,轉(zhuǎn)用“傳統(tǒng)圖書館學(xué)”的表述方式。比如,袁寶龍在《當(dāng)代視域下的傳統(tǒng)圖書館學(xué)》一文中指出:“中國圖書館學(xué)學(xué)術(shù)體系誕生于20世紀(jì)初,由中國傳統(tǒng)藏書理念與西方現(xiàn)代思潮兩者碰撞融合而成,傳統(tǒng)圖書館學(xué)與現(xiàn)代圖書館學(xué)理念也因此成為中國圖書館學(xué)的兩大源流。”[5]此外,張樹華把古代圖書館學(xué)稱為“前圖書館學(xué)”,她說:“有關(guān)整理圖書的知識發(fā)展為‘目錄學(xué)’,有關(guān)鑒定圖書的知識發(fā)展為‘版本學(xué)’、‘校勘學(xué)’。公、私藏書家有關(guān)圖書的訪求、整理、庋藏、保管、管理及應(yīng)用的知識和理論也日益增長,并日趨完善。這些知識和理論可以說是中國圖書館學(xué)的一部分,我稱之為‘前圖書館學(xué)’。”[6]
筆者認(rèn)為,傳統(tǒng)圖書館學(xué)的內(nèi)容,首先是古代藏書管理(有學(xué)者將其稱為藏書學(xué),即書籍的收集、保存、利用與傳承)的思想、方法等;其次是古代藏書整理的部分思想與方法,即校讎學(xué)(至20世紀(jì)多稱“文獻學(xué)”,但校讎學(xué)仍有沿用)。
按照與圖書收藏、利用之間關(guān)系的密切程度,校讎學(xué)可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與藏書活動直接相關(guān)的目錄學(xué)、版本學(xué)等;第二層次是間接相關(guān)的輯佚學(xué)、辨?zhèn)螌W(xué)等;第三層次則是校勘、注釋等相對獨立的學(xué)問,并非藏書整理活動的必備工作。因此,藏書管理和“校讎學(xué)”即是中國古代的圖書館學(xué)。
“從概率上講,”我身邊的博學(xué)派男生威爾笑著說,“即使是亂打,到現(xiàn)在最起碼也該打中一次。”他滿頭蓬松的金發(fā),雙眉之間有一道豎紋。
基于以上分析,筆者認(rèn)為中國“古代圖書館學(xué)”的概念是成立的,受到西方現(xiàn)代圖書館學(xué)話語體系的影響而認(rèn)為中國古代沒有圖書館學(xué)是不合適的,就像“哲學(xué)”這一概念,在寫中國哲學(xué)史時能夠因為中國古代沒有“哲學(xué)”這一概念而認(rèn)定中國古代沒有哲學(xué)嗎?因此,筆者承認(rèn)中國“古代圖書館學(xué)”這一概念的成立,同時也注意用現(xiàn)代圖書館學(xué)話語體系來解釋古代的圖書館學(xué)現(xiàn)象。
近百年間中國圖書館學(xué)教育的開設(shè),其中目錄學(xué)、版本學(xué)等文獻學(xué)課程一直是圖書館學(xué)專業(yè)的重要課程,這從另一個側(cè)面也說明上述學(xué)問是圖書館學(xu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古代圖書館學(xué)與現(xiàn)代圖書館學(xué)在學(xué)術(shù)的發(fā)展上是一脈相承的關(guān)系,我們不應(yīng)該在現(xiàn)代西方圖書館學(xué)話語體系的沖擊下,將中國圖書館學(xué)史人為地割裂開來,并否認(rèn)中國“古代圖書館學(xué)”的存在。
2 關(guān)于中國圖書館學(xué)史的分期問題
每一門學(xué)科的發(fā)生、發(fā)展都必定會經(jīng)歷一定的歷史過程,而這一過程往往是漫長的,進行學(xué)科史的研究就必須確定學(xué)科發(fā)展的分期問題,這樣才能使學(xué)科發(fā)展的歷史過程清晰地展現(xiàn)出來。中國圖書館學(xué)史的研究也不例外。
對于中國圖書館學(xué)史的分期問題,主要有兩種劃分途徑:一是以中國社會歷史發(fā)展的分期為依據(jù),這一途徑主要是以承認(rèn)“古代圖書館學(xué)”的稱謂為前提;二是以20世紀(jì)初期“圖書館”作為專有名詞出現(xiàn)在中國,隨后在20世紀(jì)20年代中國圖書館學(xué)教育正式建制開始,主要勾勒整個20世紀(jì)中國圖書館學(xué)的發(fā)展脈絡(luò)。顯然持這一劃分途徑的學(xué)者是對中國古代有“圖書館學(xué)”這一說法存在異議的。
對于第一種劃分途徑,吳仲強在《中國圖書館學(xué)史》一書中,按照中國歷史分期把中國圖書館學(xué)史劃分為中國古代圖書館學(xué)史(1840年以前)、中國近代圖書館學(xué)史(1840-1919年)、中國現(xiàn)代圖書館學(xué)史(1919-1949年)、中國當(dāng)代圖書館學(xué)史(1949年以后)四個時期[7]。楊建東、羅德遠(yuǎn)認(rèn)為中國圖書館學(xué)史應(yīng)分為四個時期:中國圖書館學(xué)的孕育時期(封建社會)、中國圖書館學(xué)的萌芽時期(19世紀(jì)后半葉至20世紀(jì)初)、中國圖書館學(xué)的產(chǎn)生時期(辛亥革命以后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圖書館學(xué)的發(fā)展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8]。宓浩在《圖書館學(xué)原理》一書中認(rèn)為,清以前為中國古代圖書館學(xué)時期;1949年以前為中國圖書館學(xué)創(chuàng)建時期;1949年以后為中國圖書館學(xué)的發(fā)展時期[9]。
按照以上兩種劃分途徑分別進行中國圖書館學(xué)史分期研究的學(xué)者還有很多,不一一贅述。有些學(xué)者甚至認(rèn)為我國的圖書館學(xué)就是模仿西方圖書館學(xué)的歷史,由此得出中國圖書館學(xué)還處于萌芽狀態(tài)的結(jié)論。認(rèn)為目前圖書館學(xué)確實存在大量無法達成一致意見的術(shù)語和概念,使得眾多學(xué)者感到單從學(xué)術(shù)角度去探討中國圖書館學(xué)史的分期問題有些無從下手[10]。
很明顯,按照第一種途徑進行劃分的學(xué)者是以歷史發(fā)展階段為依據(jù)的;按照第二種途徑進行劃分的學(xué)者突出了圖書館學(xué)的主體性,但忽略了中國古代圖書館學(xué)的存在。
筆者認(rèn)為,長期以來我國學(xué)術(shù)界在專門史(如圖書史、藏書史與圖書館史)或?qū)W術(shù)史(如圖書館學(xué)史)發(fā)展階段的研究中,受社會歷史階段論劃分的影響很大,忽略了這些專門史或?qū)W術(shù)史自身的主體性與特征。
筆者對于中國圖書館學(xué)史的分期問題,從圖書館學(xué)史發(fā)展過程的學(xué)術(shù)特點,根據(jù)中國圖書館學(xué)發(fā)展的特征,將其分為四個時期:
(1)中國古代圖書館學(xué)(20世紀(jì)以前)。上文中已討論“中國古代圖書館學(xué)”的概念等問題。筆者認(rèn)為古代圖書館學(xué)是中國圖書館學(xué)史一個重要階段與重要組成部分。鴉片戰(zhàn)爭之后,按歷史學(xué)家的看法,中國進入近代社會,但圖書館學(xué)研究并未發(fā)生質(zhì)的變化,其研究內(nèi)容與形式仍然延續(xù)著固有的模式。因此,筆者把古代圖書館學(xué)的下限定在19世紀(jì)末。
(2)中國近代圖書館學(xué)(20世紀(jì)前期)。20世紀(jì)是中國圖書館學(xué)變化最大的時期。從“圖書館”到“圖書館學(xué)”的提出,從思想方法的引進到逐步本土化,從傳統(tǒng)教育到現(xiàn)代專業(yè)教育的正規(guī)化,中國圖書館學(xué)告別古代,進入近代階段。
(3)中國現(xiàn)代圖書館學(xué)(20世紀(jì)后期)。有一點無可否認(rèn),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對中國學(xué)術(shù)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因此,筆者將20世紀(jì)圖書館學(xué),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間點,分為近代和現(xiàn)代兩個階段。從總體看,20世紀(jì)后20年,中國圖書館學(xué)無論是教育還是研究,在深度與廣度上都超越了20世紀(jì)前期的水平,中國圖書館學(xué)才真正進入現(xiàn)代階段。
(4)中國當(dāng)代圖書館學(xué)(21世紀(jì)以來)。20世紀(jì)末,隨著網(wǎng)絡(luò)化與數(shù)字圖書館的出現(xiàn),圖書館學(xué)研究在很多領(lǐng)域出現(xiàn)了根本的變化,因此,筆者認(rèn)為,以21世紀(jì)為節(jié)點,中國圖書館學(xué)進入當(dāng)代階段。
3 關(guān)于中國圖書館學(xué)史的寫法
中國學(xué)術(shù)史研究有著優(yōu)良的傳統(tǒng)。從黃宗羲的《明儒學(xué)案》、戴望的《顏氏學(xué)記》到梁啟超、錢穆的近三百年學(xué)術(shù)史研究,直至張舜徽的《清儒學(xué)記》,學(xué)術(shù)史研究一脈相傳,其方法雖各異,其內(nèi)容或趨同。就學(xué)術(shù)史具體內(nèi)容而言,筆者在《圖書館學(xué)史研究與學(xué)術(shù)傳承》一文中提到,約略有如下數(shù)端:“(1)學(xué)人的學(xué)術(shù)經(jīng)歷,撰述、學(xué)術(shù)思想的評述等;(2)辨章學(xué)術(shù),考鏡源流,學(xué)人學(xué)術(shù)傳承與學(xué)派;(3)一個時代的學(xué)術(shù)基礎(chǔ)(教育、出版與學(xué)術(shù)雜志等)、學(xué)術(shù)思潮以及對學(xué)人的影響。”[11]
學(xué)術(shù)史可讓后學(xué)知曉學(xué)術(shù)發(fā)展脈絡(luò),學(xué)術(shù)的精華與糟粕,讓“上下諸先生,深淺各得,醇疵互見”[12],并為當(dāng)代學(xué)術(shù)的發(fā)展奠定基礎(chǔ)。當(dāng)然學(xué)術(shù)史還有另一層重要的意義,如張舜徽所云:“我們總結(jié)前人在學(xué)術(shù)上取得的成就時,除條理史實外,也還有觀摩借鑒的一面。對他們的為人處世之道,進德修業(yè)之方,都要認(rèn)真體認(rèn),引歸身受。他們好的言論行動,可資學(xué)習(xí);缺點錯誤,可為厲戒。”[13]
隨著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的建立與學(xué)術(shù)的分科,專業(yè)學(xué)術(shù)史的建立更應(yīng)受學(xué)術(shù)界重視。關(guān)于圖書館學(xué)史,即圖書館學(xué)術(shù)史,二者不應(yīng)有什么區(qū)別。另外,圖書館學(xué)所研究的對象,如圖書文獻、藏書與圖書館等,與圖書館學(xué)史有重要關(guān)聯(lián),但其歷史不應(yīng)是圖書館學(xué)史的一部分。而圖書館學(xué)教育與圖書館學(xué)研究有著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因而圖書館學(xué)教育史應(yīng)為圖書館學(xué)史的一個組成部分。有鑒于此,筆者將中國圖書館學(xué)史的撰寫,根據(jù)不同階段,每階段分為三個方面:
(1)中國圖書館學(xué)史通論。討論這一階段圖書館學(xué)發(fā)展脈絡(luò),辨章學(xué)術(shù),考鏡源流,以期探究圖書館學(xué)發(fā)展的規(guī)律。
(2)中國圖書館學(xué)史專論。選取與圖書館學(xué)研究有密切關(guān)系的重要事項,如社會思潮、藏書樓、圖書館的發(fā)展、古代圖書整理、圖書館學(xué)教育、圖書館人留學(xué)、圖書館學(xué)會、圖書館學(xué)期刊等,分別專題討論,以期探究圖書館學(xué)發(fā)展所受的社會影響。
(3)中國圖書館學(xué)史學(xué)案。選取一批重要圖書館學(xué)人,對其生平、著述與思想加以討論,以期探討其在中國圖書館學(xué)史上的傳承、成就與影響,可為今人之借鑒。
4 結(jié)語
隨著“中國圖書館學(xué)史”課題項目研究的有序進行,我們在逐漸厘清上述爭議問題和模糊地帶的同時,進一步明確了課題規(guī)劃和寫作重點及方向,為課題的后續(xù)開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chǔ)。我們期待在2018年課題結(jié)項之時,能夠為廣大圖書館學(xué)人勾勒出一幅相對完整又兼具自身寫作特色的中國圖書館學(xué)史全景。
[1][2][3]謝灼華.中國圖書館學(xué)史序論[J].武漢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1985(3):122-127.
[4] 李剛,倪波.分期的意識形態(tài)——兼論20世紀(jì)中國圖書館學(xué)[J].圖書情報工作,2002(6):48-51,56.
[5] 袁寶龍.當(dāng)代視域下的傳統(tǒng)圖書館學(xué)[J].圖書館學(xué)研究,2014(5):8-14,3.
[6] 張樹華.中國“前圖書館學(xué)”的發(fā)展及有關(guān)文獻[J].大學(xué)圖書館學(xué)報,2012(3):30-36.
[7] 吳仲強.中國古代圖書館學(xué)史論[J].圖書情報工作,1992(4):1-7,48.
[8] 楊建東,羅德遠(yuǎn).中國圖書館學(xué)的形成與發(fā)展[J].河北高校圖書館,1985(3):12.
[9] 宓浩.圖書館學(xué)原理[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88:23.
[10]成驥.中國圖書館學(xué):從模仿走向創(chuàng)新——從中國圖書館學(xué)史分期說起[J].圖書館建設(shè),2005(4):24-27.
[11]王余光.圖書館學(xué)史研究與學(xué)術(shù)傳承[J].山東圖書館學(xué)刊,2009(2):1-3.
[12]黃宗羲.明儒學(xué)案·黃黎洲先生原序[M].北京:中華書局,1985:10.
[13]張舜徽.清儒學(xué)記·自序[M].濟南:齊魯書社,19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