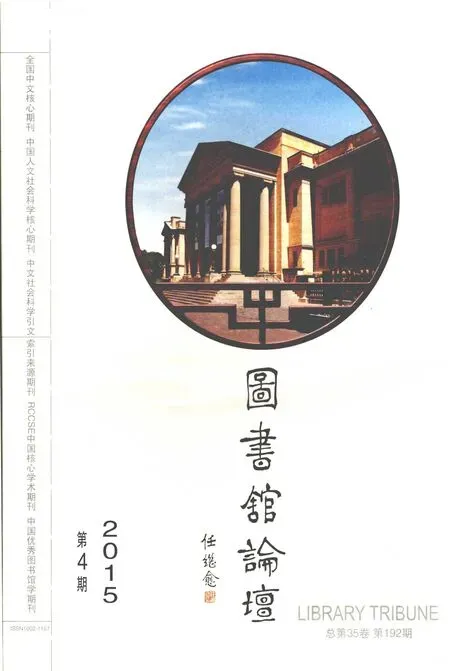張舜徽先生學術思想對圖書館學的影響*
王余光,錢 昆
0 引言
張舜徽(1911.8.24-1992.11.27),湖南沅江人,出生于書香之家,自學成才,治學廣博,在文史哲領域均有創見,尤以文獻學研究見長,代表作有《廣校讎略》《中國文獻學》《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清人文集別錄》《清人筆記條辨》《漢書藝文志通釋》《中國古代史籍舉要》等[1]。
在現有學科體系中,文獻學與圖書館學有著緊密的聯系,文獻學亦是圖書館學專業的重要課程,因此張先生的學術思想與治學軌跡難免與圖書館、圖書館學產生千絲萬縷的聯系。“張先生在自學與治學的漫長歲月里,與圖書館結下了不解之緣,他不僅早年自學得益于圖書館,在他后來治學的幾十年里,也無處不利用圖書館,因而他熟悉了解圖書館,關心圖書館的建設發展,并身體力行,以自己的實際行動支持圖書館的工作。”[2]張先生的藏書在其去世后送藏湖南圖書館。1947年張先生致劉國鈞先生的一封信中可略見其與圖書館學人的學術交流與互動:“衡如先生左右,昨接清談,彌欽通核。承索拙著《廣校讎略》。茲奉上一本,敬求教正。”[3]
張舜徽先生的學術思想對圖書館學的深遠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1 治書之學
文獻是記錄知識的一切載體,廣義的圖書等同于文獻。對圖書與圖書館史的研究歷來是圖書館學研究的重點。張先生在文獻學研究過程中對書籍制度和古書的散亡(即“書厄”)等問題頗有研究,形成獨到的治書之學。張先生的治書之學發軔于1945年出版的《廣校讎略》,而在1982年出版的《中國文獻學》中得到進一步完善。
《廣校讎略》共5卷100篇。卷一討論校讎學及相關名稱,20世紀初期普遍被人接受的名稱是“校讎學”而非“文獻學”。從校讎學討論范圍看,有狹、廣之分,狹義的校讎學即今日所說的校勘學;廣義的校讎學即今日所說的文獻學。20世紀出版的校讎學著作幾乎都是廣義的校讎學,張先生在《廣校讎略》中主張的也是廣義的校讎學。20世紀后期校讎學被文獻學取代。卷二討論古代書籍流傳問題,主要包括著述體例、著述標題、關于作者、稱引體例、序書體例和注書流別。卷三討論古代書籍流傳問題,包括簡紙與書籍的篇卷以及書籍之散亡。卷四討論校讎學的各種方法,如目錄、分類、校勘、辨偽、輯佚。卷五討論漢唐宋清學術成就,重點放在校讎學方面,如辨章學術始于太史公、鄭玄注群經[4]。
《中國文獻學》 共12編。第1-2編沿襲《廣校讎略》卷一、卷二體例,討論文獻學的范圍與任務、古代文獻的散亡和編述體例等;第3-5編依次闡述古代文獻整理的三項主要工作,即版本、校勘和目錄;第7-10編闡述前人整理文獻的具體工作、豐碩成果、業績和貢獻等;第11編指明今后整理文獻的重要工作;第12編重申整理文獻的主要目的和重大任務[5]。
此二書皆體現了張先生在治書之學方面的會通思想。他在《廣校讎略》中說:“近世學者于審定書籍,約分三途:奉正史藝文、經籍志及私家簿錄數部,號為目錄之學;強記宋、元行格,斷斷于刻印早晚,號為板本之學;羅致副本,汲汲于考訂文字異同,號校勘之學。然揆之古初,實不然也。蓋三者俱校讎之事,必相輔為用,其效始著。否則析之愈精,逃之愈巧,亦無貴乎斯役矣。”[6]他在《中國文獻學》中進一步總結章學誠的見解:“古人只有校讎之學,別無所謂目錄之學。”[7]該觀點雖非張先生首創,然張先生始終堅持這一觀點,引起圖書館界對此問題的爭論。
2 目錄之學
張先生治學講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因此極其重視“提要”與“別錄”文獻研究方法,有《清人文集別錄》《清人筆記條辨》兩部力作問世。張先生亦重視注釋實踐工作,繼《說文解字約注》,更在晚年完成《漢書藝文志通釋》這部力作,對文獻學研究貢獻巨大,尤其在目錄學研究領域。由于圖書館學界普遍認為目錄學是一門獨立的學科,也是圖書館學的必修課程,所以張先生在目錄學領域對圖書館學的影響,不僅表現在鴻篇巨制的學術著作里,更表現在學術觀點對圖書館學人的影響,這種影響當然也包括某種觀點引起的爭論。
張先生本著鄭樵、章學誠的觀點,強調目錄、版本、校勘皆校讎之事,校讎學之外,不應另有目錄學。關于目錄學的名實爭論由來已久,在張先生繼鄭樵、章學誠二人之后再次重申這一觀點時,引發圖書館界更為激烈的爭論。比如,彭斐章、謝灼華兩位先生在探討目錄學研究對象時,指出持“否定說”的人認為:“目錄、版本、校勘三者是校讎學的組成部分,目錄不能自成為學科,但舉校讎足以包舉無遺。這并非什么新觀點,早在清代,章學誠就不承認有目錄學,而欲以校讎學包舉之。從那時起直到今天,還有人不斷地否定目錄學的獨立存在,這種觀點既不符合現代科學的發展,又不能反映目錄學發展的歷史和現狀。隨著社會的向前發展,文化科學的進步,以及知識的不斷分化,從而導致目錄學與版本學、校讎學劃分了界限。它們各自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分別發展成獨立的學科。這也是人類對于客觀世界認識不斷深化的結果。”[8]
董慧敏認為校讎學與目錄學“這二者之間雖然還有某種必要聯系,但作為兩門學科,其性質、研究對象及任務不能混淆”[9]。柯平在對張先生否定目錄學的觀點提出質疑時,進一步總結校讎學與目錄學之爭主要有三派觀點:一是否定目錄學的存在,用校讎學包舉目錄學;二是認為校讎學即目錄學,用校讎目錄學之名替換;三是目錄學與校讎學是兩個獨立學科。柯平認為章學誠、杜定友、張先生同屬一派,觀點都是用校讎學包舉目錄學,而今仔細推敲,這樣歸納未必妥當。他進一步強調,現在目錄學與校讎學是兩門獨立的學科,古典目錄學是文獻學的組成部分,而現代目錄學則沖出了文史目錄學、校讎目錄學、版本目錄學的范圍,內容更豐富,并日趨走向新的時代,我們應該看到這一點[10]。柯平說:“三十年代著作中否認目錄學,五十年代著作中承認目錄學,七十年代文章中又否認目錄之學。前后矛盾,使人難得其解。”[11]
其實這是誤解,張先生在著作中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正如李勤合所說:“張先生有時著書論文之所以用“目錄學”之名,多因涉及之人自稱目錄學家,而求行文方便,非真騎墻之論也。”[12]
當然,也有人支持張先生的觀點。比如,李華斌、魯毅認為:“從張氏《廣校讎略》《中國文獻學》等來看,不承認目錄學、反對單立目錄學的觀點可能有些偏激,與主流看法不合,難被學者接受……但籀繹其理,則發現其確立的為會通的校讎學……會通的校讎學作為一種代表的學術觀點,隨著時間的流逝,逐步被學術界理解、認可和接受,例如程千帆、徐有富編寫《校讎廣義》,分版本、校勘、目錄、典藏四篇,繼續沿用廣義校讎學的概念。”[13]
李勤合指出:“張舜徽于1945年提出用校讎學包舉目錄、板本、校勘,而否定目錄學的意見。這是由他通人之學、反對狹隘、由博返約的學術風格決定的。”[14]他進一步指出:“對于學者之觀點論說,不能簡單地僅從邏輯上去判斷,還須從學者所處之環境、人生之經歷、為學之風格考量,這是從孟夫子‘知人論世’說到近代陳寅恪‘了解之同情’說傳下來的我國優秀的文化傳統。可惜,學界在批評張舜徽先生有關目錄學的觀點時,少有從此入手者。”[15]這是對張先生目錄之學最好的注解。結合張先生所處環境、人生經歷以及為學風格,可以進一步理解張先生的文獻學觀,從而理解他的目錄之學。
3 閱讀指導
我國自古以來就有先生給學生開書目的傳統,以達到指導后生治學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圖書館學界,不管是對目錄學的理論研究,還是對閱讀推廣工作的實踐研究,閱讀指導一直是研究重點,尤其在經典閱讀方面,張先生的閱讀指導思想亦可為今日圖書館的閱讀推廣工作和目錄學理論研究提供借鑒。
張先生自1941年起,先后在湖南國立師范學院、北平民國大學、蘭州大學、華中師范大學等校任教,博覽群書,走通博之路,對小學、經學、史學、文獻學都有精深研究,因此張先生的閱讀指導主要以繼承傳統學術、經典閱讀為核心內容,而研究并繼承傳統學術的前提是通識古文字。張先生強調:“閱讀舊籍,必識古字古義。士而有志習本國文史,則日接于目者,皆古書也。茍不識其文字,何其通其語義,故讀書必以識字為先。”[16]為此,1947年張先生在蘭州任教期間,曾給學生開列了《初學求書簡目》。張先生認為:“讀書以識字為先,學文以多讀為本。必于二者深造有得,而后可以理解群書。”[17]意即通識古文字是讀書的基礎,通而不讀始終會立于學術之門外,因此,識字必須與讀書相聯系,并以讀書為歸宿。他在《初學求書簡目》中首列“識字”“讀文”兩類,其中“識字”類下細分為字形、字音、字義三小類,字形類開列的書目包括《文字蒙求》《說文解字》《說文解字注》等8種,字音類開列的書目包括《廣韻》《說音》《切韻考》等8種,字義類開列的書目包括《爾雅義疏》《廣雅疏證》《釋大》等6種。凡此20余種,作為識字的入門書,以為閱讀舊籍的基礎。在21世紀的今天,大學生閱讀不再以識字為先,一些大學生閱讀書目中不再收錄《說文解字》,但筆者認為在研習傳統學術、閱讀古代經典文獻方面,張先生在“識字”方面開列的書目仍有指導和借鑒意義。
除列“識字”類外,張先生另在“讀文”類收錄選本三種,包括《古文辭類纂》《續古文辭類纂》《經史百家雜鈔》。在“識字”和“讀文”之后,又列經傳、史籍、百家言、詩文集、綜合論述五類,其中經傳類包括《詩》《尚書》《左傳》《國語》《論語》《孟子》等19種;史籍類包括《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鑒》《文獻通考》等32種;百家言類包括《管子》《老子》《莊子》《墨子》《孫子》《荀子》等24種;詩文集類包括《楚辭》《文選》《全上古三代秦漢六朝文》《杜工部集》《白氏長慶集》《歐陽文忠集》等19種;綜合論述類包括《夢溪筆談》《容齋五筆》 《日知錄》《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31種。所錄各書,張先生皆作版本或作者提示,或作書中提要,或品評得失,有利于初學。
張先生在華中師范學院歷史系講授過《中國歷史要籍介紹及選讀》,1983年主持編撰《中國史學名著題解》,再次強調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走博通之路,方能“由淺入深,自近及遠,有自得之樂”[18]。
4 結語
張舜徽先生治學走博通之路,成就斐然,在治書之學、目錄之學和閱讀指導三個方面對圖書館學的發展產生了影響。筆者主持的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圖書館學史”也體現了“會通”的思想,這也是張先生對筆者潛移默化的影響。
[1][5][7]張舜徽.中國文獻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 劉雪萊.張舜徽先生與圖書館[J].圖書館,1993(3):51-53,39.
[3] 王余光.張舜徽致劉國鈞的一封信[J].圖書與情報,2011(6):136-137.
[4] 王余光.張舜徽先生的文獻學成就[J].圖書與情報,2002(4):15-19.
[6] 張舜徽.廣校讎略:漢書藝文志通釋[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7.
[8] 彭斐章,謝灼華.目錄學文獻學論文選[M].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2-3.
[9] 董慧敏.從古今校讎學與目錄學的分合看目錄學獨立之可成立性——兼與張舜徽同志商榷[J].圖書館建設,1982(S2):267-271.
[10][11]柯平.目錄學札記——校讎學與目錄學[J].贛圖通訊,1986(1):23-24.
[12][14][15]李勤合.張舜徽目錄觀發微[J].九江學院學報,2007(5):123-125.
[13]李華斌,魯毅.張舜徽會通校讎學發微[J].黔南民族師范學院學報,2009(1):17-20.
[16][17][18]王余光.文獻學與文獻學家[M].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122-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