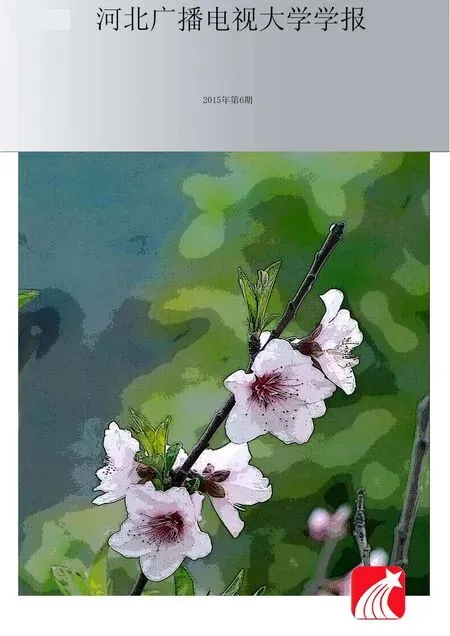單音節動詞的句法—語義關聯:以“變”為例
李蘭霞
(北京交通大學 語言與傳播學院,北京 100044)
?
【文學·語言研究】
單音節動詞的句法—語義關聯:以“變”為例
李蘭霞
(北京交通大學 語言與傳播學院,北京 100044)
“變”在語料庫中的關聯模式顯示,“變”的特質屬性為[-控制],構成了“變”的主流用法;但同時,通過使用“讓、使、把”等語言手段,“變”派生出了[+控制]屬性,構成了“變”的非主流用法。“變”句法—語義關聯的特點反映了單音節動詞句法—語義關聯可能具有的基本屬性,為單音節動詞句法-語義關聯的系統考察奠定了基礎。
單音節動詞;句法—語義;關聯模式;語料庫;變
一、引言
1.句法—語義關聯的考察方式
詞匯尤其是動詞的句法—語義互動可以說是語言學研究中的核心論題之一。
詞匯語義學1和詞匯驅動的語法研究認為,許多語法現象可以由詞匯語義預測或決定(張麗麗、陳克健、黃居仁,2000),比如動詞論元的句法實現——它們的句法類型和語法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從動詞的意義來預測(Levin &RappoportHovav,1996)。但同時,“很明顯,只有意義的特定方面才浮現為句法現實,成為研究的目的”(Mei-chun Liu,2003)。那么,怎樣才能確定和句法表現相關的詞匯意義呢?
Mei-chun Liu(2003)認為有五種方法可以考察和句法相關的語義:“Fillmore & Atkins(1992)的框架語義學(frame semantics),Levin(1993)基于替換的方法(alternation-based approach),Jackendoff(1990)的概念結構和局部歸因法(conceptual structure and the localist approach),Pustejovsky(1995)的生成詞匯學(generative lexicon),以及Biber et al.(1998)基于語料庫的方法(the corpus-based approach)”。其中,基于語料庫方法的支持者(如:Biber et al.,1998)相信,一個動詞的意義會被投射在它的“關聯模式”(association patterns)中。所謂“關聯模式”,是指某些語言特征和其他語言、非語言特征相結合的系統方式(Biber et al.,1998:5),而這些“關聯模式”可以在大規模語料庫中找到。這樣,基于語料庫的“關聯模式”的統計學計算就可以揭示語義差別(Mei-chun Liu,2003)。①張麗麗等原文所用為臺灣譯法的“詞匯語意學”,這里采用大陸通行的“詞匯語義學”。
本文以“變”為例,通過對“變”在語料庫中關聯模式的統計分析,考察其句法—語義之間的關聯和互動,并以此為基礎對單音節動詞句法—語義關聯的基本屬性進行初步探討。
2.動詞“變”的基本特點
本文之所以選擇動詞“變”作為出發點,是由于該動詞同時具備語義和句法上的簡約性和彈性。《現代漢語詞典》(第5版)(2005:83)對“變”的釋義如下:

可以看到,“變”的九個義項中,只有①—③屬于作為動詞獨立使用時的義項,④—⑧都為“變”作為構詞語素時的義項,⑨則是一種姓氏。雖然可以把成詞和不成詞兩種情況統一起來進行全面考察(朱彥,2006),但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考察“變”作為動詞獨立運用的情況,即只涉及前三個義項。
從前三個義項及其舉例來看,“變”的意義和一般的多義詞并不相同。比如動詞“出”的義項中包括“從里面到外面”和“超出”兩個有明顯區別的義項,彼此之間雖然有聯系,但無法用近義詞來釋義。而“變”的前三個義項,其核心意義并無這樣明顯的區別,比如義項②和③都可以納入①中“和原來不同”這種釋義范圍;且三個義項的釋義都使用了“改變”這一詞。因此,“變”三個義項的主要區別并不在于意義,而在于句法形式,比如義項②和③一般都要帶賓語,③有使動用法。也就是說,“變”作為動詞獨立使用時其實接近于單義詞,意為“和原來不同”。
“變”接近于單義詞這一特點使得本文的研究可以集中在句法—語義本身的關聯上,避免了義項之間的聯系導致的復雜性;但“變”的意義在使用中又有一定的變化,其用法不像一般的單義詞那樣單一,使得句法—語義之間的關聯具備一定的彈性,構成了句法—語義關聯豐富性的基礎。
二、“變”的語料分析
首先,我們以“變”為關鍵字在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現代漢語語料庫中進行搜索,截取前1 000條語料,其中“變”共出現1 247次,排除2例人名后剩余1 245例。然后從1 244例中去除“變”作為復合詞語素的749例,剩下作為詞獨立使用的用法496例。最后,排除1例屬于古代漢語的名詞用法(“玄武門之變”),剩余的495例都為動詞用法,即為本小節進行關聯模式分析的語料。
張麗麗、陳克健、黃居仁(2000)提出從“特質屬性”和“角色內部屬性”兩個方面來界定動詞的語義,特質屬性“和動詞核心概念緊密相關”;角色內部屬性則“指角色本身的特性”,“會影響到動詞的使用情況”。[±控制]和[±意志]分別是一組能對大多數動詞的語義進行界定的屬性,其中特質屬性[+控制]“指主事者可以操控該動作或狀態”;角色內部屬性[+意志]“指主事者具有行使此動作的意圖”。語料分析發現,動詞“變”主要為[-控制],但也可以為[+控制],兩種屬性的“變”分別具有不同的角色屬性和關聯模式。
1.[-控制]“變”
[-控制]是“變”的主要屬性,共401例用法,占495例用法的81%,共有以下七種關聯模式(S=主語,O=賓語,C=補語):
(1)S+變。
如:忽然,光線變了。
(2)S+變+O,O為名詞,表經驗者。
如:他變了臉色,沉默了大約5分鐘。
(3)S+變+O,O為名詞,表結果。
如:雌魚變雄魚的秘密在哪里?
(4)S+變+成/為+O,O名詞,表結果。
如:他被人利用了,結果變成蔣介石走狗了。
(5)S+變+C,C為形容詞,表結果。
如:眼看從家里帶來的錢一天天變少,我開始著起急來。
(6)S+變+得+C,C為謂詞性結構,表狀態。
如:北京對于她來說變得沒有了—點生氣。
(7)S+給+變。
如:現在有好些個這年輕的小孩兒說話都給,都給變了。
七種關聯模式的使用頻率和所占百分比如表1。可以看到,(4)是最高頻用法,比例高達41.4%;(6)、(1)、(5)次之,分別占20.4%、20.2%、15.7%;(2)和(3)所占比例則非常低,僅為0.5%、1.5%。以上關聯模式都可以與“了”共現,加“了”之后,都表示事物變化之后新的事物或性質、狀態的延續。

表1 [-控制]“變”的關聯模式
根據論元數量和表達的結構意義,[-控制]“變”的關聯模式可以歸納成四類。
第一,一元結構,其參與角色為【[-意志]經驗者】。該結構表示論元的狀態開始發生不可控的變化,變化后的狀態繼續存在,但是變化后的具體狀態未知,包括(1),占20.2%。
第二,二元結構,主語的參與角色為【[-意志]經驗者】,包括(2)、(3)和(4),占43.4%。其中(3)和(4)賓語的參與角色為【[-意志]結果物*“結果物”即張麗麗、陳克健、黃居仁(2000)文中所指的“漸生題旨”,本文這里采用較能見文知義的說法。】,(2)則為【[-意志]經驗者】。又可分為兩類。
A.該結構表示賓語論元的狀態開始發生不可控的變化,變化后的狀態繼續存在,但是具體狀態未知,指第(2)類。(2)的一大特點是,主語和賓語之間有“整體”和“部分”的關系;而“變”的直接參與角色只是處于賓語位置的“部分”,“整體”的變化是通過“部分”的變化反映出來的。從語法上看,賓語位置的“部分”都可以提前到主語的位置,或者作為謂語部分的小主語,比如:
1)他變了臉色。——他的臉色變了。——他臉色變了。
B.該結構表示主語從事物A轉變成另一種不同的事物B,B繼續存在,包括(3)和(4)。二者的區別在于“變”后是否帶“成/為”。“成”的隱現規律決定于“成”后面的論元是否是簡單結構:如果是簡單結構,則“成”可以省去;如果是帶有修飾語的復雜結構,則“成”不能省去,如:
2)仿佛看到了茫茫沙灘并不遙遠的未來——沙漠變綠洲/沙漠變成綠洲/沙漠變成豐美的綠洲/*沙漠變豐美的綠洲。
3)誰要是被她看上一眼,就會變成一塊石頭/就會變成石頭/就會變石頭/*就會變一塊石頭。
第三,一元結構,主語的參與角色為【[-意志]經驗者】。該結構表示主語從狀態A轉變成另一種不同的狀態B,B繼續存在,包括(5)和(6),占36.2%。
第四,一元被動結構,主語的參與角色屬性為【[-意志]經驗者】。該結構表示經驗者被動地發生了某種變化,包括(7),共1例,占0.2%。這時,“變”之前需要使用表示被動意義的“給”,但不能使用“被”。
總的來說,[-控制]“變”最多可有兩個參與角色,出現在主語和賓語位置,其屬性都是[-意志]。
2.[+控制]“變”的關聯模式
[+控制]“變”的用法共94例,占“變”作為單音節動詞495例用法的19%。共有以下幾種關聯模式:
(8)S+能愿動詞+變(+C/數量O)(2例)
如:我得變,只是變化需要時間。
(9)S+變+O,O為名詞,O表對象(2例)
如:楊政委望著周大勇那急迫的神氣,突然變了口氣。
(10)S+把+O+變,O為名詞(12例)
如:我不知道她從哪里搞到了我的手機號碼,于是把號碼變了。
(11)S+把+O1+變+O2,O2為名詞,表結果(14例)
如:水把沙漠變了良田。
(12)S+把+O1+變+成/為+O2(38例)
如:外星人所到之處,就把那里變成了一片廢墟。
(13)S+使+O+變+C(11例)
如:而沙漠卻使人類的生存空間變小。
(14)S+讓+O+變+得+C(18例)
如:當然也有權利讓自己、讓家人的生活變得更美好。
七種關聯模式的使用頻率和所占比例如表2。可以看到,(12)的使用頻率最高,占40.4%;(14)、(11)、(10)和(13)所占比例基本屬于一個數量級,都在20%-10%之間;(8)、(9)所占比例非常低。以上關聯模式都可以和“了”共現,和[-控制]“變”一樣,加“了”之后都表示事物變化之后新的事物或性質狀態的延續。

表2 [+控制]“變”的關聯模式
根據論元數量和表達的結構意義,[+控制]“變”的關聯模式可以歸納成三類:
第一,一元主動結構,主語為【[+意志]主事者】。該結構表示主語有意識地進行變化,包括(8),共2例,占[+控制]用法的2.1%。這時,“變”之前需要用能愿動詞,如“要、想、能”等;“變”之后可以沒有別的成分,也可以有補語或數量賓語,如:我想變漂亮一些。
第二,二元使動結構,主語為【[+意志]主事者】,“變”的直接賓語或者介詞“把”、動詞“讓、使”后的賓語為【[-意志]對象】。該結構表示主事者使對象發生某種變化,包括(9)、(10)、(13)、(14)。又可以分成兩個小類:
A.表示主事者使對象發生變化,變化后的具體狀態未知,但該狀態繼續存在,包括(9)、(10),共12例,占14.9%,且二者的結構可以自由轉換,比如:
4)楊政委望著周大勇那急迫的神氣,突然變了口氣/突然把口氣變了。
5)我不知道她從哪里搞到了我的手機號碼,于是把號碼變了/于是變了號碼。
B.表示主事者使對象轉變成另一種狀態,該狀態繼續存在,包括(13)、(14),共29例,占30.9%。這兩種結構也都需要使用動詞“讓、使”或介詞“把”引出對象;“變”和“變得”之后需要使用的成分分別為形容詞和謂詞性結構。
第三,三元使動結構,主語為【[+意志]主事者】,“變”后的賓語為【[-意志]結果物】,介詞引導的賓語為【[-意志]對象】,表示主事者使對象從一種事物A轉變成另一種事物B,B繼續存在,包括(11)、(12),共52例,占55.3%。這兩種結構都需要使用“讓、使、把”來引出事物A;“變”之后一般要用“成/為/成為”來引出變化之后的事物B,“成/為/成為”的隱現規律同樣決定于“成”后面的論元是否為簡單結構。
綜上所述,使動用法是[+控制]“變”最高頻的用法,三元結構占到所有[+控制]用法的一半以上,二元用法次之。在句子中使用“讓、使、把”等三個表示使動、處置義的動詞或介詞是使“變”具有[+控制]屬性的最常用手段;添加能愿動詞是使“變”具有[+控制]屬性的另一個手段,尤其是在結構(7)中,能愿動詞是必不可少的。[+控制]“變”最多可有三個參與角色,其主語位置的參與角色屬性都是[+意志];“變”后的賓語或句式中其他動詞“讓、使”、介詞“把”后的賓語則都是[-意志]。
三、討論
1.從[-控制]到[+控制]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控制]是“變”的基本屬性,構成了“變”的絕大部分用法;[+控制]是“變”的派生屬性,其用法僅占全部用法的不到五分之一。要實現從[-控制]基本屬性到[+控制]派生屬性的發展,必須在句法形式中有相應的發展。“變”句法形式發展有以下幾方面的特點。
第一,句法形式由簡至繁。可以看到,當表達[-控制]時,“變”的句法結構比較簡單:(1)-(3)都只有“變”一個動詞;(4)-(5)通過增加謂詞加入了補語:(4)增加了動詞“成/為”,(5)增加了形容詞;(6)的補語由于可以自由擴展,有可能比較復雜,但已經和“變”不在一個層面;(7)增加了介詞“給”表被動。總之,[-控制]“變”的句法結構中必不可少的成分不超過兩種謂詞。當表達[+控制]派生義時,關聯模式(9)和(10)在“變”之前分別增加了能愿動詞和“把”引導的介詞結構,(11)-(14)則在(3)-(6)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動詞“使、讓”或介詞“把”,這些增加的形式都成為句子中必不可少的成分。
第二,基本句法形式保持不變。雖然表達[+控制]派生屬性的句法形式發展得更復雜,但都是以[-控制]基本屬性的句法形式為基礎增加其他語言成分,并沒有對基本句法形式進行根本改變。而且,從表3的統計結果可以看到,基本句法形式與其對應的派生形式的使用頻率基本一致,比如在表達[-控制]時,關聯模式(4)使用頻率最高,由其發展而來的對應類型(12)在表達[+控制]時使用頻率也最高;(2)的使用頻率屬于[-控制]類的最低層次,和其對應的類型(9)也為[+控制]類的最低頻率;[-控制]類使用頻率最低的(7),從理論上來說也可以有[+控制]的對應形式,比如加入“讓港臺腔”這樣的語言成分,形成類似“好些個年輕的小孩兒說話都讓港臺腔給變了”的結構,但語料庫中未搜索到,說明該結構和(7)一樣,使用頻率都非常低。

表3 [-控制]和[+控制]關聯模式的對應
注:括號中為該類關聯模式占所屬語義類型的百分比。
第三,在各種關聯模式中,只有(2)、(3)和(9)即“S+變+O”這一句法形式可能有歧義,即該句法形式是[-控制]還是[+控制]需要上下文語境來確定。比如“他變了臉色”,如果主事者主動改變“臉色”,則“變”為[+控制],否則為[-控制]。
2.[±控制]和[±意志]的匹配
“變”特質屬性和參與角色屬性的匹配有如下特點。
首先,[-控制]屬性總是匹配【[-意志]經驗者】屬性的主語。當二者相匹配時,“變”的句法形式最多為二元結構,即主語和賓語,賓語可能直接由“變”支配,也可能由動補結構“變成/為”支配。
其次,[+控制]屬性總是匹配【[+意志]主事者】屬性的主語。當二者相匹配時,“變”的句法形式最多可為三元結構,即在主語和賓語之外,還有“讓、使、把”支配的賓語,都成為構成“變”句法形式必不可少的成分。
第三,不管是[-控制]還是[+控制]屬性,都可以和[-意志]屬性的賓語匹配。“變”句法結構中支配的賓語可以分三類,一類是【[-意志]對象】,“讓、使、把”支配的賓語以及使動意義的“變”直接支配的賓語都屬于這一類,這時“變”的屬性為[+控制];第二類是【[-意志]結果物】,這時“變”的屬性為[-控制],賓語由“變”或“變成/為”支配;第三類是【[-意志]經驗者】,“變”的特質屬性也為[-控制],賓語由“變”直接支配。
3.“變”與“了”的共現
根據前文的語料,“變”的14種關聯模式都可以與“了”共現,且不管“了”出現在句中還是句尾,都表示論元變化后新出現的性質、狀態或事物的延續,如:
6)忽然,光線變了。
7)楊政委望著周大勇那急迫的神氣,突然變了口氣。
8)他被人利用了,結果變成蔣介石走狗了。
其中例6)表示光線變化后的顏色、亮度等的延續,7)表示變化后出現的新“口氣“的延續,8)表示“他”成為“蔣介石走狗”這種新狀態的持續。一些原本沒有出現“了”的例句也可以加“了”,如:
9)眼看從家里帶來的錢一天天變少(了),我開始著起急來。
10)北京對于她來說變得沒有了—點生氣(了)。
11)我得變(了),只是變化需要時間。
12)而沙漠卻使人類的生存空間變小(了)。
加“了”之后,句子的基本意義沒有改變,只是強調句子所表達的新狀態開始出現并持續。
但另一方面,“了”作為一種必不可少的成分卻只出現在以下幾種關聯模式中,它們是:[-控制]類的(1)、(2)、(3)、(4)、(7)和[+控制]類的(9)、(10)、(11)、(12)。其中(3)的例句“雌魚變雄魚的秘密在哪里?”之所以沒有“了”,是由于“變”所在結構只是句子的定語出現,當單獨成句時則必須帶“了”。這9種模式中,由于[+控制]類都由[-控制]類派生而來,包含的基本句法形式相同,因此可以歸結為以下兩種句法結構:
S+(給+)變
S+變(+成/為)+O
而不需要“了”作為完句成分的關聯模式為[-控制]類的(5)、(6)和[+控制]類的(7)、(8)、(13)、(14),也可以歸納為以下兩種句法結構:
S+變(+得)+C
S+能愿動詞+變
也就是說,“變”是否需要“了”作為必不可少的完句成分,取決于“變”后是否有賓語、補語,“變”前是否有能愿動詞三個條件。當“變”后有賓語或無補語且前無能愿動詞,必須有“了”作為完句成分;當“變”后無賓語且有補語或前有能愿動詞,則不須“了”作為完句成分。前者的使用頻率為318,占495例用法總和的64.2%;后者的使用頻率為177,占35.8%,前者遠遠高過后者。
總之,“變”是否需要“了”作為必須的成句成分,和其[±控制]和[±意志]等屬性無關,主要和其基本句法結構相關。
4.小結
標記理論認為,語言中存在大量的無標記項和有標記項,二者有以下幾方面的區別:后者比前者出現頻率低;后者比前者結構更復雜;由于結構更復雜,后者在思維努力程度、注意力要求和認知加工時間方面要求也更復雜(王立非,2002)。從特質屬性的角度看,“變”的[-控制]和[-意志]屬性屬于無標記項,[+控制]和[+意志]屬性屬于有標記項;從句法結構形式看,“變”后有賓語或無補語且前無能愿動詞時,須用“了”為完句成分,是“變”用法的無標記項;“變”后無賓語且有補語或前有能愿動詞時,不須用“了”為完句成分,是“變”的有標記項。無標記項構成了“變”的主流用法。
從對“變”的考察結果出發,我們可以初步推測一般單音節動詞句法—語義關聯的基本屬性。
首先,每個動詞都有自己的基本語義屬性,是該動詞的無標記項,構成主流用法。但這種基本屬性并不是恒定不變的,在使用中可以通過一些語言手段使得該屬性發生變化,派生出其他屬性,構成有標記項,是該動詞的非主流用法。因此,張麗麗、陳克健、黃居仁(2000)對“快樂、喜歡”的屬性進行絕對性劃分的做法值得商榷。
其次,動詞的不同語義屬性都對應著不同的句法形式,基本語義屬性的對應句法形式比派生屬性的要簡單,即前者是無標記項,后者是有標記項。在語言教學中,前者是首先需要教授的重點內容。
最后,[+控制]與[-控制]可以構成動詞語義的一對基本屬性,其主語的參與角色屬性一般為[+意志]與[-意志]。當從[-控制]轉變為[+控制]時,常用的句法手段是通過“把、被、使”的使用使得動詞具有使動性。賓語一般都為[-意志],對于區分句法—語義關聯無區別意義,但其角色屬性是否結果、對象則有重要的區別意義。
對于單音節動詞句法—語義關聯的描寫具有重要意義。第一,單音節動詞是構成雙音節動詞的基礎,雙音節動詞的研究須以單音節動詞為基礎;第二,雙音節動詞由于包含兩個語素,語素之間在語義上可能存在抵消、融合、疊加等各種關系,使得雙音節動詞的語義相對更復雜;第三,不僅是語義,雙音節動詞構詞語素所帶的論元有時可能投射到句法層面,直接影響雙音節動詞的句法形式(朱彥,2006)。因此,單音節動詞比雙音節動詞更能反映動詞句法—語義關聯的基本屬性,同時為更復雜結構的動詞句法—語義關聯的描寫奠定基礎。
四、結語
本文基于語料庫對單音節動詞“變”的句法—語義關聯進行了考察,并以此為基礎討論了單音節動詞句法—語義關聯可能具有的基本屬性。
根據目前的初步結果,在未來的研究中,以下兩個角度的研究對于確定單音節動詞句法—語義關聯的基本面貌可能具有重要意義。首先,是否所有基本屬性為[-控制]的單音節動詞都能發展出[+控制]屬性,如果能的話可以使用怎樣的句法手段;其次,基本屬性為[+控制]的單音節動詞是否能發展出[-控制]義,以及如果能的話會使用怎樣的句法手段。對上述兩方面的問題的考察可以為動詞句法—語義關聯的描寫確定基本坐標,為全面系統的描寫奠定基礎。
[1]Biber Douglas,Susan Conrad&Randi Reppen. Corpus Linguistics: InvestigatingLanguage Structure and Use[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2]Chu-Ren Huang,Kathleen Ahrens,Li-li Chang,Keh-jiann Chen,Mei-chun Liu,&Mei-chih Tsai.The module-attribute representation of verbal semantics: From semantics to argument structure[J].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2000,5(1):19-46.
[3]Mei-chun Liu.From Collocation to Event Information:The Case of Mandarin Verbs of Discussion[J].Languageand Linguistics,2003,4(3):563-585.
[4]王立非.語言標記性的詮釋與擴展[J].外語學刊,2003(2):87-92.
[5]現代漢語詞典(第5版)[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83.
[6]張麗麗,陳克健,黃居仁.漢語動詞詞匯語義分析:表達模式與研究方法[J].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2000,5(1):1-18.
[7]朱彥.核心成分、別義成分與動作語素義分析——以“收”為例[J].中國語文,2006(4):313-320.
The Syntactic-semantic Associations of Monosyllable Verbs: An Example ofBIAN
LI Lanxia
(School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 China)
The association pattern of the verbBIANin the corpus shows that the basic semantic feature of the verbBIANis [-control], which produces its main uses in the corpus. While by using the words ofRANG,SHIandBA, the verbBIANhas developed the semantic feature of [+control], which produces the secondary us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syntactic-semantic associations of the verbBIANreflect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monosyllable verbs, which lays the foundation of the systematic examination on syntactic-semantic associations of monosyllable verbs.
monosyllable verbs; syntactic-semantic; association pattern; corpus;BIAN
2015-10-23
北京交通大學基本科研業務費人文社會科學專項研究項目資助(H13JB00010)
李蘭霞(1979-),女,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博士,講師,主要從事漢語詞匯與漢語第二語言習得研究。
H146
:A
:1008-469X(2015)06-004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