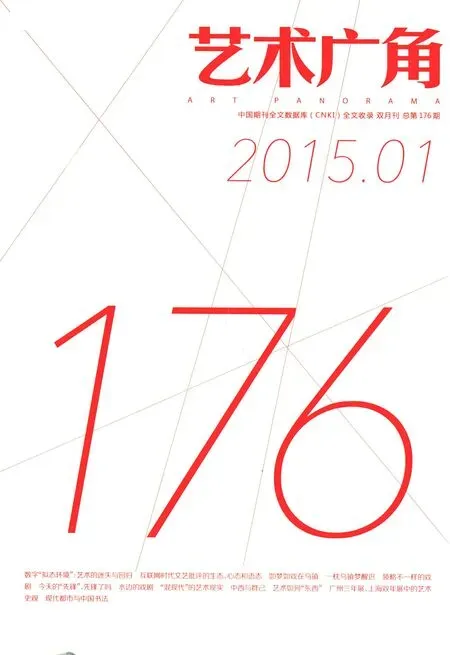水邊的戲劇
鐘一鳴
水邊的戲劇
鐘一鳴
鐘一鳴:供職于遼寧省藝術研究所,研究方向為先鋒戲劇。
從烏鎮回來,特別想寫一篇關于戲劇節的文章,可一拿起筆,卻又不知從何寫起。躊躇徘徊許久,我將這種情況歸咎于心靈深處作為普通觀眾的“本我”與當下作為一名戲劇工作者的“自我”的互相拉扯、彼此矛盾。我的“本我”,很享受那幾天的時光:我能夠打著藝術熏陶的“幌子”,整日游蕩在江南小鎮的白石橋和青磚小樓間,隨時駐足,品評街頭巷尾的即興表演。細雨朦朧的傍晚時分,匆匆踏過濕漉漉的青石板路,胡同深處的劇目即將開演,勾人心魂。而作為一個戲劇工作者,這些時日更多的則是焦急和遺憾,還有期許和慚愧。幾種情緒交織在一起,感觸唯“復雜”一詞可以形容。這“復雜”,要從“大戲”開始說起。
本次烏鎮戲劇節,“先鋒戲劇”為主。我看到的劇目有七部,其中大陸四部,《青蛇》《女仆》《一鳥六命》《開膛手杰克》,香港一部,《萬歷十五年》,國外兩部,《莎士比亞濃縮版》和《第十二夜》。毋庸置疑,其中最大的看點就在于田沁鑫、孟京輝和林兆華三位中國戲劇“領軍者”一同在“先鋒”的擂臺上競技。古往今來,明星是戲劇舞臺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戲劇作品的受重視程度和上座率多半是隨著編導演的名氣而來的。一方面明星效應是觀眾“從眾心理”的一種體現,另一方面“大師”的作品理所應當“物有所值”或“物超所值”,這樣觀眾花錢買票就有了心理保障,如同消費者愿意在市場購買帶有“質量合格”標簽的商品。
本次戲劇節上,田沁鑫的《青蛇》、孟京輝的《女仆》和林兆華的《一鳥六命》,三部作品在形式和主題上可謂大相徑庭,各有千秋,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代表了當今中國先鋒戲劇藝術的最高水平。如果讓我來評判的話,三部作品就像三分天下一般各占一方。《青蛇》占地利,《女仆》占天時,而《一鳥六命》占人和。
《青蛇》是我在烏鎮戲劇節上看的第一部作品。之所以占地利,是在水劇場的壯觀上。傍水露天的巨型舞臺,輕紗幔帳的朦朧和水中停泊的小舟上燈火點點,烏鎮水劇場為田沁鑫這部改編自白蛇傳說的《青蛇》做足了氣氛。而演員更是在劇場正中的水池中踏水表演,有江南獨有的清風細雨做伴,作為觀眾,我在長達兩個小時的觀看過程當中,一次又一次震驚于場面的奇異和靈動,甚至渾然不覺憑空增加的這4D效果(不允許打傘)有何不妥,真可謂占盡了地利優勢。
《女仆》占天時,原因有二。一是《女仆》的演出時間在午夜。本來《女仆》就是改編自日奈這位著名荒誕大師的作品,講述的是兩個女仆不斷扮演主人最后無法自拔的故事。法國人的怪誕和孟京輝式的先鋒交織在一起,在午夜的襯托之下透著詭異的幽光,令人期許之中夾雜著興奮。二是在《女仆》之前,觀看了長達三個小時的《萬歷十五年》,雖然該劇內核精彩并具有批判性,但是形式單調乏味,臺詞為粵語,字幕又看得人頭昏眼花。因此,風格多變的孟京輝《女仆》就更讓人向往。果然,孟京輝的形式真的是太多變了,真的是比任何形式都更講究形式。那種形式讓大家在通過午夜靜謐的胡同準備回去睡覺之前有了一致的感受,那就是被形式狠狠地打擊了一把。白色的布簾、巨大的銅鑼,四處飛濺的花生皮,甚至真正的冷凍豬肘,還有那首不著邊際的歌,讓人摸不著頭腦。
林兆華《一鳥六命》可謂三部戲當中最不先鋒的作品,樸實的裝束和簡單的舞美設計,讓人恍惚來到普通的現實主義戲劇當中。但《一鳥六命》從人物設計上,就明顯帶有“符號化”這一特征。符號是一種思維,化繁為簡而又留有余地。七種人性格被巧妙地陌生化,然后在情節的掩護下又默默回到故事當中,既能讓觀眾心曠神怡地看完故事,又能跳出來冷靜分析。我認為能讓大部分觀眾接受、理解、喜歡,《一鳥六命》算占有人和。
但就算如此,《青蛇》和《女仆》,還是對我的“自我”震撼較大的。“自我”的疑問非常明顯,中國的先鋒戲劇莫非要撇開故事做戲劇么?因為我看到兩位大導注重的并非故事,田沁鑫的《青蛇》勉強在講一個故事,但情節缺乏新意,依舊是老《白蛇傳》那一套。雖然以法海這個角度切入確為首創,但到底和劇名《青蛇》相差相當遙遠,或許改名叫《禿驢你到底懂不懂愛》會更讓人接受一些。孟京輝的《女仆》就更過分了。故事要靠開場之前發的一紙劇情提要來判斷。因為整個劇情被孟京輝徹底打亂了,打碎了,然后還不好好拼接。語言上的粗俗可以理解,但真正一塌糊涂就不妥了。孟京輝希望用午夜來闡述他的先鋒理念和他對荒誕的理解。然而當荒誕成為人們眼中的荒唐,戲劇故事只能靠場景來維系,戲劇的主題只能靠吶喊來讓觀眾感受,這樣的戲劇還能不能稱為戲劇呢?
《青蛇》和《女仆》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們恰恰體現了當下話劇界的兩大問題——過于注重場面、過于注重形式。毋庸置疑,場面和形式都是戲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并不是戲劇的全部或是重點。先鋒戲劇可以奇特,但不能拋開觀眾而獨立存在,愚弄觀眾思維或只滿足觀眾視聽上的需求都是不可取的,令人意想不到的故事情節和能夠引發人深思的主題才是關鍵。《一鳥六命》雖然在形式的新奇上略輸于《青蛇》和《女仆》,但其從故事入手的方式,作為先鋒戲劇的實驗效果絲毫不差,還帶有強烈的批判性。這足以說明先鋒是存在某種界限的——起碼,它不能以觀眾的全然不解作為成功的標志。
或許大導們自有大導們的意圖,年輕人參不透罷了,那就讓年輕人自己玩自己的吧。烏鎮戲劇節別出心裁地設計了青年競演單元。本次青年競演單元有著幾項特殊的規定,例如領隊導演年齡不得超過35歲,作品必須原創,作品命題式,必須含有“帽子”“看不見的門”和“一件樂器”三樣東西。用競賽的模式選出12部劇同臺PK,最終決出冠軍。當然,冠軍的獎金是豐厚的,但我認為青年戲劇工作者更多關注的是如何用這個平臺來自我展示。
青年競演單元,我看了其中五部作品,形式的多樣性自不必說,整體呈現的效果也令人驚異,讓作為同齡人的我羞愧萬分。以獲獎作品《跳墻》為例,無論主題思想的深刻性,還是演員的表演水平,都堪稱佳作。作品以一個被寺院收養的小和尚準備跳墻逃下山去之前復雜的心理狀態為切入點,用兩個女孩分別飾演這個小和尚靈魂當中的兩個對立面,一唱一和重疊往復。臺詞像是汪曾祺作品《受戒》那種畫面感極強的詩性語言,再佐以女孩曼妙的極富禪意的舞姿和不時輕撫的古箏。整個作品給人一種震撼,又不乏心曠神怡的感覺。雖然有一些小的瑕疵,但《跳墻》仍不失為用心之作,讓人難以忘懷。
毋庸置疑,在藝術創作依然崇尚權威的今天,留給年輕一代戲劇工作者的空間是不大的,尤其是剛步入戲劇工作行列的新人,可供表現的機會更是少之又少,就如同《爺爺歷險記》中賣力演出的演員們,我能看出他們的每一個動作都是帶著激情。在這個戲劇不斷萎縮的時代,年輕戲劇工作者的成長需要提速,而提速的方式就是真正獨立自主地創作排演戲劇。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學習觀摩的次數再多,不如真正排演一部戲來得快,青年競演單元恰恰提供了這樣一個平臺和目標。《開膛手杰克》在此次戲劇節成為大戲,而它的主演陳明昊就是從青年競演中脫穎而出的導演,這樣的人越多,中國戲劇才會越有希望。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烏鎮戲劇節推動了中國戲劇,尤其是青年戲劇的創作發展。
先鋒戲劇之“先鋒”二字,從字面上理解,“先”是超前和創新,“鋒”是銳利和批判。既超前又銳利的戲劇,我認為更符合年輕人的理念。偏激一點講,先鋒戲劇若想在中國發展下去,非年輕人不可勝任。因為先鋒擔任的是實驗的任務,實驗的重點是探索,而探索是需要極富冒險精神的人來做的,是需要輸得起的人去做的。這樣,先鋒戲劇才會不斷發展和創新。就如同《西》《怪獸》《半獸人》的出現一樣,尊重年輕人的創作,更多的原創劇目才會被創作出來,而不會只停留于改編(幾乎我看到的大戲全都來自改編)。
中國戲劇已經在水邊徘徊了,也快到了“背水一戰”的時候了。當大家都在尋找培養戲劇土壤方式的時候,烏鎮戲劇節找到了一種途徑。它培養了大批學生觀眾群體,擴大了戲劇在中國的影響力。大量的高校學生前往觀看,事實上是一種回歸,回歸中國戲劇發源地——校園。
再后來,我不再糾結于“本我”與“自我”,他二人各得出了結論。從“本我”來講,烏鎮有戲,可觀之。從“自我”來說,戲劇之未來,烏鎮“有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