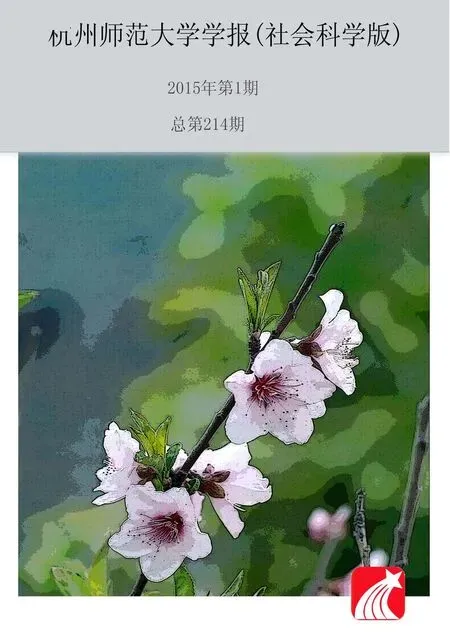外國文學研究的元方法論——一個系統論視角
范 勁
(華東師范大學 中文系, 上海 200241)
?
文藝新論
外國文學研究的元方法論
——一個系統論視角
范勁
(華東師范大學 中文系, 上海 200241)
摘要:由盧曼的系統論視角,可以考察作為一個知識交流系統的外國文學研究的整體運作。外國文學研究的方法論,其實包含了三個層面:方法、理論、超理論。從超理論層面來統觀,外國文學研究的交流過程被理解為退出/進入和異域/自我的雙重循環,這種循環交替構成了一般主客認識的基礎和一般方法論的元方法論。在此理論框架內,試圖解決困擾當代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的幾個重要問題:1.“失語癥”命題;2.反對理論;3.翻譯研究的定位;4.問題意識;5.中國文化立場。最后,提出連接盧曼系統論和中國傳統思想的可能性,并且揭示了新整體性思想在當代西方理論場中的潛在脈絡。
關鍵詞:外國文學;系統論;超理論
一、作為交流系統的“外國文學”及自我觀察的程序
談論外國文學研究的方法論,必須由一個基本悖論出發。首先,沒有實體性的“外國文學”,由此可推出,外國文學作為研究對象不存在;然而,另一事實是,研究外國文學者人數甚眾,從這個角度來說,外國文學又是一個實在的建構對象。如何處理這一悖論,需要思維框架的變換。
對于外國文學的蔑視,常來自于國別文學的研究者。外國文學的概念看起來不倫不類,不倫不類是因為超出了傳統西方學科的建制。“外國文學”(現在常常被稱為“世界文學”)學科以及相關的“外國文學史”、“外國文學作品選讀”課程的設立和長期存在,是一個特有的中國事物(吳元邁甚至提出要建設一種“外國文學學”)。在英、法、德等傳統西方文化體的學院體制內,盡管有比較文學,卻很少有綜合性的“外國文學史”。但是不應忘記,任何學科設置都隱含了一種世界秩序的規劃。外國文學概念所表達的,是我們身處的社會系統對整體文化秩序的意識形態需要,是一種對世界文化進行統觀的宇宙主義理想。不應忘記,“世界文學”規劃及各種世界文學選集的編撰在同為世界性大國的美國,也受到了高度重視。
顯然,這里的外國文學不能從經驗意義上去理解,它不是英國文學、德國文學、俄羅斯或是阿根廷文學等任何一種具體的文學形態,而如同“世界文學”或“文學性”、“美”,說到底只是一種象征性的交往媒介,正因為沒有物質性載體的限制,才適合普遍的交流需要。這種交流將外國文學研究者、翻譯家、讀者、出版者、作家們結合在一起,共同從事于意義的構建工作。這種意義,也就是人與人、文本與文本、文化與文化之間的普遍聯系本身。外國文學由此成為一個自我區分、自行演變的功能系統。
外國文學若是一個特殊的交流系統,外國文學研究就成為稱之為“外國文學”的整個交流過程的一部分,如何研究外國文學就是如何進行有效的自我觀察,而這必然導致在基本概念和思維方式上的急劇轉換。為了減少轉換造成的不適應,首先要對所涉及到的基本理論問題進行一些簡單梳理。
“文學”是價值生產的機制,生成從意識形態、教育到娛樂、消費等各方面的價值,但它所生產的最重要價值是一種對“現實/虛構”之雙重結構(伊瑟爾)的超越性。生活中解決不了的疑問,理性不能企及的知識,將按照經濟學原則分配到“文學”機構,以文學性彌合現實和理念的鴻溝,突破固有的界限和可能性。那么,外國文學在此機制中實現怎樣的功能?又在何種意義上區別于文學?不妨說,外國文學是一個由系統指定的文學“異托邦”,它以自我/異域的區分原則為前提,專門經由自我/異域的交流而達到整體,而有別于文學作為現實/虛構的二元結構。“異域”成為外國文學獨有的語義要素,而英、德、俄等民族文學不過是異域性的更具體、更細分的象征物。
承認外國文學作為整體系統的存在,才能進一步談論外國文學的方法論問題。外國文學研究的方法論,其實包含了三個層面,即:(一)方法;(二)理論;(三)超理論。以往在探討方法論問題時,往往混淆不分。
何為方法?方法即第一級觀察。觀察的實質為區分,必由某一區分標準出發,但方法以為自己是全然中立的,只服從于實踐需要。這就是說,在認識和對象的關系上,方法被設定為從屬于對象,是為了達成現實目標而履行的步驟。作為具體執行者,它無需檢驗自身的成果,即按照一定的形式原則返觀局部成果的連貫性,這種檢驗屬于第二層的觀察即理論的范疇。方法代表了對世界的直接感知,在直接感知中沒有真/假的判斷。而理論屬于科學的交流系統,能夠借助隱喻超越一般的因果邏輯,完成自身的封閉,這一點在人文學科領域體現得尤為明顯。*伊瑟爾指出,人文學科的理論的一大特性,是必須要借助于隱喻來完成自身的封閉,實現系統的完整性,譬如維特根斯坦的理論完全奠基于語言作為游戲的隱喻。參見伊瑟爾《怎樣做理論》,朱剛、谷婷婷、潘玉莎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7頁。隱喻其實是系統的原始代碼,它體現了理論和對象在根本上的非同一性,并使理論在對象的眼里成為一種虛構。即是說,理論的首要目的并非適應現實對象,而是構成和外界相區分的系統本身,一個完整、自覺自主的系統才稱得上理論。反之,方法只能在一套理論體系中才能工作,其作用方式是事先就規定好的。方法的成功貫徹的前提,就是放棄反思,不但要忘記為其提供特定區分標準的理論源頭,還要通過自身的成功實施,幫助理論掩飾其虛構特性。
理論是第二級觀察,即觀察的觀察,同樣基于區分原則。理論之為理論,在于能分辨真和假。理論檢驗——也即連接——方法的操作結果,給予解釋和評判,也討論方法本身,由此進入科學交流的層面。理論是簡化世界之復雜性的模式,也只有在簡化的前提下才能展開自身的復雜性。不同的理論方向意味著不同的化簡方式,或者說生成復雜性的程序。但是理論須在已經假定為文學的領域中發生作用,是文學系統內進一步細分的媒介,顯然任何理論都不涉及文學/非文學(系統/環境)的最初區分,換言之,文學理論事先就排除了整體性的文學世界。這一點令它陷入了自相矛盾,因為文學的本性即整體性,是虛構和現實的合一(故弗·施勒格爾稱文學為“宇宙詩”)。理論放棄了文學本身,遺忘了系統/環境的原始區分,才能獨立發展自身的觀察程序,這是其巨大效力的秘密,但它又必須以文學為隱蔽框架。故排斥不等于忽略,“否定就其自身來說已經是一種標示的形式,這種標示的形式強調了肯定和否定的區分”。而最終的框架——世界的整體性——雖不可能在反思中現身,卻是一切理論性區分和標示的前提。[1](PP.372-373)
要觀察整體,要在整體中觀察理論對文學世界的具體區分,不可能依據另一種理論,而必須走向“第三級的觀察”。*參見Niklas Luhmann, Die Wissenschaft der Gesellschaft, 3. Aufl.,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98, P. 485。 盧曼說:“當代碼(Code)自身造成了一種第二級的觀察,即一種對于觀察之條件的觀察時,身份反思(Identitaetsreflexion)卻關涉一種第三級的觀察,這一級秩序包括,第二級的觀察者如何解決同義反復的推論的問題,即自我參照的問題。”第三級的觀察者觀察第二級的觀察者如何觀察,如何排斥其他觀察,或者說,基于觀察的系統如何形成。只有在這一層面才可能反思整體,然而這也是一個不可能的整體——是在整體之內對于整體的建構。第三級觀察意味著科學系統內部的進一步分化,理論為消除(或掩蓋)自身的封閉性和宇宙生命的統一性之間的悖論,創造了新的觀察層次。第三級觀察實際上是第二級觀察的一部分,但這一概念代表了理論系統連接生命系統的愿望。在“自我參照”(Selbstreferenz)和“外來參照”(Fremdreferenz)之外,盧曼還提出了“元參照”(Metareferenz)的概念,“元參照”乃是對自我參照和外來參照進行統一觀照的層次。這一層次,說到底就是系統的自主性或“自動生產”(Autopoiesis)本身,它體現為系統內部結構所決定的自我參照/外來參照、系統/環境的永恒交替。[2](P.290)20世紀各種新的思想傾向,從主體間性到歷史主義、相對主義,表面看來是所謂反整體主義,究其實質不過是以一種新的參照打破系統的自我參照,故并未觸及“自我參照”/“外來參照”這一原始區分,換言之,標舉為新范式的反整體主義未曾觸及整體本身。這一層面上的反思,構成了盧曼的一個晦澀概念——“超理論”(Supertheorie)。[2](P.389)我們通常講方法論,指的是作為第二級觀察的理論的形式,卻忽略了對于理論觀察之觀察的法則,事實上,不斷跳出現有觀察層面,走向第三級、第四級乃至無窮級的觀察,代表了一種深層的方法論。文學系統對于人類認識論的獨特貢獻正在于此,因為文學是觀察和自我觀察的復雜游戲,在文學領域,以思維和存在、認知和對象的吻合為主題的傳統認識論失去了意義,需要探討的是以觀察、自我觀察、觀察之觀察為運行模式的系統何以可能的問題。如果在文學中也有所謂“認識”,那就是“一種不斷地區分眾多區分的操作,而最終——幾乎是在傳統的真理論意義上——是一種對于人們憑借某種區分能觀察什么和不能觀察什么的區分”。[2](PP.507-508)恰恰對于不可觀察者,文學有著難以割舍的情感。
文學作為文學的特別之處,在于對“內在性”(Innerlichkeit)的向往。內在性實有兩義,其一是作為無限的整體性在意識上的投射(有點類似王陽明講的“良知是無盡藏”,即作為整體性的天在人心中顯出來的“用”),其二是理論對整體性的概念性模擬。第一義不可說,第二義才是可說的。作為整體性在意識層面的顯現,內在性超越一切,囊括過去和未來、意識和潛意識、大地和世界,卻無法被理論所觀察,因為它屬于人的內在意識,即盧曼所謂的心理系統。理論則屬于社會系統。社會系統的運轉通過交流,而心理系統的運轉通過意識過程(認知、思考、感覺、意志、注意力),兩者都遵循“自動生產”原則,不發生直接關聯,心理系統的感覺、認知僅僅是實現社會系統交流的前提。換言之,文學理論作為交流由交流本身造成,并不能傳達內在于意識的認知過程。但人的意識和理論系統之間仍然有著互動可能,即環境和系統間的“結構性聯接”(strukturelle Koppelung)。通過這一受結構制約的聯接,作為環境的心理系統得以對文學交流系統施加影響,但又不妨礙后者自主運行。這種可望不可即的特殊關系成了文學的主題,文學作為一種默會的交流系統,所交流的就是接近內在性的不同方式,以此和一般紀事、歷史、新聞區別開來。按照柯勒律治對于詩的定義,詩的天才以良知為軀體,幻想為外衣,運動為生命,想象力為靈魂——這個靈魂將一切合為優美而機智的整體:
他(指詩人)散播一種整體的語調和精神(a tone and spirit of unity),他依靠一種善于綜合的、神奇的力量,即我們專門稱為想象的力量,促使各物混合并進而溶化為一。這種力量……善于平衡和調和相反的、不協調的品性,例如同與異、普遍與具體、理念與意象、個別性的與代表性的、新奇感與舊的熟悉的事物、不尋常的情緒與不尋常的秩序……[3](PP.179-180)
但其實,包容一切的想象界,不過是想象的想象,即系統本身對于無限的內在性的模擬,這就是內在性的第二義。文學以虛構把握“想象”,文學理論以自身的程序安置“想象”。理論總抱有錯覺,認為能擁有或接近內在性,故總是不滿于自身,又因為能輕易地看到理論和內在性的差距,故總是感到有必要排除其他理論。就這樣,內在性雖不直接參與交流,卻作為刺激性因素時時“干擾”理論的展開,構成一個超出理論系統的外在環境。系統和環境之間的“結構性聯接”為語言媒介的固有功能,但在日常語言實踐中處于被忽略的自動狀態,只有超理論的觀察能讓它顯現,在此意義上,也可以說超理論制造了“結構性聯接”。超理論本質上是理論的一部分,即理論系統指定來完成與環境的溝通的理論。每一理論都依賴超理論的渠道來實現和意識的接觸,它也就起到了整合的作用。反過來,超理論又能以一種可控制的方式去刺激意識,使意識在維持自身的系統運轉的同時,對于加入理論系統的交流過程也始終抱有興趣。須知,當代文學理論無論多么功能化,實際上還是揣有一個隱秘愿望,即以理論允許的方式創造一個對應于內在性的無限狀態,因為這一“無限”——這一共時性整體——乃是社會分配給文學機構的價值。換言之,文學理論必須照顧到文學的天馬行空的想象特性,現實/虛構的文學代碼也應該成為辯證對立的文學理論相互聯系的紐帶。理論之所以能相互攻擊,爭執不休,恰恰是因為它們知道這種激進的交流方式不會破壞整體,反而是模擬生命運動之整體性的唯一方式。超理論則是這樣一個觀察層次,在此層次上,理論不再關注對象,而是返觀自身的行為方式及其和周圍環境間的互動情形。
二、系統運作的超理論框架
從超理論的立場來看,外國文學研究是一個退出/進入的交替過程。所謂退出/進入的交替,是指一旦進入一種針對文學作品的方法性操作,操作本身就隨時凝固為概念知識,從而置身于生動的交流之外,只有解構了這種知識,新的操作才能開始。故所要退出的,是文學場中的一切既定的理論程序。理論以概念為基本單位,一種理論就是按一種建構原則連接起來的概念體系。在理論的自洽性框架中,概念與概念兩兩相對又互相連接,連接方式就構成了特定的理論形式——如女性主義從性別角度,馬克思主義從階級對立的角度,存在主義從存在的本真性角度來進行連接。科學的基本代碼“真/假”和文學的基本代碼“現實/虛構”交替作用,造成了諸多在不同連接方式中展開的相對項(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古典-現代,詩意-散文,內容-形式,作者-讀者,等等)。文學體現為現實/虛構與真/假兩種區分形式的復雜游戲,文學相對于生活的現實(真)是虛構(假),這種虛構又代表了一種真的現實,從而使生活的現實淪為虛構(假),而倫理學的“善/惡”代碼也總是卷入游戲之中。無論文學理論之間的沖突多么激烈,它們都是“現實/虛構”與“真/假”兩對二元代碼的復雜調配,不同流派的文學理論不過是按照不同的局部程序(Programm)來實現這一對初級代碼(Code)而已。事實上,也只有借助另一種區分(如真/假),才能和文學的現實/虛構的區分形成區分,對文學的觀察才得以成立。故可以說,多虧了現實/虛構的區分,文學的內涵才無比豐富;多虧了真/假的認識論區分,文學對象才能被定義和判斷。通過區分形式的組合、分離、再組合,由科學和文學的代碼演化出一系列概念,構成一個潛在的、具有既定規則的語言系統。但如果認識到文學概念的象征性和系統的自我演變特色,對于概念的僵化信念,對于美學場域中一切既定位置的執著都會動搖。實際上,文學的“現實/虛構”代碼構成了文學理論的遺傳基因,“重新輸入”(re-entry)于每一次概念操作,故一切文學概念均分享了邏輯和想象的二元性,既是分析工具,又是文學虛構。文學概念因為同時包含現實/虛構兩項而成為一個象征。“象征即神秘化”*諾瓦利斯的格言,轉引自Niklas Luhmann, Die Wissenschaft der Gesellschaft, 3. Aufl.,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98, P. 189。,象征的眼光以神秘化統一對立項,而在邏輯眼光下,一切悖論均無可遁形,一切既存的文學定義、理論形式終會自行解體。
退出/進入實際上表達了一般文學研究的超理論框架,它相當于知識的凝固化和去凝固化的交替。超理論所關心的不是進入或退出某一形式,而是實現這一區分或交替本身。但是具體到“外國文學”的生成,還需考慮到一種特殊性。外國文學之為外國文學,不是因為它的異質性地理來源,而在于它受限于另一種超理論的交流框架。外國文學作為文學系統的自我分化,實際上是以異域/自我的區分對現實/虛構的文學代碼進行再加工的產物。外國文學研究除了以退出/生成的程序建構一般意義上的文學空間,還要實現其作為異域符碼的特殊含義,即實現異域/自我的區分。保持其異域性,意味著忠實于原文的意義結構,而這在一定程度上就等于,外國文學研究者在操作時,首先要據有國外批評家開辟的理論立場,進入業已確立的問題域和語文學框架。類似于文學的翻譯者,他必須在忠實于原文的基礎上發揮創造性,從事一種戴著鐐銬跳舞的藝術。某種意義上說,外國文學研究是沒有自身的方法論的,正如我們不可能拋開西方人的觀點,完全用中國古人評點小說的方法來闡釋《浮士德》——那就意味著創造了一部新的《浮士德》。
從靜止的觀點看,退出和進入構成了一種悖論,因為它們代表相互解構的操作方向,理論場因此成了意識形態交鋒的生死場,不同理論為了這一問題爭執不休:誰能正確地解讀文本?模仿和創造也構成一種悖論,從而導致研究者的身份困擾:外國文學研究者是西方殖民話語的代理人嗎?*易丹的言論在這方面有代表性:“外國文學研究在我們的文學乃至文化領域內所扮演的角色,正是一種‘殖民文學’或‘殖民文化’的角色……我們簡直是完美的外國文化的傳播者,是杰出的‘殖民文學’的推銷者。”易丹《超越殖民文學的文化困境》,《外國文學評論》,1994年第2期。然而,超理論作為對于系統身份的整體反思,其核心任務就是要解決系統自身的悖論。進一步說,知識本身就是悖論,因為知識代碼是“真/假”這一差異的合一,其悖論在于:不是通過某種神圣的外部標準,而只有通過不是假的,才能成其為真的。超理論超出于形式邏輯之處,就是要去理解:“即使其構成是如此悖謬:系統的自動生產仍然在繼續進行,甚至還納入了對于悖論本身的交流。”[2](PP.483-484)
解決退出/進入的關鍵在于引入時間概念。退出和進入的操作一旦涉及時間,就不再是一對悖論,而是相繼相續的生動過程,也就是說,時間才是交流過程中不同立場的聯系媒介。這就意味著,投入文學的交流過程本身,隨交流而沉浮,才是奠基性的認識活動。所有主客吻合意義上的靜態認識,都取決于交流過程本身的流動。
解決異域/自我的關鍵則是對于復雜性的理解。外國文學同中國文學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和研究主體之間沒有文化血緣的聯系,因此就剝奪了闡釋性操作的基本支撐。對于我們,來自異域系統的外國文學除了純語法層面的信息外,就是一堆漂浮的亂碼,沒有國外批評家提供的支點,根本無法立足——無法有效地化簡過多的復雜性。追隨外國文學源出地的批評家的基本立場,意味著復雜性的減少,然而“復雜性的減少正是復雜性提升的條件”,[4](P.121)這正是盧曼關于系統運作的著名論斷。只有主動進入另一種審美和認知傳統,服從“外國文學”媒介及其區分原則的限制,才能就外國文學的意義進行交流、協商,或者說,創造出外國文學的新的語義復雜性。實際上,外國文學在方法論層面的非自主,恰恰生動而貼切地模擬了現代社會的知識形勢,真實地反映了主體在自動分化、自我參照的知識系統面前無可避免的被動性,這就讓本文所討論的話題不僅具有了時效性,還帶上了預測性、實驗性和前衛性的意味。
退出/進入和異域/自我的循環交替保證了外國文學研究作為一種功能系統的運轉。然而長期以來,我國的外國文學研究均缺乏作為系統特征的自主性格。意識形態指令成為現實環境干預外國文學交流的最直接方式,對于方法、理論的選擇有決定性影響,如對于批判現實主義的偏愛,緊扣著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基本立場,而對于巴赫金的狂歡節理論或德里達的解構主義的熱情,也暗示了反宏大敘事的意識形態策略。甚至對于某種方法、理論的特性和功能的認知,也取決于外部的意識形態需要。袁可嘉在上世紀40年代是新批評理論的鼓吹者,在艾略特、瑞恰慈等人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套“新詩現代化”主張;但是到了60年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強調文學的工具性,新批評的藝術自治成了異端邪說。在環境重壓下,袁可嘉對新批評進行了嚴厲批判,斥其為“從壟斷資本的腐朽基礎上產生并為之服務的反動的文化逆流”。[5]而在新時期,審美和藝術維度獲得政治平反,袁可嘉和文藝界的理論姿態又進行了相應調整,新批評成為取代庸俗社會學的新的主導性范式。這種情形,當然談不上系統的自我分化和自動生產。
但外國文學必須保持相對獨立,才能維護自身作為系統的存在。一個悖論現象是,外國文學越是能作為獨立系統存在,就越能服務于社會整體。從知識發展的角度來說,文學系統自我分化出外國文學的子系統,不單是出于社會對于文化溝通的現實需要,更是知識體系自身展開的邏輯后果:一個能分化出自身的對立面并與之有效互動的系統,才具有自我更新的生命力。上世紀90年代中國理論界的文化研究轉向和后現代話語的登場,標志著意識形態的逐步淡出,外國文學研究的功能系統特征日益明顯,方法論的轉換日益成為學科系統內的自我生產。這當然不意味著和外部現實環境的脫鉤,而是說,系統自身的分化原則成為理論運動的主導原則,它決定了外國文學研究在何處、以何種方式和現實問題發生關聯。外國文學研究者一如既往地關心中國的社會沖突、性別關系、權力分配等現實問題,然而在當下語境中產生對這類問題的關注,首先因為它們是文學和理論界討論和爭執的專業話題,即源自于外國文學交流系統自身的結構性需求,而非完成某一指令性的政治任務。
三、外國文學研究方法的幾個關鍵問題
從超理論的角度來觀察外國文學研究,把外國文學研究視為一個功能系統的整體運作,關于外國文學研究方法的幾個重要問題就能得到解決。
(一)“失語癥”命題
曹順慶《21世紀中國文論發展戰略與重建中國文論話語》[6]、《文論失語癥與文化病態》[7]、《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的基本路徑及其方法》[8]等文發表后,關于“失語癥”的討論已成為中國的外國文學、比較文學研究界在方法論反思上取得的重要成果,它觸及到了系統能否適應過度劇烈的知識變動的問題。但實際上,“失語癥”恐懼源于概念層次的混淆。中國學界強調的“失語癥”,既不會發生在方法層,也不會發生在超理論層,而是理論層面上的特殊現象。在最深層的超理論層面上,沒有“失語”者。反過來說,如果在這一層面發生了“失語”,那就是真正的民族的夢魘,因為它意味著系統的崩潰。可惜,多數“失語癥”論的追隨者并未從系統整體的角度來深入探討這一問題,而更多地停留于現象描述和文化意識形態批判的層面。事實上,“失語癥”的提出本身就是系統對失語的自我糾正,系統是一刻也不會失語的,因為那就意味著系統的死亡。曹順慶近年來的《論“失語癥”》[9]、《失語癥:從文學到藝術》[10]等文中已經體現出元理論思考的企圖。曹順慶指出,能夠提供源頭活水的并不是一般的“風格”、“妙悟”、“意境”等中國古代文論范疇,而是超越于范疇的深層文化規則,范疇會消失,規則卻會永續[9](P.79),這是高明的見解,同時也說明,他反思“失語癥”的重心已逐漸由最初的理論觀察(古代文論)層面轉到一個超理論層面。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真正的道(盧曼的“元參照”)寓于立場轉換所暗示的動態的整體性。
(二)反對理論
理論之為理論,在于能分辨真和假。這一區分依據具體程序得以實現,不同的區分程序,構成不同的理論訴求(而方法尚未達到區分原則的自覺,無法在自我參照和外來參照之間進行區分),如女性主義文學理論以女性/男性為區分程序,原型批評以原型/非原型為區分程序,后殖民理論以殖民者/被殖民者為區分程序,心理分析以意識/無意識為區分程序。但區分意味著排他性的選擇,故理論必然“偏頗”,站在方法和實踐的立場來說,一切理論都是荒謬的。
以方法反對理論,或者說以具體現象反對理論的策略,在美國的文學批評界表現得很明顯。一個代表性例子是韋恩·布斯在英譯《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導言中對巴赫金的責難。布斯說,巴赫金的對話和復調理論的缺陷在于,它無法解釋,為何也有許多優秀作品是獨語性的。但是他顯然忽略了,理論不僅預先設定了自己的現象,也設定了接近現象的方法。在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前提下,獨語就只是對話的一種特殊形式,即自己和自己的對話。故我們可以在理論的層面反對巴赫金理論,或者說,以否定的方式和巴赫金理論發生聯系,但決不能拿“現象本身”為依據,說它違背了現實,因為一種理論就有一種相應的現實,不存在一種對所有理論而言都是共通的、既定的文本現實。[11]中國的外國文學界在2000年前后一度響起“反對理論”、“回到文本”的呼聲,號召重新拾起利維斯式的細讀傳統,以為治療理論片面性的良方是只關注方法的實用批評,犯的是同一種理論幼稚病,其根源仍然在于概念層次的混淆。實際上,方法不能反對理論(除非以方法為理論),反之理論有資格取消或改變方法,因為它處于方法之后的觀察位置,而方法從本性上說對于理論是盲目的。正是方法和理論脫鉤,保證了方法的嚴格性和中立性。
(三)翻譯研究的定位
當代外國文學和理論界對于翻譯問題的過分關注,其實質并非翻譯技術本身,而不過是后哲學時代探討個體與個體、個體與普遍的溝通問題的新方式。盡管翻譯研究看起來比外國文學批評更具有實證性,但翻譯的可能性更像是意識形態問題而非真實的學術問題。毋寧說,翻譯不過是交流可能性的一個具體象征,有了交流問題,才有翻譯是否可能的問題。外國文學一方面造成自我的雙重化(自我/異域),同時又以溝通來消除雙重化,兩者是二而一的——要合一,首先就要造成分隔的事實。
由整體性立場出發,可以設定一種普遍性的外國文學體系的存在,而文學翻譯就是這種可能性的表達。以下引文出自一個世紀前英國牛津大學的教授穆爾頓之口,作為普遍性的世界文學最早的擁護者,他的辯護立場頗具代表性:
現在,有一種普遍的感覺,認為讀翻譯文學是一種權宜之計,是二手學術的救星。但這種想法本身就是迄今為止占上風的分科研究的產物,在這種分科研究中,語言和文學如此緊密地纏繞在一起,很難將它們分開來思考。這種想法卻經不起理性的檢驗。假如一個人不是由希臘文,而是由英語去讀荷馬,他無疑會失去一些東西。但問題在于:他所失去的是文學嗎?顯然,相當一部分構成文學的東西并未失去,如古人生活的呈現,史詩敘事的動感,英雄人物和事件的構想,情節設置的技巧,詩的意象——所有這些荷馬文學的要素都向譯文的讀者敞開著。但是據說,語言本身就是文學中的主要因素之一。的確如此,但要記住,“語言”的概念包含了兩種不同的事物:對于相鄰近的語言而言,相當一部分語言現象是共同的,可以從一種轉到另一種,而另一些語言因素是習語性的、固定的。荷馬的英國讀者失去的不是語言,而只是希臘文。況且他失去的也并非全部希臘文,高明的譯者能將某些習語性的希臘文的道德思想傳達出來,他運用的雖然是正確的英語,但并非英國人會寫的那種英語。[12](PP.3-4)
不知道這段話的出處,恐怕會誤以為是在反擊后現代主義的差異性主張。但它絕非經驗意義上的歸納、論證,而是整體理念的同義反復,其關鍵是整體空間對于個別習語以及相關學術研究的超越,如穆爾頓所說:“問題的關鍵不是文學和語言的比較價值,而是實現文學作為統一整體(realizing literature as a unity)的可能性。”如果文學從根本上屬于超越了個人和語言的整體視域,文學的世界性當然就不成問題——即使沒有一種統一的世界文學。換言之,翻譯研究和外國文學其實是共生關系,能夠想象整體,也就能夠想象作為整體之聯系的翻譯。只要讀者能借助翻譯媒介感受到和荷馬史詩的共鳴,外國文學對他來說就是現實。反之,如果不能在想象中建構文學性整體,就算用原文來閱讀,用國別文學的闡釋程序來分析,這一外國文學同樣不存在——英、德、俄語等個別習語的熟練使用,并不能保證外國文學的結構性完整和自主。
(四)問題意識
問題意識是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的外國文學方法論反思的熱點之一。[13](PP.141-147)何為“問題”?用知識社會學的術語來說,“問題”即來自外部環境的“刺激”(Irritation),它還未經過“結構性聯接”的疏導而上升到系統內運作的形式層面。所謂“問題意識”,就是這種刺激本身成為系統內交流的話題。但是,問題意識并不代表主體性自覺,有些刺激是完全無效的,另一些則是臆想的刺激,故可見中國問題不等于真正的中國文化立場,且中國問題在某一時刻恰恰可能是:無法實現中國文化立場的形式。中國問題是有待中國文化立場加工的、還不具備形式的純粹媒介,而作為形式的中國文化立場代表了自我創造、自行演化的系統整體,包容了外國文學研究的進入/退出和自我/異域的二重循環。也就是說,有關中國的問題并不就等于中國化的問題。反之,棘手之處在于,中國問題如何能成其為中國問題,即:如何讓中國的現實問題、本土問題成為中國化的、以中國特有的方式提出的問題。
(五)中國文化立場
盡管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和中國問題本身向來密切結合,甚而是密切配合,學界依然感到真正的中國立場的缺失,換言之,研究者直覺到,還沒有真正進入一個超理論的觀察層面。吳元邁在總結新中國五十年外國文學研究時,指出的第一條缺點就是:“尚不能完全以我為主,從中華民族的主體性出發來探討和研究外國文學。”[14](P.13)只有進入超越一般方法理論、一般中國問題的超理論層面,才能回答有關中國立場或“中華民族的主體性”的問題。
中國文化立場即中國研究者的超理論空間。放棄外國文學研究在理論層面的自主,意味著對于外國文學的異域規定性的尊重,但并不意味著不需要在超理論層面對外國文學的符碼要素進行創造性調諧。在第三級觀察的層面,中國有著極其豐富的本土資源,這是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者的真正用武之地。首先,對整體的體察,或者說對超出一切“有”(系統、實在、理論、意義)的“無”的想象,是中國古代文人的重要話題和儒道釋三家思想的共同基礎。“吾道一以貫之”,中國思想始終關注普遍有效的道,它所追求的統觀,遠超越了西方解釋學中整體和個別的相互參照,而是對于大小宇宙、意識和無意識、實體和非實體的綜合觀照。懂得了這種思維的真諦,就無需為局部性批評理論的潮來潮往、大旗變換而困惑。其次,如何實現“道”的整體?對中國古人來說,整體性的希望不在事物的完善狀態,而全賴于稱為“幾”或“微”的萌芽點。“幾者,去無入有,有理而未形之時。”[15](P.18)顯然,中國文化立場并非具體的理論范疇,而是促成變化、生長的符號組織原則。中國文化空間也只是創造性地演繹那“大”的境界的空間構造行為本身,不僅要求超越任何實際的中國的社會政治觀點,也要超越中國古代文論范疇乃至國學傳統(因為任何理想的框架,都只有在否定和超越中實現自身)。同時,超越不是指向系統外的終極目的,而是在不息的向上升進中回復到一陰一陽的宇宙律動,超越性和內在性合二為一,從而實現了“自然”的本義。
對于上述問題的反思,最終會導致對一種新的認識論框架的需要。從認識論角度來說,超理論以進入/退出和異域/自我的區分標準取代了傳統認識論的認識/對象的區分,從而擺脫了各種形式的理論都無法解決的文學認識的基本悖論,即文學中既不曾有固定的認識對象,也不曾有固定的認識者:有現實主義的卡夫卡,也有表現主義、象征主義或后現代主義的卡夫卡;今天的《簡·愛》不同于昨天的《簡·愛》,伊格爾頓的《簡·愛》不同于斯皮瓦克的《簡·愛》,而西方的《簡·愛》又不同于中國的《簡·愛》,任何關于《簡·愛》的“認識”都不過是一時一地的建構。執著于認識/對象的區分標準,等于否認了文學場域的認識的可能性。在此意義上,中國的外國文學和比較文學界熱議的“失語”危機、要理論還是回到文本的爭議、如何堅持本土立場的問題,都不過是認識論轉型期特有的迷惑,因為上述問題只存在于認識/對象的傳統認識論框架之內,這一框架卻并不適用于外國文學交流過程。不難想象,由這種框架和內容的錯位導致的悖謬會如此展開:(一)如果非要問,怎樣的理論才能符合外國文學文本,理論間的相互抵制就是必然結果;(二)能和外國文學文本相符合的,從道理上說只有外國文學理論,那么中國觀察者必然處于失語狀態;(三)可是說到底,理論不可能符合文本,只有文本本身能符合文本,故文本主義鼓吹“不要理論”,但“不要理論”又是一種理論。綜合起來,后果就是一個“失語”。“失語癥”論是對轉型期文化現狀的犀利批評,但這種觀察的有效性僅限于第二級觀察層面,它只是告訴我們,我們的理論場上處處是悖論,現有的理論和文學對象的關系異常緊張。但是由第三級的觀察來看,理論最終也只是悖論:理論無法觀察自身的區分標準。理論因悖論而展開,因為失語,故而能語。同時“失語癥”論也沒有回答,何為真正的解悖論形式。顯然,如果把中國古代文論看作理論層面上新的競爭者,只是重復了悖論,而并未在理論的真/假標準外引入新的認識論標準,也就無法在區分的基礎上觀察這一真/假標準的種種形式。
四、兩種系統論的交匯和一種理論趨勢
超理論旨在引入新的認識論區分,從而在系統內部實現對系統整體的返觀。超理論的元方法論欲探討的,不是認識和對象是否吻合,而是如何延續系統的自動生產。從超理論角度來看,任何理論都具有合法性,它們共同搭建起文學的想象空間,以相互間的交替循環呈現文學空間的完整性——現實/虛構的二元共存。“進入/退出”所代表的悖論化/解悖論化的區分,在任何形式的理論操作中都會重復出現。它意味著,任何觀察本身都是悖論,因為它無法觀察這一觀察自身(即觀察所依據的區分標準)。通過改換觀察角度,悖論會自然消除,但是新的觀察角度同樣是悖論性的,因為它同樣無法觀察自身的觀察,唯有靈活、生動的轉換能將悖論無限推后。
中國文化立場成了元參照框架的象征,它不關心具體理論程序,卻暗示了作為認識路徑的系統/環境或自我參照/外來參照的循環,以此來沖破知識的凝滯與固化,使文化活動融入生命律動。從根本上說,理論操作的有效性在于,既能保證意義的繁衍,又讓單個意義的生成和宇宙的整體背景相關聯,從而避免多義性淪為個別性的專制。如果能朝這個方向邁出步伐,讓中國文化空間成為一個超越意識形態、充滿變易可能的場域,就可以驕傲地說,曾經生成了中國傳統文學批評方法的中國文化規則,也可以引導我們和當代方法理論對接,以中國方式來組織外國文學想象空間。中國文化立場反映系統的整體運行,而一般理論代表了局部程序,承擔特殊的建構功能。但因為文學以整體為結構性動機,以邏輯和想象的交替為分化原則,故文學理論又天然地具有向整體躍進的趨勢,既要實現功能性,又要超越局部程序,進入一個包容理論觀點的循環轉換的生命空間。
這正是盧曼的系統論理想。盧曼曾批評說,20世紀西方思想的最大問題是摧毀了整體后無力再思考整體[2](P.502),故他力圖設計一個非目的論的、充滿變動的新整體圖式。對他來說,系統不是為了消滅偶然性而存在,相反偶然性和不確定性是系統演進的基本動力。[2](P.521)為了徹底消除所有的未來的確定性,他不惜用知識的進化論代替傳統的邏輯實證主義、共識理論或連貫性理論。在知識的進化論中,“時間”成了真正的結構性范疇,認識(理性)被徹底地時間化,知識隨時勢而變動,剎那生滅。盧曼認為,傳統的西方認識論以一個固定的觀察者和一個固定的觀察對象為出發點,而現代的認識論應從變動的觀察者和觀察對象出發,以一種悖論性的“操作邏輯”(operative Logik)取代傳統邏輯,在這一點上他接近了《易經》的基本立場。
《易經》的一陰一陽可視為文學的現實/虛構二元性的最佳詮釋,相比之下,辯證法的矛盾對立僅限于在場者范疇,與之并不處在同一層面。同時,一陰一陽也道出了盧曼的知識的凝固化/去凝固化的區分的真義。一陰一陽謂之“道”,“道”就是統一了有和無、系統和環境、自我參照和外來參照、觀察和操作的整體。故《易經》預見了盧曼的系統論反思。在《易經》系統中,天道體現為系統論強調的“循環”(“復”)。易的三義源自不同層面的世界觀察:在第一級觀察層面,是世界萬物遵循一般因果規律在生成、變化;在更宏觀的第二級觀察中,世界如四季般循環往復;在第三級的觀察層面,世界是“不易”的宇宙秩序本身。
按照中國觀念,坤(陰)主保藏,賦予萬物穩定的形態,然而坤道承乾,乾道統坤,才是宇宙規律。乾道主變,代表了生命的進進不止。而以一個超理論立場打破一般表意過程的凝滯的想法,也早就在注重功能性的西方理論內部醞釀了,20世紀理論史上留有它清晰的印跡,絕非簡單的“中國特色”。與之相共鳴的,首先可以舉出上世紀初的本雅明。本雅明將實現文本意義的關鍵環節推到一個全然陌生的層面。《譯者的任務》主張,翻譯不是對原文的自我實現的妨礙,而恰恰是要幫助原文向純語言的層面超越。為了“純語言”的緣故,譯者冒險打破民族語言之間固有的藩籬。譯者得天獨厚的優勢就在于,他只需關注語言自身,而不必像作者那樣背負沉重的表意負擔:
在不同的語言中,那種終極本質即純語言只與語言因素及其變化相關,而在語言創造中,它卻背負沉重的陌生的意義負荷。要解脫這一重負,把象征變成被象征,從語言流動中重新獲得圓滿的純語言,則是翻譯的巨大和唯一的功能。在這種純語言中——它不再意指或表達什么,而作為非表現性和創造性的“道”,它成了各種語言所意指的東西——一切信息,一切意義,一切意圖,最終都在一個語層上遭遇,并注定在這里消亡。這個語層為自由翻譯提供了一個新的和更高級的理由,這個理由并非產生于將被表達的意義,因為從這個意義中解放是“信”的任務。[16](P.10)
按照本雅明的形象表述,譯文體現了原文的來世生命,更確切地說,譯文不過是造成運動的媒介,它以一種激進形式迫使原文蛻去內容的外殼,在向純語言的躍升當中實現真正的內容。對本雅明來說,意義(信息、意義、意圖)即為凝滯,而人類語言的本質是翻譯所象征的流動。按照這個原理,中國文化空間作為陌生的語言環境,同樣能促成外國文學的意義生長,因為它使作品擺脫了源出環境中與之共生的各種意識形態的制約。
羅蘭·巴特的“文學”概念也起著類似中國文化空間的包容功能。文學是絕對“真實”,亦即絕對“界外”。它容納任何知識,而從不將其固定。它使知識超越了認識論層面,而進入一個戲劇化過程,即近于生命本身的無休止的自我反思與超越過程,文學恰是為了糾正科學和生命的落差而生。巴特的文學成了符號游戲的大劇場,而他的語言無政府主義也正基于對文學的包容能力的信心:文學允許主體根據欲望的自由或欲望的倒錯而選擇合適的語言。[17]作為制造變化的符號空間,文學和形而上學的整體框架的區別,就是可寫文本/可讀文本、書寫/作品、讀者/作者的區別。可讀文本設定了一個固定框架(典型社會環境、典型人物),使讀者淪為信息的被動接受者。相反,可寫文本為讀者提供了參與權力游戲和文本建構的空間,邀請他們去生產無數的實體:“可寫文本是一個永恒的當前,關于它無法提出任何連貫的言語(后者必定將它轉化為過去);可寫文本,它就是我們處在寫作中,在世界的無限游戲(世界作為游戲)被某種單一系統(意識、體裁、批評)所橫越、分割、制止、塑形之前。正是這種系統壓制入口的多樣性、網絡的開放和語言的無限。”[18](P.11)
斯皮瓦克也曾鄭重其事地向西方同行推薦一種由異文化的翻譯、調諧而實現的“遠距制作”(teleopoiesis),其理由是,在“星球化”時代,被他者想象才是自我想象的最佳途徑。在“遠距”(teleo)的“想象制作”(poiesis)工坊,來源、訴求迥然相異的種種理論原素各得其所,相得益彰,將文學的符號空間合作建設為一個動態、開放的生命空間。這個概念挪用自德里達的《友誼政治》,在德里達那里,“遠距制作”意為在一個完全不同于你自身之所處的時空中,在事先完全不知道將會發生什么的情況下,促成某種東西的生成。斯皮瓦克由此引申出了一種新的比較文學研究方法:“這是想象你自身,而其實是讓你放棄保障,讓你自身通過另一種文化、在另一文化中被想象(經歷那種不可能性)……”[19](P.52)事實上,斯皮瓦克相信一切真正的詩學都是這樣一種由充滿非確定性的遙遠時空媒介進行“制造”的詩學。
以上三位理論家都相信,理論恰恰要在一個貌似神秘、混沌、非科學的空間中才能實現自身。無獨有偶,三人都提到了意義的消亡和語言的重生的辯證關系。“一切信息,一切意義,一切意圖,最終都在一個語層上遭遇,并注定在這里消亡”,這一純語言的層面被本雅明稱之為“上帝的記憶王國”。對羅蘭·巴特來說,要傾聽“語言的簌簌聲”(le bruissement de la langue),恰恰要超越一切語法和邏輯,融入那“永遠而高貴地置身于句子之外的東西”即“非句子”(non-phrase)之中。[20](PP. 79-80)斯皮瓦克則意味深長地引用了托妮·莫里森的《寵兒》結尾處的一段,來暗示那種超乎言語之外、卻在后殖民作家的文學虛構中呈現的“星球化”空間:
漸漸地,所有的蹤跡消逝了。不僅足跡被遺忘,還有流水,以及水底的東西。留下的是天氣。不是無法追憶、無可解釋者的氣息;而是屋檐上的風,或者迅速融化的春季的冰。也就是天氣。
抹去言說的“痕跡”(trace),才能領會亙古不變的“天氣”(weather)和“大地的語調”(earth’s tone),這豈非孔子說的“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斯皮瓦克相信,唯有進入這一“無語”的境界,才談得上所謂文化間的翻譯,比較文學亦才能起死回生。[19](PP.88-89)
其實,理論家們大都清楚,一般的方法論只是人為的區別系統,而真正的方法論是在主體想象和宇宙生命之間進行有效調諧,將方法的區別納入整個世界的交流系統,從而使方法操作的成果超越一時一地的功能性意義,幫助文學實現其文學性——實現其作為普遍化的交往媒介的使命。這就是德里達的“差異”(différence)和“延異”(différance)的區別:一般的方法論就是一般的區分(“差異”),而真正的方法論是動態的宇宙性區分(“延異”),是造成區分的區分之區分。*盧曼也提到了德里達的“延異”概念和帕森斯的不斷“重新輸入”系統自身的“原始區分”的相似性,見《社會中的知識》,Niklas Luhmann, Die Wissenschaft der Gesellschaft, 3. Aufl.,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98,第190頁的注釋38。盧曼在知識社會學上的激進之處就在于,他已經意識到,認識論的終極問題乃是如何解決循環、無限后退、同義反復和悖論的問題,他的辦法是以觀察/操作的區分來代替傳統形而上學的思維/存在和先驗/經驗,以無窮的觀察將悖論向后無窮推遠。《易經》則可謂這一“操作邏輯”的進一步簡化,既是理智的終點,也是返璞歸真的開端,它的陰/陽、靜/動的區分道出了觀察/操作的區分的實質。對于《易經》,不變的就是“易”本身;對于盧曼,系統之所以能實現其運行和演化,正因為放棄了一切固定的根據或目的。*參見Luhmann,Die Wissenschaft der Gesellschaft, P. 591。 “所有穩定性的最終參照是系統的自動生產:即延續那些帶有系統特別編碼的操作——分配真假兩種價值,以便實現系統內部的知識處理的象征化。”
文學研究應該和“無限”(整體)之維掛鉤,以融入“無限”為闡釋學的核心問題。無限當然不等于無界限,因為無界限即無世界的生成,而是在現實的邊界內(系統內)擁有自我分化的無窮可能,在保存的同時還可無限生成,而實現這一點,正是系統論觀念下文學認識論的核心問題,也是所謂“回到文學本身”的真實含義。“無限”的真義是交流的無休止,而文學應成為具有“自動生產”能力的交流系統。在這一交流系統中,理論闡釋是不可少的一環,因為闡釋是促成交流行動的主要手段。但理論真正的使命是交流行動本身,一方面嫁接入新的交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促成和文學外交流系統如倫理、法律、權力、貨幣等的關聯。這種新的交流當然是在創造新的差異(意義),但從根本上說,它只是實現了文學交流系統自我更新、自動生產的內涵本身。所謂的意義不能理解為——作為闡釋終點的——現成的存在物,而僅僅是一種媒介,一種促成文學交流行動的契機。
有了世界,才談得上世界上的萬千變化。有了文學,才談得上種種文學的復雜性。故即使在今天這樣一個厭惡元敘事、反對普遍主義的時代,整體性框架仍不可或缺。后現代欲以整體/非整體的區分打破現代的自我參照,僅僅因為這個區分,它就失去了整體這一自設的斗爭對象。從超理論角度來看,后現代恰恰因為立足于潛在的整體性,才得以反整體,也就是說它本身就是一種新整體性的表達。關鍵是,這一整體框架要促進、而非遏制創造性的差異游戲。
參考文獻:
[1]Niklas Luhmann.Literatur als Kommunikation[M]//SchriftenzuKunstundLiteratur.hrsg. von Niels Werber. Frankfurt a. M.: Suhrkamp, 2008.
[2] Niklas Luhmann.DieWissenschaftderGesellschaft: 3. Aufl.[M].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98.
[3]Samuel Taylor Coleridge.BiographiaLiteraria[M].Boston: Crocker & Brewster, 1834.
[4]Niklas Luhmann,EinführungindieSystemtheorie[M]. hrsg. von Dirk Baecker. Heidelberg: Carl-Auer-Systeme, 2002.
[5]袁可嘉.“新批評派”述評[J].文學評論,1962,(2).
[6]曹順慶.21世紀中國文論發展戰略與重建中國文論話語[J].東方叢刊,1995,(3).
[7]曹順慶.文論失語癥與文化病態[J].文藝爭鳴,1996,(2).
[8]曹順慶.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的基本路徑及其方法[J].文藝研究,1996,(2).
[9]曹順慶.論“失語癥”[J].文學評論,2007,(6).
[10]曹順慶.失語癥:從文學到藝術[J].文藝研究,2013,(6).
[11] Mikhail Bakhtin.ProblemsofDostoevsky’sPoetics[M].ed. and trans. Caryl Emerson.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12] Richard G. Moulton.WorldLiteratureanditsPlaceinGeneralCulture[M].New York: Macmillan,1911.
[13]趙淳.話語實踐與文化立場——西方文論引介研究:1993-2007[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
[14]吳元邁.回顧與思考——新中國外國文學研究50年[J].外國文學研究,2000,(1).
[15]周易正義[G]∥十三經注疏.孔穎達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16]本雅明.譯者的任務[C]∥陳永國.翻譯與后現代性.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17]Roland Barthes.Lecture in Inauguration of the Chair of Literary Semiology[J].trans. Richard Howard.October, 1979, 8(Spring).
[18]Roland Barthes.S/Z[M].Paris: Seuil, 1970.
[19]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DeathofaDiscipline[M].New York: Columbia UP, 2003.

(責任編輯:吳芳)
Metamethodology of Foreign Literature Research:
A Perspective Based on Systems Theory
FAN J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Based on Luhmann’s Systems Theory, this paper aims at investigating the global operation of the foreign literature research which is often treated as a system of knowledge commun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paper, there involves three levels of methodology, that is, method, theory and supertheory. From a super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about foreign literature research is understood as a double circulation of exit/entry and the foreign/self, which forms the basis of the common subject-object cognition and the metamethodology of general methodology. Within t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olve some important issues discussed in China for years on foreign literature research: 1) “aphasia” proposition; 2) opposing theories; 3) locatio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4) problem consciousness; and 5) standpoint of Chinese culture. Finally, the possibility of connecting Luhmann’s Systems Theory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s is to be put forward in the paper, which reveals a potential development of neo-holistic thinking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theories.
Key words:Foreign literature; Systems Theory; supertheory
基金項目: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當代西方的神經美學研究及其思想啟示”(13BZX094)的研究成果。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5.01.007
中圖分類號:IO-0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2338(2015)01-0044-11
作者簡介:范勁(1973-),男,貴州遵義人,文學博士,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主要從事外國文學、比較文學研究。
收稿日期:2014-11-25 2014-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