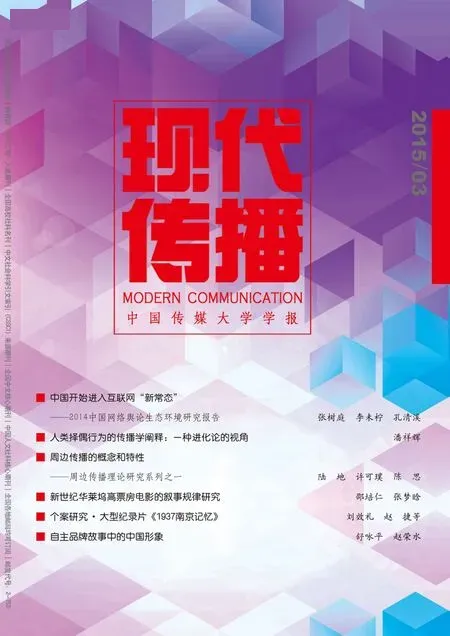電影數(shù)字技術(shù)美學的對比解析與辯證審思
■鞏杰
電影數(shù)字技術(shù)美學的對比解析與辯證審思
■鞏杰
隨著電影技術(shù)從機械技術(shù)時代進入到數(shù)字技術(shù)時代,電影美學已由機械技術(shù)美學向數(shù)字技術(shù)美學轉(zhuǎn)變。與傳統(tǒng)機械技術(shù)時代的電影美學相比,數(shù)字技術(shù)美學在電影本體性、電影題材和想象以及電影時空的拓展上都產(chǎn)生了新奇的變革。電影數(shù)字技術(shù)美學奇觀化的呈現(xiàn)和對人的想象力的最大化表達,使電影美學由傳統(tǒng)的“感受美學”變成“驚奇美學”。審美體驗由“藝術(shù)震撼”取代“藝術(shù)韻味”,“審美愉悅”變成“審美驚奇”。值得審思的是,只有在電影的技術(shù)美學美感中融入更多的人文情懷和普世價值,才能更好更全面地提升電影的美學品格內(nèi)涵。
電影數(shù)字技術(shù)美學;超現(xiàn)實主義;虛擬現(xiàn)實;審美驚奇
美國著名導演詹姆斯·A·卡梅隆這樣說道:“視覺娛樂影像制作的藝術(shù)和技術(shù)正在發(fā)生著一場革命,這場革命給我們制作電影和其他視覺媒體節(jié)目的方式帶來了如此深刻的變化,以至于我們只能用出現(xiàn)了一場數(shù)字化文藝復興運動來描述它。”①今天的電影已經(jīng)從機械技術(shù)時代進入到數(shù)字技術(shù)時代,電影已經(jīng)由本雅明所說的“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shù)作品”變成了數(shù)字復制的藝術(shù)作品。數(shù)字技術(shù)對電影創(chuàng)作和視覺媒體帶來了巨大變革。這種變革出現(xiàn)在技術(shù)層面,而使機械技術(shù)時代傳統(tǒng)的電影美學和審美體驗發(fā)生新奇轉(zhuǎn)變的,不僅限于技術(shù)領(lǐng)域。
一、數(shù)字技術(shù)時代電影數(shù)字技術(shù)美學的凸顯
在數(shù)字技術(shù)剛剛誕生的時期,我們只重視數(shù)字技術(shù)對于電影制作的神奇作用,而沒有從美學層面上思考數(shù)字技術(shù)帶給電影的新奇變化。如今,電影已經(jīng)告別了機械技術(shù)時代,電影前期拍攝、后期剪輯制作以及影院放映,都是用數(shù)字技術(shù)設(shè)備來完成的。在拍攝階段已經(jīng)用高清數(shù)字攝像機代替了原來的膠片攝像機,用硬盤和存儲器取代了膠片。在后期制作中,用各種非線編軟件取代了原來的機械化的人工膠片剪輯。在放映中,數(shù)字放映機取代了以前的膠片放映機。這些都標志著電影已經(jīng)迎來了一個全新的數(shù)字技術(shù)時代。
如今,我們需要對電影數(shù)字技術(shù)進行理論提升,不能總停留在技術(shù)層面談問題,而應(yīng)該從電影數(shù)字技術(shù)美學的高度來認知和解決問題。數(shù)字技術(shù)的出現(xiàn)為電影藝術(shù)創(chuàng)作和電影美學開辟了新視野。
電影數(shù)字技術(shù)美學是電影技術(shù)由機械技術(shù)發(fā)展到數(shù)字技術(shù)階段后,在電影美學領(lǐng)域發(fā)生的新變化。電影美學大概經(jīng)歷了戲劇美學、表現(xiàn)美學和紀實美學形態(tài),這些傳統(tǒng)的電影美學形態(tài)都是建立在電影機械技術(shù)基礎(chǔ)上的,無論是電影拍攝、剪輯或特技處理都是依靠機械技術(shù)來完成的。而唯有電影的數(shù)字技術(shù)美學,是與計算機數(shù)字合成技術(shù)(CGI)發(fā)展相關(guān)聯(lián)的。“從剪輯的技術(shù)到蒙太奇的藝術(shù)(敘事的和表現(xiàn)的)、再到蒙太奇的美學觀念;從景深鏡頭的發(fā)明到長鏡頭的藝術(shù)(場面的內(nèi)部調(diào)度)、再到長鏡頭的紀實美學——美學從來就是藝術(shù)的概括與總結(jié),新技術(shù)只有真正融入了電影的藝術(shù)系統(tǒng),它才有可能上升到電影美學的層面來加以觀照。”②作為新技術(shù)的電影數(shù)字技術(shù)充分融入到電影藝術(shù)系統(tǒng)中,長期發(fā)展并經(jīng)過提煉總結(jié),產(chǎn)生了數(shù)字技術(shù)美學。
在電影數(shù)字技術(shù)經(jīng)過四十多年的發(fā)展成熟后,我們已經(jīng)迎來一個全新的電影數(shù)字技術(shù)美學時代。正如美國電影歷史學家羅伯特·羅森在一篇關(guān)于數(shù)字藝術(shù)美學的文章中這樣寫道:“從《黑客帝國》開始,雨后春筍般出現(xiàn)的這些彰顯新興電影美學特征的影片不再是讓人束之高閣的藝術(shù)試驗片,而是一步步侵占主流市場。我想唯一能解釋這一切的就是:數(shù)字時代的電影已經(jīng)具備了一套嶄新的美學體系,此類電影共有的美學體征已被新生代廣為接受。”③
二、電影數(shù)字技術(shù)美學與傳統(tǒng)電影美學的對比解析
與傳統(tǒng)的機械技術(shù)時代的電影美學相比,數(shù)字技術(shù)美學在電影本體性的延伸上,在電影題材和想象力拓展上,以及電影時空的開掘上,都有產(chǎn)生了新奇的美感。
在機械技術(shù)時代,無論是面對實景還是在影棚中,電影的攝制都必須要依原物為摹本進行拍攝,正如巴贊在《攝影影像的本體論》中所寫道:“攝影的客觀性賦予影像以令人信服的、任何繪畫作品都無法具有的力量。不管我們用批判精神提出多少異議,我們不得不相信被摹寫的原物是確實存在的。它是確確實實被重現(xiàn)出來,即被再現(xiàn)于時空之中。”④而到了數(shù)字技術(shù)時代,電影攝制已經(jīng)不完全依靠實景拍攝。一方面,數(shù)字技術(shù)可以“真實再現(xiàn)”現(xiàn)實世界中的自然景觀和視覺奇觀,進而完成電影虛擬現(xiàn)實的夢想。另一方面,就如鮑德里亞所言,“類象不再是對某個領(lǐng)域、某個指涉對象或某種實體的模擬。它無須原物或?qū)嶓w,而是通過模型來生產(chǎn)真實:一種超真實。”⑤即使沒有原物出現(xiàn),通過電腦技術(shù)設(shè)計,我們就可以再現(xiàn)現(xiàn)實或者創(chuàng)造出一種人們能想象到的、但根本就不存在的世界景象。
從攝制手法和程序而言,這似乎看上去是對巴贊所提出的紀實美學的一種顛覆,但是從電影的真實性而言,恰恰是對電影反映或者再現(xiàn)現(xiàn)實的一種同構(gòu)。電影的真實來自生活、客觀事物和情感的真實,即便是在電影的紀實美學表述中,電影藝術(shù)也不等同于生活本身,用巴贊的話來說是“電影是現(xiàn)實的漸近線”。
電影的數(shù)字技術(shù)美學和紀實美學并不矛盾,也不是對巴贊紀實理論的一種挑戰(zhàn)和反抗,而是使電影多了一種美學形態(tài)的可能。“影像在復原中孕育了呈現(xiàn)的沖動,奇觀本性與真實本性的斗爭最終決定了想象的實物的誕生,這正好為數(shù)字時代的影像誕生開辟了美學道路。”⑥所以,有人把數(shù)字技術(shù)所創(chuàng)造的“無中生有”的世界稱為超現(xiàn)實主義,正如鮑德里亞所言:“超現(xiàn)實主義仍然與現(xiàn)實主義有關(guān)聯(lián),它質(zhì)疑現(xiàn)實主義,但它卻用想象中的決裂重復了現(xiàn)實主義。超真實代表的是一個遠遠更為先進的階段,甚至真實與想象的矛盾也在這里消失了。非現(xiàn)實不再是夢想或幻覺的非現(xiàn)實,不再是彼岸或此岸的非現(xiàn)實,而是真實與自身的奇妙相似性的非現(xiàn)實。”⑦
所以,電影紀實美學和電影數(shù)字技術(shù)美學是電影美學存在的兩個方面,都是對現(xiàn)實生活的反映。依照電影數(shù)字技術(shù)美學原則——影像上的擬真也來自真實的現(xiàn)實生活,而且更具有逼真性和更富有想象力。特別是一些想象類題材,比用真人表演或者實景拍攝更能產(chǎn)生真實感。
電影數(shù)字技術(shù)創(chuàng)造的美可以把人們的想象世界變得更為逼真,這是機械電影攝像技術(shù)難以達到的效果。不管機械復制時代的膠片電影使用長鏡頭抑或是蒙太奇,都很難達到電影數(shù)字技術(shù)所創(chuàng)造出來的虛擬世界和虛擬人物的美妙效果。電影數(shù)字技術(shù)所創(chuàng)造的逼真的畫面,雖然可能是現(xiàn)實生活中不存在的世界,但所表達的思想內(nèi)容依然符合人類情感需要和世界存在的需要,是對客觀現(xiàn)實的虛擬化、仿真化的再現(xiàn)。通過人們在欣賞中對電影產(chǎn)生的假定性和“審美構(gòu)形”,使人的精神和情感投入其中,想象并“構(gòu)形”影像世界的合理性和科學性,從而實現(xiàn)電影的造夢功能。
電影技術(shù)美學具有形式美的特征,虛擬性和逼真性共存,把人的豐富的想象力變?yōu)榭梢暤男蜗螅M而創(chuàng)造出未知世界并拓展了電影的題材范疇和主題內(nèi)涵。就此而言,美國的數(shù)字電影藝術(shù)創(chuàng)作在題材和想象力上更具有獨有的魅力,充分彰顯了數(shù)字技術(shù)美學的特質(zhì)。進入新世紀以后,《魔戒》《人工智能》《珍珠港》《怪物史萊克》《蜘蛛俠》《哈利·波特》《冰河世紀》《海底總動員》《納尼亞傳奇》《北極故事》《三百壯士》《機器人總動員》《阿凡達》《飛屋環(huán)游記》《海底世界》《盜夢空間》《猩球崛起》《蝙蝠俠:黑暗騎士崛起》《星際穿越》《超體》等,更加把世界電影帶入到一個新境界和新天地。
從這些影片我們可以看出CGI技術(shù)在美國電影中的無窮魔力。特別是《指環(huán)王》和《阿凡達》的出現(xiàn),更是給電影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震撼。《指環(huán)王》影片中創(chuàng)造的第一個計算機動畫人物“咕嚕”也成為高科技電影技術(shù)的里程碑。“《阿凡達》的最大價值,體現(xiàn)為人類想象力的釋放。甚至讓技術(shù)走在了想象力的前面,而不是讓劇情淪為技術(shù)的奴隸。想象力給人帶來一種顛覆性的視覺沖擊體驗,成為人類發(fā)明電影一百多年來又一次技術(shù)上的藝術(shù)突破。”⑧
從題材而言,美國的數(shù)字技術(shù)電影多在探求人與宇宙、人與外星人、人與自然,人與奇異世界的關(guān)系,所以影片充滿了傳奇冒險和魔幻色彩。這些題材領(lǐng)域的開拓,需要相應(yīng)的數(shù)字技術(shù)作為實現(xiàn)的可能,進而創(chuàng)造電影的逼真性,來實現(xiàn)創(chuàng)作者頭腦中的想象世界。另外,相對于本土題材而言,好萊塢電影在本土電影題材資源貧乏和單一的情況下,把題材范圍擴展了世界范圍。表現(xiàn)歐洲題材的電影如有關(guān)北歐童話和神話的《納尼亞傳奇》《哈利·波特》系列等。另外對于東方市場,他們利用中國文化題材創(chuàng)作的電影有《花木蘭》《功夫熊貓》《無間道風云》等;利用印度題材創(chuàng)作的電影有《貧民窟的百萬富翁》《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等。
通過美國數(shù)字電影藝術(shù)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數(shù)字技術(shù)美學不僅僅是在視覺層面發(fā)揮作用,它對電影的題材和主題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把人的想象世界變成可見的影像世界。如果純粹地只講視覺沖擊而忽視了電影想象力和題材的拓展,那么這樣的數(shù)字技術(shù)將會變得空洞而成為純粹的形式,就會喪失電影應(yīng)有的美感和韻味。
除了在題材類型上的拓展外,數(shù)字技術(shù)也營造出奇特的電影空間。機械技術(shù)時代的電影中,長鏡頭所生成的紀實美學力求保持電影時空的同一性和真實性,具有庫里肖夫?qū)嶒炇降拿商婵梢源蚱茣r空,實現(xiàn)時空的自由組接的作用。而到了數(shù)字技術(shù)時代,電影的時空表現(xiàn)可以實現(xiàn)更大地自由創(chuàng)作和表現(xiàn)在更為廣闊的領(lǐng)域。
正如金丹元教授所言:“數(shù)字技術(shù)的引入,使得電影空間的表現(xiàn)力空前擴大,觀眾不僅對空間的感受更加強烈,而且還能獲得某種奇特的空間體驗。數(shù)字技術(shù)突破了傳統(tǒng)攝影機的拍攝視角,創(chuàng)造出一種奇特而又迷人的時空效果。攝影機視角的解放,也將人類對時空的想象力發(fā)揮得淋漓盡致,制造出了令人匪夷所思的視覺效果。”⑨因而,依托計算機 CGI技術(shù),充分發(fā)揮電影創(chuàng)作者主體的主觀能動性,數(shù)字技術(shù)可以將理想與現(xiàn)實任意組接和創(chuàng)造,創(chuàng)造出虛實共生的電影空間和美輪美奐的藝術(shù)形象。
三、審美主體互動式的自由審美體驗
進入數(shù)字技術(shù)時代以后,人們的觀影方式和體驗也與機械技術(shù)時代大為不同。隨著家庭影院的興起和電視、電腦的普及,電影院不再是人們觀影的唯一場所。人們完全可以在私人空間完成自由選擇式的觀看,而不一定要去公共場所的電影院,影院黑暗洞穴式場所的神秘感和觀影的儀式感變得可有可無。而在私人空間觀看電影則可以自由拉片,播放、回看、快進、暫停等,個人可以完全自由選擇,觀影方式由被動接受變?yōu)橹鲃荧@取。電影的傳輸方式由單項輸出變?yōu)楹陀^眾互動方式,注重和觀眾情感方面的交流和反饋,觀眾可以發(fā)揮自己的想象力和審美感受對電影進行“二度創(chuàng)作”。這些具有數(shù)字技術(shù)美學的影片就成了尼葛洛龐帝在《數(shù)字化生存》中所提出的“互動式多媒體(Interactive Multimedia)。他認為:“數(shù)字技術(shù)電影與傳統(tǒng)藝術(shù)相比,具有實時互動性、多媒介性、多維性、虛擬沉浸性等特性。”⑩這就使得電影欣賞者不必再像傳統(tǒng)的電影觀眾那樣一味接受或者遵從影片獨有的審美定位,觀眾能自由地表達自己對影片的審美愉悅,甚至可以按照自己的審美訴求參與影片的“改寫”。
電影技術(shù)美學把電影中人們能想到而不能直接用鏡頭拍攝的畫面和美學效果通過電腦技術(shù)制作的方式呈現(xiàn)出來,帶給人們驚奇的視聽享受和美感。電影數(shù)字技術(shù)美學對奇觀化的呈現(xiàn)和對人的想象力的最大化表達,使電影美學由傳統(tǒng)的“感受美學”變成“驚奇美學”。從藝術(shù)審美體驗的角度看,“藝術(shù)震撼”取代“藝術(shù)韻味”,“審美愉悅”變成“審美驚奇”。
人們在觀看機械復制的時代的膠片電影時,很容易區(qū)分電影中的想象世界和現(xiàn)實世界,觀眾與電影之間存在一定的審美距離感,這就要求觀眾要具有“靜心體味”和“聚精凝神”的審美態(tài)度,電影才能與觀眾產(chǎn)生情感共鳴,進而使觀眾充分感悟電影的價值內(nèi)涵。而在數(shù)字技術(shù)時代的數(shù)字合成技術(shù)的電影觀賞中,人們很難區(qū)分想象世界和現(xiàn)實世界,數(shù)字技術(shù)從多感官綜合介入電影。就像電影《阿凡達》中依托于現(xiàn)實的再造“真實”感覺,利用交互作用在虛擬世界中實現(xiàn)自身的感知和存在,交互技術(shù)的“擬真”和“造真”成就了觀眾與電影之間的零距離接觸,為觀眾創(chuàng)造了一種完美的虛擬沉浸式美感體驗和快樂幻覺,帶來欲望的極大滿足感。(11)這種文化景觀和情感交互體驗,顛覆了傳統(tǒng)電影的美學觀念和審美情趣。“形成全新的非時序、碎片化、偶然性、可控性的非線性敘事觀和觀眾參與的交互創(chuàng)作觀,為觀眾創(chuàng)造了零距離的虛擬沉浸之美,為逃離現(xiàn)實的欲望找到了近乎完美的棲息之所……”(12)
隨著4D電影的產(chǎn)生,電影充分發(fā)揮觀眾的觀感功能,人們對電影的審美體驗還會發(fā)生很大的改變。4D電影以3D立體電影為基礎(chǔ)摹本,利用周圍環(huán)境特效模擬仿真,通常將煙霧、氣泡、氣味、震動、吹風、噴水、布景和人物表演等效果模擬引入電影中,給觀眾一種獨特的審美體驗,觀眾通過視覺、嗅覺、聽覺和觸覺多重身體感官體驗電影所產(chǎn)生的審美效果。
總之,觀眾全方位沉浸于數(shù)字電影現(xiàn)實與虛擬交互的世界,可以滿足人們盡情放松的交流和審美趣味的需求,激發(fā)觀眾超越現(xiàn)實的自由情感體驗和審美體驗,實現(xiàn)傳統(tǒng)電影難以企及的效果。數(shù)字技術(shù)電影的美學品格極大地拓展了人類審美情感的深度和廣度,使審美主體第一次獲得了真正意義上的審美自由,從而將人類的審美經(jīng)驗引向了一個新境地。(13)
四、數(shù)字技術(shù)與電影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辯證審思
盡管數(shù)字技術(shù)在影片中創(chuàng)造出耳目一新的美感,但是我們也應(yīng)該清醒地認識到,它的作用就像一把雙刃劍,對電影的影響是雙向的。它豐富了電影的視聽語言內(nèi)容和空間,但同時也會破壞傳統(tǒng)電影中原本所具有的詩意的視聽美學境界。這種美學品質(zhì)的轉(zhuǎn)變使電影在視覺美上發(fā)生了根本性改變。就中國電影而言,數(shù)字技術(shù)美學對中國電影的視覺效果和影像風格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使中國電影由原來的“審美意境”變成了“審美驚奇”,用“審美奇觀”代替了“審美韻味”,使中國電影中含蓄溫婉的意境美有所喪失,取而代之的是強烈絢麗的視覺藝術(shù)之美。
2002年,張藝謀的武俠大片《英雄》的出現(xiàn),標志著中國依靠數(shù)字合成技術(shù)制作的大片時代的到來。《英雄》中的主要場景如百萬秦軍、秦軍箭陣、抵擋箭雨、劍穿水珠、意念之戰(zhàn)、秦殿燭火等,都是用電腦技術(shù)合成制作出來的。這樣的技術(shù)效果可以增強實景拍攝效果所達不到的震撼力。同時也使原有的電影技術(shù)發(fā)生轉(zhuǎn)變,豐富了視聽語言的形式和內(nèi)容,創(chuàng)造出電腦數(shù)字合成技術(shù)的電影美感。另外,《英雄》把中國傳統(tǒng)美學寫意、意境等美學思想用于其中,又和高科技制作相結(jié)合,給人以強烈美感和視覺享受。但是《英雄》在主題闡釋上卻被人們所詬病。因為相對于美麗震撼的畫面而言,電影的思想內(nèi)容顯得乏善可陳。《英雄》中的技術(shù)美所改變的只是給人帶來的視覺美和形式美,而電影主題的內(nèi)涵美和人物精神之美卻沒有充分展現(xiàn)。像《英雄》這樣的缺乏人類情懷和人類共同價值觀的電影是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的。
美國大片中以美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為底蘊的思想內(nèi)涵和普世價值觀沖擊了中國電影和中國電影觀眾傳統(tǒng)的價值取向和審美心理,使得中國電影中的價值觀和觀眾欣賞的價值取向出現(xiàn)混亂,使中國電影很難在短期內(nèi)建立具有引導性和本土文化風格的普世價值觀。據(jù)此,中國數(shù)字技術(shù)大片被人們所詬病的主要原因在于想象力和思想內(nèi)容貧乏的同時,卻不合時宜地穿上了一身華麗的“數(shù)字外衣”。只是在技術(shù)領(lǐng)域的跟風和模仿,而思想內(nèi)涵領(lǐng)域并未出現(xiàn)大片,更顯出思想的貧瘠和技術(shù)的拙劣。中國電影所學到西方技術(shù)美學其實只是其皮毛,真正的精神內(nèi)容還沒有學到,也沒有更好地開發(fā)和豐富本土文化資源,致使中國所謂的具有數(shù)字技術(shù)合成的大片顯得題材單一、內(nèi)容貧乏,觀念落后,無法打動人的心靈。“技術(shù),永遠為藝術(shù)服務(wù),只有這樣,技術(shù)才有資格存活在藝術(shù)之中,才配稱得上技術(shù)美學。”(14)
而好的電影數(shù)字技術(shù)則可以產(chǎn)生更好的美學效應(yīng),如同有人評價《阿凡達》那樣:“可以肯定地說,《阿凡達》對技術(shù)的使用是隱蔽的、弱化的、向傳統(tǒng)電影攝影靠攏的,這正是《阿凡達》在技術(shù)和藝術(shù)關(guān)系上的思辨之處。……卡梅隆的高明之處在于,他深知只有講好故事,他的技術(shù)才能被記住。從炫耀到收斂,這也是電影史上每一次技術(shù)成熟的特征。”(15)這也正如卡梅隆所說的:“我希望人們遺忘技術(shù),就像你在電影院里看到的不是銀幕而是影像一樣,一切技術(shù)的目的,都是讓它本身消失不見。”(16)有些電影數(shù)字技術(shù)創(chuàng)造的視覺美因內(nèi)容的陳舊和空洞而最終消解了電影整體的美學韻味,這樣的技術(shù)制作會造成電影的虛假感,也喪失了電影的真實性。所以,我們在看到數(shù)字技術(shù)美學對電影產(chǎn)生奇觀美感的同時,也要看到唯技術(shù)論對電影創(chuàng)作造成的負面影響。
因此,我們在運用數(shù)字技術(shù)創(chuàng)造審美空間和美感的同時,不應(yīng)該唯技術(shù)論或把數(shù)字技術(shù)美學奉為圭臬。畢竟,電影藝術(shù)的美不僅體現(xiàn)為視覺的震撼,也在于其主題內(nèi)涵和人物精神境界之美。這就要求我們在注重視覺美感的同時,也要締造電影的精神內(nèi)涵和精神之美。
五、結(jié)語
我們承認電影數(shù)字技術(shù)對電影形成的巨大影響,但并不是所有的電影都必須要去做數(shù)字技術(shù)。數(shù)字技術(shù)美學也不會取代傳統(tǒng)的電影技術(shù)美學。電影藝術(shù)中的各種制作方式將會長期并存。一些電影依然可以運用戲劇美學、影像美學、紀實美學的原則進行拍攝,而不是一味地迷戀數(shù)字技術(shù)。
電影的發(fā)展不僅僅是在于技術(shù)革新完善,更在于對電影價值觀念和題材內(nèi)容的創(chuàng)新。編創(chuàng)人員如果沒有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力,電影依然無法走出困境。缺乏想象力的故事和陳舊的電影理念,使得技術(shù)美成了一種華而不實的“畫皮”。電影數(shù)字技術(shù)絕對不是為了炫耀技術(shù),而是為了把人的想象世界變?yōu)楝F(xiàn)實,使人的想象力能夠得到更好的發(fā)揮。
注釋:
①[美]托馬斯·A.奧漢年、邁克爾·菲利普斯著:《數(shù)字化電影制片》,施正宇譯,中國電影出版社1998年版,第3頁。
②顏純鈞:《從數(shù)字技術(shù)到數(shù)字美學》,《電影藝術(shù)》,2011年第4期。
③[美]羅伯特·羅森著:《媒介飽和語境下對數(shù)字電影美學的思考》,黃望莉、張凈雨譯,《當代電影》,2012年第11期。
④[法]巴贊著:《電影是什么》,崔君衍譯,中國電影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頁。
⑤[美]道格拉斯·凱爾納、斯蒂文·貝斯特著:《后現(xiàn)代理論批判性的質(zhì)疑》,張志斌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版,第135頁。⑥鄧光輝、唐科:《烏托邦之后:電影美學在今天》,《當代電影》,2001年第2期。
⑦[法]波德里亞:《象征交換與死亡》,車槿山譯,譯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頁。
⑧(14)高鑫:《技術(shù)美學研究(下)》,《現(xiàn)代傳播》,2011年第3期。
⑨金丹元、徐文明:《多元語境中電影數(shù)字技術(shù)的美學與文化反省》,《當代電影》,2008年第3期。
⑩戴東方:《數(shù)字媒體藝術(shù)本體論》,《新視覺藝術(shù)》,2012年第6期。
(11)(12)參見王杰飛:《次世代數(shù)字交互式城市電影的美學嬗變》,《當代電影》,2014年第11期。
(13)熊立:《數(shù)字電影本體論》,《文藝評論》,2014年第11期。
(15)屠明非:《技術(shù)與文化:數(shù)字媒體時代的電影藝術(shù)》,《當代電影》,2010年第7期。
(16)蕭游:《卡梅隆精彩的夢是筆好買賣》,《北京青年報》,2010年1月14日。
(作者系西北大學文學院講師,中國傳媒大學藝術(shù)學部電影學博士研究生)
【責任編輯:李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