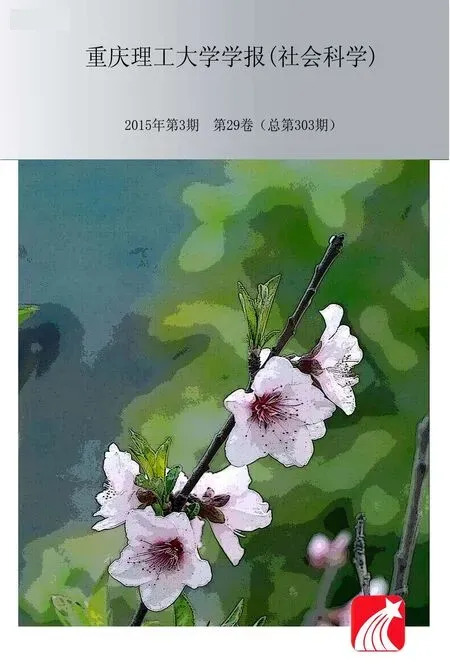何止譯者:馬戛爾尼使團訪華活動之譯員考析
劉 黎
(重慶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重慶 400074)
一、前言
1793年喬治·馬戛爾尼勛爵(Lord George Macartney)率領規模龐大的英國使團訪華是中英關系中的重大事件,它是奠定兩國正式外交的里程碑。盡管這次由英國發起的外交多被視為以失敗告終,但它卻成了中英文化交流史和中英外交關系研究的熱門話題,經久不衰。
近年有學者開始涉獵英使團訪華的翻譯研究領域,并出了一些有重要價值的研究成果,如有學者對“英國國王喬治三世致乾隆皇帝國書”的翻譯進行了詳細解剖[1],也有學者將清宮檔案中保存的外交文件的譯文,與當代學者譯出的使團成員筆記作了對比研究[2],還有學者宏觀地討論了當時翻譯的歷史局限和影響翻譯的問題[3]。然而,談及中英雙方溝通的橋梁——譯者時,論者要么匆匆帶過,要么忽略不提。譯者是誰?他們如何被選定?他們在這次外交活動中起到什么作用?這些問題的研究能幫助我們了解特定歷史時空下譯者的特點,并可引發我們對歷史語境與譯者關系的思考。
二、歷史考析
毋庸置疑,譯者是任何翻譯行為的主體。在英使訪華事件里,中英雙方都認識到翻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物色和安排合適的翻譯人員對雙方來說都絕非易事,這要歸因于中英關系的歷史遺留問題和封建中國歷來的對外政策。
明末海禁,嚴格限制中國人同外國人來往。英國東印度公司倫敦總部的人曾一度希望,英王詹姆斯一世能寫封信給中國皇帝,獲準英國商人到中國貿易,但該公司駐萬丹(Bantam)的主管在1617年寫信潑冷水說“沒有中國人敢翻譯并呈遞這些信件;根據該國法律,這樣做是要獲死罪的”[4]10。清王朝建立后,沿襲明制,閉關政策更甚。大約自1715年,中國通事說一種新奇的“中英混雜行話”(pidgin English),它成了在廣州貿易中廣泛使用的語言[4]67。但這種語言難登大雅之堂。英國大班們苦不堪言,他們“經常難以找人把中文文件翻譯成英文,并把他們的申訴正確地翻譯成中文”[4]75。
當時中國通事地位低賤,隨時有生命危險,英國人有關中國通事被戴鐐銬和投監情況的記載屢見不鮮[4]97,103。在這樣險惡的情形下,為擁有自己的翻譯,1736年英國“諾曼頓號”船長里格比于寧波貿易時,曾留下一英國少年,讓他偷學中文,此人便是洪仁輝(James Flint)。沒曾料到,此舉導致了1759年的“洪仁輝事件”,洪本人后在澳門被圈禁3年,他的中文老師、為其寫中文訴狀的劉亞匾被殺頭。“洪仁輝事件”后,為“防范于未萌”,清政府出臺了《防范外夷規條》(1759),其中第四條規定“外夷雇人傳遞信息之積弊,宜請永除”[5]。在廣州的外國人受到更加嚴密的控制,而中國人也更不敢與外國人交往。清政府的強硬政策激起外商尤其是英國人的強烈不滿,累請撤銷無果,最終導致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在此之前,洪仁輝、末文和巴頓(Thomas Bevan and Barton,1753年由東印度公司派往南京學漢語)等英國苦心經營培養出來的翻譯均已作古,所以馬戛爾尼無法在英國物色到翻譯。
清政府雖然有培養譯員的外事機構,如清初設立的會同館和從明朝接手過來的四譯館,分別主管朝貢外交和翻譯事務,但除使用漢字或東方語言的周邊朝貢屬國外,四譯館根本不可能勝任越來越多的涉及西方國家的外交事務。18世紀初,中俄交涉日趨重要,需要把來自俄方的拉丁語文件譯成滿文,將北京發出的漢文或滿文文件譯成拉丁文,清廷于1708年設立了俄文館(在1862年并入同文館);不僅如此,還于1729年設立了翻譯館,“教授旗籍子弟以拉丁文,俾能在中俄交涉中任譯事。主館事者為巴多明;多明卒,君榮繼掌館事,兼拉丁、滿語通譯”[6]690。但據錢德明神甫說:“1729年設翻譯館,此館僅存15年,諸館生從未任譯員。”[6]515這些舉措都是因對國際形勢的誤判而作出的錯誤決策,沒能培養出能應對半個世紀后以英國為主導的外交翻譯人才。因此,當馬戛爾尼使團在1793年叩開中國大門時,中方沒有通曉英語、熟悉英國國情的本國人可供委派。
三、譯者何人
正是基于上述歷史原因,中英雙方為物色和安排譯員事宜頗費周章,最終選定的譯員都是雙方不得已而為之的結果。
英使團在籌備過程中深感尋覓譯員的艱辛。正如副使斯當東(George Leonard Staunton)所說,“有一個絕對必要的,但是難以物色人選的職務,那就是中文翻譯”[7]35。當時英國上下找不到一個懂漢語的人;而到廣州當地物色翻譯也不恰當,因為就算少數廣州人懂得英文或葡萄牙語,但他們的外文知識非常有限,難以應付買賣交易以外的事項[7]35;最終使團決定到歐洲大陸尋找曾去過中國并學會了漢語后來又回國的人,或者出國學會了任何一種歐洲語言的中國人[7]35。斯當東被派往法國巴黎物色翻譯未果,又輾轉到意大利,在那不勒斯專門培養中國籍教士的中國學院(Chinese College)找到兩位中國神甫——周保羅(Paolo Cho)和李雅各(Jacobus Ly)。關于這兩位神甫的生平資料不多:周保羅不在方豪考證的同治前歐洲留學生名單內;李雅各漢名李自標,原籍甘肅武威,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并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與另外7位中國青年一起去歐洲學習傳教[8]383,393。在清廷文件里,李雅各被稱作“通事婁門”,這其實是Plum不太準確的音譯,使團成員因他姓李而玩笑地稱他為Plum(李子)先生。這兩位中國神甫不懂英語,但會拉丁語和意大利語,而使團中少數高級成員懂拉丁語,在當時看來,他們已是使團翻譯的最好人選,故斯當東帶著他們于1792年5月18日回到英國,并許以150英鎊年薪聘他們擔任翻譯[9]292-305。
另外,副使斯當東的兒子小斯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以馬戛爾尼見習童子(page boy)的身份隨團去中國。一路上小斯當東跟隨中國翻譯學習中文,進步較快,其父不無得意地在回憶錄里稱贊他雖然學習不夠努力,但感覺敏銳、器官機能靈活,容易找到學習中國語言的關鍵,并正確運用[7]247。小斯當東在必要時能充當一名相當稱職的翻譯[10]88。使團船隊到達澳門后,兩位中國翻譯之一周保羅執意與搭船回國的另外兩名中國神父一起離團上岸,如此一來,使團繁重的翻譯任務就落在了李神甫及小斯當東的肩上。
中方譯員的安排同樣面臨困難。英使訪華的消息早在使團出發后不久就通過廣州洋商蔡世文傳達到廣東巡撫郭世勛,并立刻上奏乾隆。廣東官員擔心使團的目的是要投訴廣州的對外貿易,曾嘗試委派兩名廣東商人作為譯員陪同特使進京,但東印度公司認為這兩名商人英語能力太差,無法勝任翻譯;而且,這兩位廣東商人也不情愿擔任這工作,因為他們在廣州的商務利益巨大,且害怕卷入中英外交瓜葛,故廣東官員的安排未能成功[11]Vol.I:451;Vol.II:14。乾隆皇帝對英使團訪華表現出極大興趣,并專門下旨安排通事接待使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以下簡稱“一史館”)(一史館,內閣檔案:10,見文獻[12]),下同。由于當時中國并無通曉英語之翻譯人才,且清政府長久以來都依賴在宮廷服務的西方傳教士處理外交事務,故清廷派出七名在京西洋傳教士作為翻譯,他們是葡籍教士索德超(Joseph-Bernard d’Almeida)、安國寧(André Rodriguez),法籍教士賀清泰(Louis de Poirot)、巴茂正(Joseph Pairs)、羅廣祥(Nicholas Joseph Raux),意大利籍教士潘廷璋(Joseph Panzi)、德天賜(Peter Adéodat),這些傳教士也不懂英語,他們使用拉丁語為使團服務。
四、譯者何為
馬戛爾尼使團訪華拉開中英正式外交關系的序幕,英方聘請了不懂英語、毫無外交經驗的中國人做翻譯,中方委任同樣不通英語的歐洲傳教士為通事,雙方譯員以拉丁語為中介艱難地在清廷與英使團之間架起溝通的橋梁。在此過程中,雙方譯員的工作遠遠超過普通外交翻譯的職責。
斯當東認為他物色到的中國翻譯“能勝任其母語與意大利語或拉丁語之間的翻譯”[7]292,后來的事實證明這樣的評價過于樂觀。李雅各年僅13歲時就去了歐洲,闊別20年后回國,對中國只有一些模糊的記憶。對中國文字已經生疏,同時他也不熟習中國宮廷文字的體裁格式(321)。此外,李雅各毫無中國官場經驗,往往對官場上的客套話和委婉語信以為真[11]Vol.II:136,Vol.I:330。盡管李雅各的語言和翻譯能力差強人意,但他對英使團的忠誠是毋庸置疑的。他非但沒有像另外那名中國翻譯周保羅一樣,因害怕為外國人工作受到清政府懲罰而撇下使團離開,反而穿上英國服裝、喬裝成英國人,非常堅定地維護使團利益,他所做的有時完全超出了譯員的職責。乾隆見禮品單上馬戛爾尼的頭銜被譯為“欽差”,馬上下令將之改為“貢使”以符合天朝體制,之后在圓明園組織安裝設備,李雅各仍堅稱英國送給中國皇帝的是“禮品”而非“貢品”[13]40,盡力為英國爭取平等地位;在熱河期間,馬戛爾尼擔心欽差大臣徽瑞不及時奏報,決定直接把信交給中堂大人和珅,當時沒人敢瞞著徽瑞私自送信,最后是李雅各自告奮勇圓滿完成了任務,據說沿途他還遭到民眾騷擾和侮辱[11]Vol.II:255);當馬戛爾尼拒絕練習三跪九叩覲見禮后,護送使團入京的王文雄、喬人杰兩位大人要求李雅各示范一遍,但李雅各斷然拒絕這一要求,維護英方尊嚴[14]90。有論者評價李雅各是“忠實的仆人,不稱職的翻譯”[15]30,這應該是對他在英使團工作的準確概括。
另外,年僅12歲的小斯當東憑借過人的聰穎和學習能力,快速地掌握了漢語并學會寫漢字,成為英使團意外收獲的“譯員”。當使團第一次和北京派來的官員會面時,由于人數眾多,李雅各一人應付不過來,小斯當東便試著做翻譯,效果很不錯[11]Vol.I:489;他還參與禮品單的翻譯[14]100,這項任務很不簡單,為突顯禮物的貴重,馬戛爾尼在禮品單里對各項禮物作了詳細說明,所以翻譯時頗費苦心;此外,小斯當東還擔任謄抄中譯文的工作[11]Vol.II:142,一些重要文件比如馬戛爾尼有關覲見儀式的照會,雖然有人譯成中文,但因害怕被認出筆跡,沒人愿意謄寫,最后就讓小斯當東重寫一遍,并加上一句“此呈系咤株士多嗎嘶噹東親手寫”(一史館,軍機處檔案:232)。
英方翻譯人員構成比較簡單,他們盡忠職守地為英使團服務,但清廷派出的由索德超為首的西洋教士翻譯團,情況就更復雜一些了。
一開始索德超便獲委任為“通事帶領”(一史館,內閣檔案:10),即首席翻譯,負責使團的接待和翻譯工作,馬戛爾尼在與索德超見面之前就從法籍教士梁棟材(Joseph de Grammont)處獲悉索氏對使團懷有敵意,故馬戛爾尼故意以法語和英語跟索德超交談,使他無法完成翻譯工作,進而謝絕他的服務。但索德超顯然深受清廷重用,當馬戛爾尼與乾隆在熱河會面時,索德超被派往熱河,負責帶領馬戛爾尼一行等候乾隆的接見(一史館,文獻:600),除此以外,索德超主要在朝廷方面工作。清廷檔案中記載索德超進行過直接翻譯的工作,如軍機處檔案記有馬戛爾尼的信函交由索德超負責翻譯(一史館,軍機處檔案:198);他還負責查核他人的翻譯是否準確,包括馬戛爾尼送來的呈詞和乾隆寫給英國國王勅諭的翻譯(一史館,軍機處檔案:203,245);此外他還被派去察看馬戛爾尼贈送儀器的運作情況(一史館,軍機處檔案:146)。
馬戛爾尼拒絕索德超為使團效勞,并向清廷提出委派一名懂歐洲語言的教士作翻譯,朝廷便派來法國遣使會教士、法國傳教會會長羅廣祥,負責照顧使團。馬戛爾尼對羅廣祥印象非常好,并從他那里知道很多有關清廷和乾隆的情況。此外,羅廣祥還參與翻譯過一份很重要的文件——馬戛爾尼覲見乾隆皇帝的禮儀照會[14];他還與賀清泰合譯出乾隆致英國國王第二道勅諭。乾隆派出的翻譯團里其他傳教士也在不同程度上參與了翻譯工作,主要是學習安裝英國人帶來的機械禮品,并兼任翻譯,對于使團的實際運作,他們并沒有什么直接影響。
然而,這些不同國籍的傳教士在北京不光是擔任翻譯那么簡單,他們“充當各自的國家在中國的代理人,遇有涉及本國利益的事項,他們總要進行些活動”[11]。由于政治利益、宗教派系等矛盾,不同國籍的傳教士都在明爭暗斗、相互排斥,總的來說,葡萄牙的傳教士自成一派,而其他國家的教士則結成另一集團,相互間存在著嚴重的矛盾[3]。不同國籍的傳教士對待英使團的態度也大不相同。以索德超為首的葡籍傳教士對英使團很不友好,他們擔心英國如果加深對華關系會威脅到葡萄牙在華利益,出于維護本國在華優勢和對英國的嫉妒,他們對英使團的外交活動進行破壞。在去熱河之前,當馬戛爾尼提出讓英使團先從駐地圓明園里的宏雅園移居北京城里時,索德超對此百般阻擾[13]36-37。更有甚者,在馬戛爾尼使團離開中國之后,索德超等葡籍傳教士仍在散布謠言,力圖破壞英使團的聲譽[13]37。相反,法國和意大利傳教士對英國則友好得多。在他們看來,如果歐洲與中國有更好的關系,福音的傳播可能有較大的進展,而他們將獨得傳教的好處,畢竟在傳道的問題上,他們無須懼怕英國人[10]437。基于此,在翻譯乾隆致英國國王第二道敕書時,兩位法國傳教士故意緩和原文語氣,并加入一些對英王致敬的詞語[16]137。可見,清廷派出的傳教士翻譯團都是以自身宗教利益和所代表的國家利益為重,并沒有忠心耿耿地為清廷服務。
五、結語
有論者認為缺乏合格的譯者和翻譯是馬戛爾尼使團失敗的一個重要因素[3]。且不論這樣的評價是否有夸張之嫌,但中英首次外交中的第三方——譯者不應被忽視。由于歷史語境的限制,中英雙方都無法從本國人中選出合適的譯員,而是非常巧合地使用了對方的人:英方聘請了中國人做翻譯,而中方派出在京歐洲傳教士任通事。盡管雙方譯員或因語言能力差強人意,或為自身利益不顧大體,在某種意義上夠不上稱職的外交翻譯人員,但他們決不只是史書上一筆帶過稱作“通事”的幾個名字。他們有自己的國家觀、外交觀和價值觀,在英使團訪華事件里,要么積極維護使團利益,要么竭力阻撓使團成功,他們的行為遠遠超過普通外交翻譯的工作范疇,在不知不覺中影響甚至改變了歷史的進程。
[1]王輝.天朝話語與喬治三世致乾隆皇帝書的清宮譯文[J].中國翻譯,2009(1):27-32.
[2]葛劍雄.世界上不止有中文[J].讀書,1994(11):185-188.
[3]王宏志.馬戛爾尼使華的翻譯問題[J].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9(63):97-145.
[4]Morse,H.B.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53-1834[M].Oxford:Clarendon Press,1926.
[5]一史館.朱批奏折·外交類:第37號[M]//清實錄.第16 冊[C].北京:中華書局,1988,760-1.
[6]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95.
[7]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M].葉篤義,譯.香港:三聯書店,1994.
[8]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上)[M].臺北:學生書局,1969.
[9]Pritchard,E.H.The Crucial Years of Anglo-Chinese Relations,1750—1800 [M].New York:Octagon Books,1970.
[10]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M].王國卿,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11]Staunton,George.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M].London:Pall-Mall,1797.
[12]一史館.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M].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
[13]馬戛爾尼.1793乾隆英使覲見記[M].劉半農,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14]Cranmer-Byng,J.L.et al.An Embassy to China:Lord Macartney’s Journal,1793—1794[C].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99.
[15]季壓西,陳偉民.中國近代通事[M].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
[16]戴廷杰.兼聽則明——馬戛爾尼使華再探[M]//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