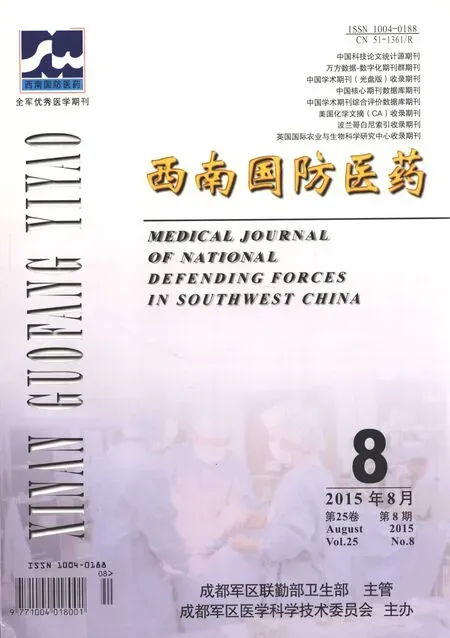鮑曼不動桿菌脊柱深部感染合并真性紅細胞增多癥1例
陸維,王均,馬金星,吳明正,陸聲
鮑曼不動桿菌脊柱深部感染合并真性紅細胞增多癥1例
陸維,王均,馬金星,吳明正,陸聲
鮑曼不動桿菌;脊柱;感染;真性紅細胞增多癥
病例男,58歲,因“腰痛6年,加重伴雙下肢疼痛、麻木半月”入院。患者6年前無明顯誘因出現腰背部疼痛,為持續性鈍痛,活動時加重,未行任何治療。半月前無明顯誘因出現腰痛加重,并出現左下肢放射性疼痛,疼痛沿大腿背側、小腿前外側至踝關節,并出現雙小腿麻木,期間患者無低熱、盜汗、咳嗽等。到當地醫院就診,予以消腫鎮痛、包中藥、針灸、理療等一般對癥治療,疼痛無明顯緩解。既往有雙下肢靜脈曲張結扎術手術史;診斷為“真性紅細胞增多癥”2年,規律服用羥基脲片,無特殊不適。門診行MRI示:腰椎退行性變,L4~S1椎間盤突出并中央偏右型突出,椎管狹窄,遂以“L4~S1椎間盤突出癥并椎管狹窄;真性紅細胞增多癥”收住院。入院后完善相關輔助檢查后,未見明顯手術禁忌證,于我院行經后路L4~S1椎間盤摘除、椎板切開減壓、Cage置入、釘棒系統內固定術,術后予以補液、止痛、維持電解質平衡一般對癥處理,常規換藥。術后第10 d傷口仍有炎性滲出,予以抗炎治療后,分泌物逐漸增多,并出現發熱,體溫38~40℃,血象、C-反應蛋白(CRP)及紅細胞沉降率(ESR)均明顯升高,考慮"腰椎內固定術后感染",再次收治入院。
體格檢查:腰部可見一長約8 cm手術切口,傷口紅腫,有炎性分泌物,皮溫升高。L4~S1棘突及棘旁突有壓痛及叩擊痛,雙側直腿抬高試驗及加強試驗陽性,臀部及雙下肢感覺減退。
實驗室檢查:白細胞17.32×109/L,中性粒細胞91.7%,ESR 27mm/h,CRP 41mg/L。
治療經過:規律服用羥基脲片。MRI提示:腰背部組織明顯水腫并見條片狀T1長T2液性信號及斑片狀長T1、短T2信號,提示感染可能。取傷口深部分泌物做細菌培養及藥敏試驗,結果顯示:鮑曼不動桿菌生長。根據藥敏結果依次予以左氧氟沙星、頭孢曲松、亞胺培南進行治療。直到入院后第5 d(使用亞胺培南第2 d),患者體溫控制后,在全麻下行腰椎術后感染清創術。術中皮下組織有大量暗紅色滲出液,逐層分離可見L4~S1椎體周圍有炎性組織生長并覆蓋椎體,且明顯水腫。術中予以徹底清除病變組織及黏稠分泌物;術后予以慶大霉素鹽水持續沖洗傷口,約5000 ml/d。術后感染仍不能控制,傷口有膿性分泌物,并反復熱遂于10 d后行第2次清創手術,取出椎弓根螺釘保留椎間融合器,并放置VSD負壓引流;術后14 d取出VSD。此后患者仍反復發熱,白細胞計數降至2.3×109/L,并間斷出現低體溫。請血液科會診后,考慮為感染,同時因長期服用羥基脲后骨髓抑制導致白細胞下降,予以重組人粒細胞因子注射液150μg皮下注射,1次/d,加速粒細胞數的恢復,連用5 d,觀察白細胞計數穩定后停用;給予亞胺培南1 g/次,1次/8 h,4w后換口服米諾環素膠囊100mg,2次/d,連續4個月。患者體溫逐漸恢復正常,傷口愈合,腰骶部疼痛及雙下肢麻木消失。術后CPR、ESR及WBC逐漸恢復正常,術后6個月檢測:白細胞6.53×109/L,ESR 7 mm/h,CRP 6 mg/L。末次手術后18個月X線提示:椎間隙植骨已融合,脊柱穩定,患者拆除腰圍,可棄拐行走。
討論脊柱內固定術后深部感染是脊柱手術的嚴重并發癥之一,文獻報道發生率為0.7%~11.0%,可造成局部軟組織腫脹充血、皮膚肌肉等軟組織壞死,甚至鋼板外露,臨床治療非常棘手[1]。隨著內固定器或假體植入在脊柱外科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高,術后感染發生率越來越高。脊柱感染除有效應用抗生素外,應及時行清創并清除病灶、消毒傷口及內固定物,放置引流管持續沖洗,爭取傷口早期愈合;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取除內固定物也是必要的[2]。CRP及ESR對于脊柱感染診斷雖然沒有特異性,但脊柱感染時兩者均有不同程度的升高,因此,在脊柱感染的診療過程中,密切監測ESR及CRP的變化,可作為反映病情變化的一項重要指標,對治療有一定的指導作用[3]。
鮑曼不動桿菌(Acinetobacter baumannii,Ab)為非發酵葡萄糖、革蘭染色陰性、無動力的雙球菌或球桿菌,普遍存在于自然界和人體。近年來,多耐藥鮑曼不動桿菌(MDR-Ab)、甚至泛耐藥鮑曼不動桿菌(PDR-Ab)醫院內暴發流行逐漸增多,已成為21世紀抗感染治療的巨大挑戰[4]。目前對其治療手段有限,多種藥物聯合治療方案成為了臨床治療的首選[5-7]。
真性紅細胞增多癥(PV)是一種克隆性、以紅系細胞異常增生為主的慢性骨髓增生性疾病。在以往報道中,脊柱內固定術后鮑曼不動桿菌的感染并不罕見。而本例的特殊性在于,合并有真性紅細胞增多癥。本例術前診斷PV 2年,長期規律服用羥基脲片,病情控制尚可。但由于感染以及手術應激導致患者體質減弱,白細胞異常下降,盡管予以藥物及手術等綜合治療,仍不能取得滿意的效果,且癥狀進行性加重。因此,在治療脊柱感染時,不僅要早期診斷并制定適當的治療方案,還應該關注患者整體健康狀態,對于患有多種基礎疾病的患者,治療其原發病也是治療脊柱感染的關鍵。
[1]Mok JM,PekmezeiM,Piper SL,et al.Use of C-reactive protein after spinal surgery:comparison with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as predictor of early postoperative infectious complications [J].Spine,2008,33(4):415-421.
[2]王征.胸腰椎脊柱后路椎弓根螺釘系統內固定術后遲發性感染處理[J].解放軍醫學雜志,2006,31:601.
[3]王巖,張雪松,肖嵩華,等.脊柱內固定術后深部感染[J].中華醫學雜志,2006,86(25):1737-1739.
[4]張玲玲,張永.多耐藥鮑曼不動桿菌感染治療方案及控制策略[J].國際呼吸雜志,2011,31(21):1646-1649.
[5]陳佰義,何禮賢,胡必杰,等.中國鮑曼不動桿菌感染診治與防控專家共識[J].中國醫藥科學,2012,2(8):3-8.
[6]楊坤祥,嚴偉玲,羅曉琳.惠州地區嬰幼兒鮑曼不動桿菌462株感染的耐藥性分析[J].現代醫院,2013,10:49.
[7]張志強,陳國強,曹海燕.689株鮑曼不動桿菌的臨床分布及耐藥性分析[J].現代醫院,2014,10:49.
R 516
B
1004-0188(2015)08-封三-02
10.3969/j.issn.1004-0188.2015.08.050
2015-04-04)
成都軍區醫學科學技術研究計劃項目(C12048)
650032昆明,成都軍區昆明總醫院(陸維,王均,馬金星,陸聲);昆明醫科大學成都軍區昆明總醫院臨床學院(陸維,王均,馬金星);昆明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吳明正)
陸聲,E-mail:drlshe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