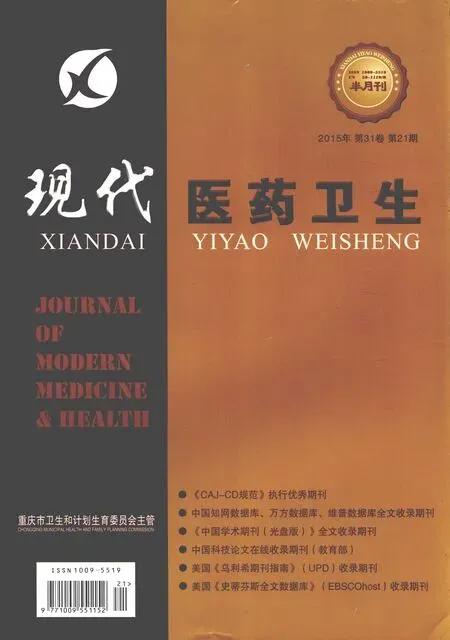胃腸道間質瘤30例臨床病理及免疫組織化學分析
秦雙立,張鐘鳳
(1.江蘇護理職業學院,江蘇淮安223001;2.貴陽醫學院附屬醫院病理科,貴州貴陽550004)
胃腸道間質瘤30例臨床病理及免疫組織化學分析
秦雙立1,張鐘鳳2
(1.江蘇護理職業學院,江蘇淮安223001;2.貴陽醫學院附屬醫院病理科,貴州貴陽550004)
目的 探究胃腸道間質瘤的臨床病理及免疫組織化學分析。方法 選取2005年9月至2014年9月貴陽醫學院附屬醫院診治的30例胃腸道間質瘤患者,對其臨床病理及免疫組織化學結果進行分析。結果 所選的30例胃腸道間質瘤(GIST)免疫組化結果:其中DOG1陽性27例,陽性率為90.0%;CD117陽性26例,陽性率為86.7%;CD34陽性23例,陽性率為76.7%;S-100和Actin的著色強度和陽性細胞數均較弱而且少,陽性率分別為13.8%、31.0%。3種性質的腫瘤DOG1、CD117、CD34表達的陽性率無明顯差異,三者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GIST惡性程度與DOG1、CD117、CD34表達的陽性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結論 在GIST中DOG1、CD34、CD117的陽性表達與交界性、良性、惡性診斷和腫瘤的大小、部位、生物學行為未見明顯相關性。GIST在臨床上可以有不同的疾病過程,其復發、轉移的風險高低與腫瘤部位、大小和核分裂有關。
胃腸腫瘤/診斷; 間皮瘤/診斷; 回顧性研究; 病理學,臨床; 免疫組織化學
胃腸道間質瘤(GIST)是臨床不多見的一種消化系統間葉源性腫瘤,好發于胃。過去因醫學技術有限,這種腫瘤始終被誤診為神經鞘膜瘤或平滑肌瘤。近幾年來,因免疫組化技術的不斷發展,不斷提升了GIST的診斷陽性率[1]。作者選取2005年9月至2014年9月貴陽醫學院附屬醫院診治的30例GIST患者,對其臨床病理及免疫組織化學結果進行分析,為臨床提供更加準確的診斷依據,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30例患者中男19例,女11例;年齡42~77歲,平均(54.2±2.6)歲;病程半個月至3年,平均(1.8±0.3)年;主要表現:吞咽異物感2例,腹部脹痛或隱脹不適21例,血便、黑便3例,腹部包塊2例,無癥狀2例;腫瘤部位:食管2例,胃14例,小腸8例,結腸2例,直腸2例,腸系膜2例,所有患者均實施超聲或內鏡、CT檢查。
1.2 方法
1.2.1 檢驗方法 對所選患者標本進行取材,然后用10%的中性緩沖甲醛進行固定、脫水、透明,組織用石蠟包埋,取4 μm厚度進行連續切片,蘇木精-伊紅(HE)染色,光鏡觀察。所有的患者標本均進行免疫組化DOG1、CD117、Actin、CD34、S-100檢查。
1.2.2 染色結果判定 DOG1、CD117、Actin、CD34、S-100陽性表達定義在細胞質或細胞膜,無著色為(-),陽性細胞不超過10%為(+),11%~50%為(++),超過50%為(+++)。
1.3 統計學處理 應用SPSS18.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數資料以率或構成比表示,采用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 果
2.1 病理檢查 (1)巨檢:腫瘤位于食道的2例患者腫物相對較小,通過手術剜除或內鏡套扎去除。14例來源于胃壁的腫塊表面黏膜潰瘍,黏膜隆起。直腸、結腸、小腸病例腫物均來源于腸壁間。其中腫瘤最大的4例出現在腸系膜和小腸,腫瘤最小的位于食道,有8例患者腫瘤同時存在囊性變及出血區,或伴壞死灶[2]。(2)鏡檢:所選的30例患者中22例以梭形細胞為主型,腫瘤細胞排列不規則,呈漩渦狀、束狀及編織狀,細胞核呈短梭形或卵圓形,染色質細致,核仁不明顯或很小。2例主型為上皮樣細胞,細胞質呈嗜酸性,一些腫瘤胞質透亮、印戒樣或空泡狀。7例為混合型,1例為多形細胞性,瘤細胞具有獨特的異型性,多見奇異型核及巨核。核分裂象差異很大、多少不一。瘤細胞間存在水浪不等的膠原纖維,7例患者存在明顯的黏液變區。
2.2 免疫組化結果 DOG1陽性27例,陽性率為90.0%;CD117陽性26例,陽性率為86.7%;CD34例陽性23例,陽性率為76.7%;S-100和Actin的著色強度和陽性細胞數均較弱而且少,陽性率分別為13.8%和31.0%。
2.3 良性、交界性、惡性胃腸道間質瘤的DOG1、CD117、CD34表達比較 通過分析可以發現,3種性質的腫瘤DOGI、CD117、CD34表達的陽性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GIST惡性程度與DOG1、CD117、CD34表達的陽性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3 討 論
1998年,GIST分子病理學研究發現大部分GIST伴c-kit基因功能獲得性突變,表達c-kit基因的蛋白產物CD117是GIST分子病理學特征。2003年,Heinrish等在無c-kit基因突變的GIST中,發現有PDGFRA基因的突變。研究學者發現了GIST多數由突變的c-kit或血小板源性生長因子受體(PDGFRA)基因驅動。GIST屬于一種消化道間葉組織腫瘤,可在胃腸道的各個部位發病,多數發生于胃(60%~70%),20%~30%發生于小腸,1%~5%見于結直腸,食管發生者少于5%[3]。表現為惡性的GIST占20%~30%,大部分在第1次就診時就出現轉移[4]。GIST主要見于中老年患者,其病理組織學形態結構排列變化復雜,細胞形態各異,最常見的表現是觸及腫塊與胃腸道出血[5]。
GIST遺傳學上頻發c-kit基因突變,組織學以富于梭形細胞為特征,本組22例為梭形細胞。CD117和(或)CD34在GIST中有高表達率,是區別GIST與平滑肌腫瘤及神經鞘瘤的重要標記物。CD117是癌基因c-kit的蛋白產物,CD34是一種骨髓造血前體細胞標記物,二者在GIST中的表達分別高達81%~100%和50%~80%[6],本組CD117和CD34表達率分別為86.7%和76.7%。因此,術后標本行免疫組化檢測CD117及CD34并結合光學顯微鏡下細胞形態學檢查是確診GIST可靠的方法。GIST良惡性的判定可以參考Emory等[7]提出的標準,將其分為良性、潛在惡性及惡性。肯定的惡性指標:(1)腫瘤出現遠、近器官的轉移;(2)腫瘤具有浸潤性。有潛在惡性的指標:(1)腫瘤直徑大于5.5 cm;(2)核分裂象大于每50 HPF 5個;(3)腫瘤壞死;(4)細胞異型性明顯;(5)細胞豐富,生長活躍。無任何惡性指標者為良性間質瘤,有1項潛在惡性指標者為潛在惡性間質瘤,具有1項肯定惡性指標或具有2項潛在惡性指標者為惡性間質瘤。惡性者可出現復發或轉移,常見的轉移部位為肝、腹膜和肺。
免疫學表型主要表明細胞的分化程度或方向,其與GIST的生物學行為之間未證實存在必然的聯系,良惡性GIST的免疫表型基本相同[8]。功能未知蛋白(DOG1)是由DOG1基因編碼的一種蛋白質,為8個跨膜區域組成的、鈣調節的氯化物通道蛋白,是最近發現的在GIST中特異表達的一種細胞膜表面蛋白,王玨基等[9]發現在139例GIST組織中有136例有DOG1表達,CD117陰性的胃腸道間質腫瘤中DOG1都有較強的表達,并且在438例非GIST瘤中僅4例有DOG1的表達。這些都提示DOG1是一個敏感和特異的GIST診斷標志物,尤其適用于CD117和c-kit及PDGFRA突變基因檢測陰性的GIST診斷。本組中,27例DOG1陽性,陽性率為90.0%;26例CD117為陽性,陽性率為86.7%;23例CD34例為陽性,陽性率為76.7%;但是DOG1、CD34、CD117表達的陽性率與腫瘤良惡性無明顯相關性。現CD117和CD34僅作為GIST的診斷標志,其表達的陽性率不作為其良惡性的判斷指標。
GIST對放療和化療不敏感,手術治療是目前首選的治療方案,其預后主要取決于腫瘤的良惡性和治療是否及時,GIST的良惡性常以多個參數來評估。不同科研人員提出的良惡性評估標準有差異,但多數認為,腫瘤的大小和核分裂象是關系到腫瘤良惡性和患者預后、生存的最重要因素。有文獻報道,當腫瘤的直徑大于5 cm、核分裂象大于每50 HPF 5個即認為具有惡性潛能[10]。但是目前沒有一種方案能對所有病例準確地判定良、惡性,還需結合多項因素綜合判斷,如腫瘤直徑、核分裂象、腫瘤壞死、核異型性、瘤細胞密度、細胞大小、非整倍體DNA含量、Ki-67表達等。腫瘤的大小和核分裂象數量是最為重要的參數。美國國立衛生研究所的GIST工作組建議以腫瘤最大徑結合核分裂象數量來評估GIST的惡性潛能。
本文通過對所選的患者進行分析,27例DOG1陽性,陽性率為90.0%;26例CD117為陽性,陽性率為86.7%;23例CD34為陽性,陽性率為76.7%;S-100和Actin的著色強度和陽性細胞數均較弱而且少,陽性率分別為13.8%和31.0%,3種性質的腫瘤DOG1、CD117、CD34表達的陽性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GIST惡性程度與DOG1、CD117、CD34表達的陽性率無明顯相關性,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綜上所述,在GIST中DOG1、CD34、CD117的陽性表達與交界性、良性、惡性診斷和腫瘤的大小、部位、生物學行為未見明顯相關性。GIST在臨床上可以有不同的疾病過程,其復發、轉移的風險高低與腫瘤部位、大小和核分裂有關。
[1]范乘龍,李芝清.胃腸道間質瘤78例臨床病理及免疫組織化學特征[J].實用腫瘤雜志,2010,24(5):581-583.
[2]侯英勇,朱雄增.胃腸間質瘤惡性程度的判斷及其對預后的影響[J].中國實用外科雜志,2010,30(4):265-269.
[3]陳杰,李甘地.病理學[M].2版.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1:268.
[4]楊蘭生,尹鵬,許傳屾.胃癌組織中粘蛋白1和基質金屬蛋白酶9的表達與臨床病理特征的關系[J].蘭州大學學報:醫學版,2010,36(1):20-23.
[5]張紅珠,張翠萍,張琪,等.MST1與YAP1在食管疾病中的表達及意義[J].青島大學醫學院學報,2014,40(1):62-63.
[6]Miettinen M,Lasota J.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review on morphology,molecular pathology,prognosis,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J].Arch Pathol Lab Med,2006,130(10):1466-1478.
[7]Emory TS,Sobin LH,Lukes L,et al.Prognosis of gastrointestinal smoothmuscle tumors:dependence on anatomic site[J].Am J Surg Pathol,1999,23(1):82-87.
[8]Mittinen M,Lasota J.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 definition,histological,immunohistochemical,and molecular genetic feature and defferential diagnosis[J].Virchows Arch,2001,438(1):1-12.
[9]王玨基,丁克峰,陳麗榮,等.胃腸道間質瘤32例的診斷和臨床病理特征分析[J].中華普通外科雜志,2004,19(6):340-342.
[10]Wang X,Mori I,Tang W.Helpful parameter for malignantpotential of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GISTs)[J].Jpn J Clin Oncol,2002,32(9):347-351.
10.3969/j.issn.1009-5519.2015.21.034
B
1009-5519(2015)21-3294-02
2015-06-24)
秦雙立(1982-),男,江蘇淮安人,碩士研究生,病理技師,主要從事生命科學的研究;E-mail:qsl051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