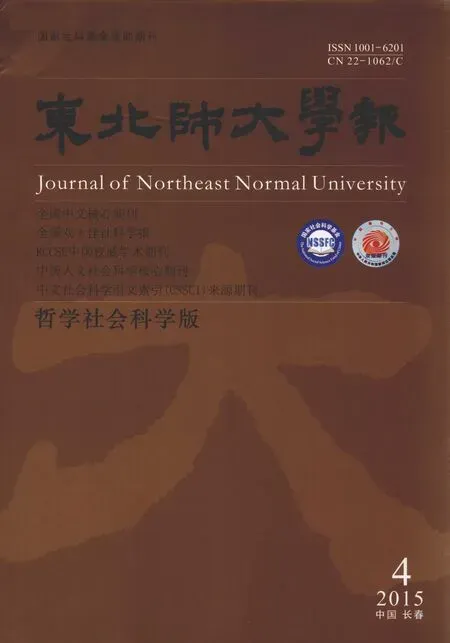技術進步方向、要素收入分配不平等和政策非對稱沖擊
董直慶,宋 偉,蔡 嘯
(1.吉林大學 數量經濟研究中心,吉林 長春130012;2.華東師范大學 商學院,上海200241)
一、前 言
學術界對收入分配不平等問題的關注由來已久,從帕累托(Pareto,1897)對收入分配不平等問題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以來,大量文獻已經對不平等的測度、產生的原因及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系統的研究[1]。近期關于不平等問題的研究,更多關注不平等持續性與初始分配的關系以及不平等持續性的動態特征。Caselli&Ventura(2000)發現,在特定形式的儲蓄函數假定下,如果經濟中不存在個人能力差異和隨機沖擊且市場完善,那么經濟中存在一個穩定的完全平等狀態[2]。隨著時間推移,收入和財富分配的不平等最終會趨于消失,初始財富分配不平等和一次性財富分配的沖擊將不影響收入和財富分配的持續性不平等。王弟海和龔六堂(2006)結合新古典內生經濟增長模型框架,建立起一個無增長且代際相聯的理論模型,討論在存在遺產機制的作用下,由個人偏好與能力差異進而產生資本收入和勞動收入的持續不平等及其動態的變化特征[3]。模型演繹結果發現,在競爭性和完善市場的假定下,存在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平等的穩定狀態,而這種不平等水平主要歸結于個體偏好、個體勞動能力以及隨機收入的差異。特別地,穩定的不平等水平與真實不平等程度無關。
然而,這類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研究并未涉及技術進步的影響,直至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出現了工資不平等逐漸加劇的現象,這一現象誘使學術界重新關注技術進步偏向性的影響。Acemoglu(1998)引入研究部門(R&D)來內生化技術進步偏向性形成過程[4]。模型結果發現,勞動力中高技術工人比例的不斷提高,與高技術工人勞動呈現出互補性技術會有更大的市場,進而引導研發部門提高對與高技術工人互補技術的研發,結果是,不同類型勞動工資差距短期內先呈現出下降、而后上升甚至可能超過其期初值的現象。因為研發部門對于與高技術工人相互補的技術研發需要時間,且這種研發中出現的技術選擇性偏向,會導致生產技術的技能偏向,進而改變技能和非技能勞動的工資差距。Kiley(1998)構造了一個不同于Acemoglu(1998)的內生化模型,將技術進步對技能勞動和非技能勞動偏向性內生化,得到與Acemoglu模型基本一致的結論,即與技能勞動和非技能勞動相對應的技能的“數量”與兩種勞動力的數量成正比,而技能勞動“數量”需要對技能勞動投入數量進行調整來實現,在調整期中會暫時降低勞動工資差距[5]。當調整完成后工資差距不僅不會縮小而且會超出原值,新調整的技術組合導致總產出增速放緩。Galor和Moav(2004)將技能勞動與非技能勞動對新技術的適應時間引入到內生模型中,當新技術出現時技能勞動顯示出更低的調整成本并以更快的時間去適應新技術,當技能勞動已完全適應新技術并開始有效地投入生產時,非技能勞動仍然處在過渡階段,生產率差異使二者的工資差距擴大[6]。但當非技能勞動也掌握了新生技術,工資差距會下降。表明技術進步方向對工資差距的影響,可能并不會使非技能勞動的分配地位永久變化。董直慶、蔡嘯和王林輝(2014)構建內生經濟增長模型探討教育選擇、技術進步和技能溢價三者關系,通過數值模擬方法分析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對我國勞動力結構以及技能溢價的作用強度[7]。技能勞動內生化選擇結果發現,技術進步方向可以通過改變個體對勞動屬性的選擇,進而改變不同性質勞動報酬[8]。
當然,工資收入只是個體收入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文獻易關注工資收入不平等,忽視資本收入對總收入的作用,而技術進步方向的研究也局限在技術進步在技能工人和非技能工人間的偏向,沒有考慮技術進步在勞動和資本的偏向程度會對收入分配不平等帶來什么樣的影響。在現代收入分配過程中,資本已成為最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并參與社會財富分配,忽視資本收入將使收入分配問題判定出現偏誤。本文與其他文獻的區別有二:一是將資本增進型技術進步與勞動增進型技術進步引入CES生產函數,從模型角度數理演繹探討兩種不同類型技術進步的變化對不平等的影響。二是引入政府行為,考慮技術進步外生和內生兩種情況下,不同政策強度如何改變不平等及穩態不平等特性。本文的剩余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構建包含政府政策以及技術進步偏向性的理論模型。第三部分根據我國宏觀數據對模型參數進行校準,用數值模擬的方法對模型結果進行推演和分析。第四部分基本結論。
二、理論模型
假定總量生產函數仍為不變替代彈性系數的CES生產函數:

其中Yt、Kt和Lt分別為t期總產出、資本和勞動,A表示中性技術進步,φ為資本增進型技術進步。生產要素處于自由市場環境中,政府征收資本和勞動報酬所得稅,稅率分別為ηk和ηl。
那么,收入法表示經濟產出為:

其中rt和wt為無所得稅時的資本和勞動的邊際報酬,Gt為政府總收入,上式將經濟總產出分成三部分:稅后資本收入、稅后勞動收入與政府收入。其在總產出中對應的比例即為資本、勞動與政府的收入份額,用公式表示為:

個體i在第t期的總收入為:

其中yi,t代表t期個體i的總收 入,CFi,t-1代表個體i在t-1期消費后的剩余收入,其作為財產繼承到t期,并在t期進行投資,(2)右側第一項為t期個體的財產性收入。Li,t為個體i提供的有效勞動,(2)右側第二項為個體t期的勞動收入。上式說明個體收入來源于稅后勞動收入和個體繼承的財產在當期的收入。依據王弟海和龔六堂(2007)的研究思路,假定個體資產滿足如下積累過程:

其中,ci,t為個體i在第t期的消費支出,假設個體i的儲蓄率為s(固定為常數),則:

假設個體勞動供給Li,t服從正態分布Li,t~N(1,σ2L),且與財產分布不相關,則:

(3)式E(CFt)表征財產的均值,(4)式表示財產在個體間不平等程度。(4)式右側第一項代表由投資帶來的收入不平等,第二項代表個體勞動能力差異引發的收入不平等。
用變異系數來表征全社會不平等的程度,公式如下:

那么資本勞動收入份額分別為:

資本和勞動的邊際報酬rt和wt可由(1)式對資本和勞動求導得到,帶入(3)式,有

在一定條件下E(CFt)會收斂至穩定值,記為,滿足如下函數:

此時,對應穩定資本和勞動收入份額為:

穩定狀態的收入相對不平等程度為:

將(7)式帶入(6)式,消去可得函數:

(9)式隱函數暗示,穩態時資本收入份額受中性技術進步、資本偏向型技術進步和政府稅收水平共同影響。下面我們將分析技術沖擊和政府稅收政策變化對穩態資本收入份額和相對不平等水平的影響。首先分析技術沖擊的影響。(9)式對A和φ求偏導,有

表明,中性技術進步和資本偏向型技術進步對資本增進型技術進步的作用方向一致,其取決于政府收入份額的大小,若政府收入份額較小,則中性和資本增進型技術進步的增加都會引起穩態資本收入份額的減小;反之,當時,兩種技術沖擊會增大穩態資本收入份額。在實際中接近于1,而政府收入份額不會太大,所以一般情況下成立,即技術沖擊會降低穩態時資本的收入份額。將(6)式和(7)式帶入(8)式得:

由(9)式可知,[(ηl-ηk)+(1-ηk)(1-ηl)]>0,所以當升高時,Ω下降,即下降,資本收入份額與相對不平等水平成反向變化。即資本增進型技術進步對穩態時收入平等性水平的作用方向與其對資本收入份額的作用方向相反。
結論1:當經濟處于穩態而稅率不變時,中性和資本增進型技術進步對資本收入份額的作用方向一致。若政府收入份額較小,則這兩種技術進步會降低資本份額并加劇收入不平等,反之則相反。
下面分析政府稅收政策變化對穩態資本收入份額和相對不平等水平的影響。
(9)式兩邊對ηk和ηl求導有

根據(10)式有:

將(11)式和(12)帶入上兩式,整理可得:

可知兩種稅率對收入平等的作用方向相同,其方向取決于兩種稅率和政府收入份額:
結論2:在無技術沖擊的穩態環境中,資本收入份額受政府稅收政策影響,若政府收入份額較小,提高資本和勞動稅率將有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水平,勞動稅率的提高會提升資本收入份額;若政府收入份額較大,則繼續增加稅率會擴大相對不平等水平。
上述分析建立在增進型技術進步外生條件下,在現實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支出大部分來自稅收,通常政府稅收收入和支出越多,研發支出比例將越高。而政府研發和補貼強度及技術與產業政策差異,將改變技術研發水平和技術創新方向,進而影響永久收入的積累速度和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為此,我們進一步考察增進型技術進步內生條件下,政府決策對資本收入份額和收入平等性的影響。
假定政府稅收總水平為G,將政府支出分為科研支出和非科研支出,科研支出中用于提升資本增進型技術的投資比例為τk,用于提升勞動增進型技術進步的比例為τl,非科研支出比例為(1-τk-τl)。技術進步表現為知識積累、新技術和新工藝的創新及應用,假設技術創新主要源于政府的研發投入,用公式表示為:{k,l},其中ξ為單位投入的研發成功率,Ak和Al分別代表兩種要素的生產效率,對應于生產函數(1)式中,應有Ak=Aφ,Al=A(1-φ)。
政府通過稅收政策和科研投入兩類途徑,轉變技術進步方向改變要素收入份額和收入平等性。假定稅收政策對資本收入份額的影響有二:一是要素收入稅率改變直接影響資本收入份額,二是稅率變化通過影響政府收入G改變政府科研投入水平,投向增進型技術進步方式影響資本收入份額。
與前述分析相同,對隱函數(7)式求導,此時有:

在(15)式與(16)式中,將政府稅收對資本收入份額的影響分解為稅收政策的直接作用,以及稅收政策通過改變技術進步進而改變資本收入份額的間接作用兩部分。不過,通過(15)式和(16)式直接判斷兩種稅率的作用方向比較困難。同樣,可以推導出稅率對相對不平等水平的影響模型,不過,也難以判斷其作用方向。為此,本文將在下一節用數值模擬的方法來判斷稅收政策的作用效果。
結論3:在技術進步內生和技術進步方向可變約束下,政府稅收政策對資本收入份額的影響方式主要有二:一是通過稅率政策本身直接影響資本收入份額,二是稅率通過影響政府收入水平,改變政府技術研發投入方向和力度,投向增進型技術進步改變資本收入份額和收入平等程度。
三、數值模擬結果與評價
前述模型分析表明,技術進步方向對社會不平等和要素收入分配結構都將產生直接影響。在數據值模擬時,我們與前述部分關于總量生產函數的假定一致,即設定為不變替代彈性系數的CES生產技術:經濟產出和生產要素如資本和勞動數據取自《中國統計年鑒》,1978—1992年資本和勞動報酬的數據來自《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核算歷史資料:1952—1995》;1993—2004年數據來自《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核算歷史資料:1952—2004》,2005—2010年數據分別來自2006—2012年《中國統計年鑒》,產出和資本均以1978年為基期平減處理。在統計資本和勞動收入份額時,需要對政府稅收凈額部分數據進行處理,不過,如何將政府稅收凈額劃歸為資本或勞動報酬,不同文獻處理思路不同。我們認為,如果將政府稅收凈額從生產利潤視角考察,也來自于資本和勞動報酬,依據資本和勞動對經濟產出的貢獻將政府稅收凈額,按比例分別劃歸到資本和勞動要素。
參考 Klump(2007)、戴天仕和徐現祥(2010)、Dong et al.(2012)和董直慶等(2013)對技術進步方向的估計方法,將要素效率增長率設定為Cox-box型,對CES生產函數進行標準化處理,利用非線性似無關相關模型估計參數。結果顯示,資本和勞動要素替代彈性參數ρ=-0.562 5,與上述文獻的結果相似,即要素替代彈性σ<1,其中A=Ak+Alφ=Ak/A。
表1數據顯示:(1)要素替代彈性小于1,表明我國資本和勞動呈現互補關系,資本投資增長將拉動勞動投入增加即吸納就業,這與相關文獻對資本和勞動替代彈性估計相吻合。(2)兩種要素的生產效率表現出明顯的差異性。其中資本生產效率Ak呈現出不斷下降趨勢,從1978年31.505降至2012年的17.517,在30余年時間內下降將近50%。而勞動生產效率Al呈現遞增趨勢,1978年勞動生產效率僅為2.317,到2012年增長到34.254提高了近15倍。1999年以前,中性技術進步A在(33.174,40.295)區間內波動,2000年后中性技術進步由32.862以年平均增長3.8%的速度增至2012年的51.771。而資本增進型技術進步φ在樣本期內不斷下降,從0.931下降至0.338,降幅達64%。由此斷定,我國技術進步總體呈現勞動相對增進型,在要素替代彈性小于1的情況下,技術進步偏向于資本。

表1 我國增進型技術進步及技術進步方向的變化趨勢
根據上述估計結果,可知我國2012年資本生產效率Ak=17.517,勞動生產效率Al=34.254,中性技術進步水平為A=51.771,資本增進型技術進步水平為φ=0.338。以2012年數據作為下面模擬的基礎數據。為保持模型前后的一致性,我們用2011—2012年新增固定資產投資除以2012年總產出度量儲蓄率,計算得s=0.337 0。用2012年全國總稅收除以當年總產出計算平均稅率0.195 2,由于我國沒有直接統計針對投資的稅種數據,參考企業所得稅率25%,近似認為資本稅率為ηk=0.250 0,根據2012年資本以及勞動數據計算得到勞動稅率為ηl=0.154 7。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長率約為3%,假定技術進步的自然增長率為1%,若剩余部分完全為政府研發投入的結果,即假定政府研發投資引發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2%,除以研發總支出得到ξ=0.809 6。政府研發支出比例,即τk+τl,用2013年國家財政教育支出與科學技術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例度量,τk+τl=0.192 8。由于缺少政府科研投入的具體用途,多大比例用于促進何種技術研發的投資難以判斷,觀察表1數據可知,我國勞動增進型技術進步在1978—2012年間穩步增長,而資本增進型技術進步處于下降趨勢,猜測政府對勞動增進型技術進步的投資較大,令兩類技術 投 入 比 為2 即τk=0.128 5 和τl=0.064 3。
表2為所有參數的校準結果。首先驗證稅收政策與技術進步相互獨立時,技術沖擊對穩態變量的影響,此時政府研發投入比例τk=τl=0。令中性技術進步在其2012年值處上下浮動20%,即中性技術進步在(51.771*0.8,51.771*1.2)內變化,資本增進型技術進步在其2012年值處上下浮動30%,即資本增進型技術進步變化范圍為(0.338*0.7,0.338*1.3)。數值模擬中性技術進步和資本增進型技術進步對資本收入份額、收入平等性的影響,結果分別見圖1—2和表3—4。

表2 數值模擬參數的校準結果

圖1 技術進步對資本收入份額的影響

圖2 技術進步對收入不平等水平的影響

表3 技術進步對資本收入份額的影響趨勢

表4 技術進步對不平等的影響趨勢
模擬結果基本吻合了理論模型推斷,其中圖1—2及表3—4中數據顯示:
(1)技術進步對要素收入分配的影響。表3數據顯示,無論資本增進型技術進步在何種水平下,中性技術進步的提高都會減少穩態資本收入份額。例如資本增進型技術進步為0.237時,中性技術進步從41.417增至62.125,資本收入份額由0.344 降至0.272。固定中性技術進步水平,資本增進型技術進步的增加將降低資本收入份額,這與理論模型結論一致。在實際經濟生產過程中,資本和勞動互補,資本增進型技術進步同時也是勞動偏向型,這會提高勞動收入份額而引致資本收入份額的下降。中性技術進步同比例地提高了資本和勞動報酬,在穩態時,勞動收入的提高意味著未來預期收入的增加,這使得人們將更少的資金用于投資,所以資本收入份額降低。另外,結合表1,我國1978—2012年的技術進步方向為中性技術進步增加和資本增進型技術進步的減小,對應表3中的次對角線數據(左下角至右上角),可以看到,模型結果與實際數據相似,資本收入份額在這種變化下略有上升。
(2)技術進步對收入分配平等性的影響。表4數據顯示,中性技術進步或資本增進型技術進步的增加都加劇了社會不平等水平,結合技術進步方向對要素收入分配的影響可知,兩種技術沖擊降低了資本收入份額,引發社會不平等。主要原因是由于資本收入份額變低時勞動收入份額增加,在異質性勞動生產率差異作用下使不同類型勞動報酬分化,引發收入不平等。

圖3 稅收政策對資本收入份額的影響
結合稅收政策不變時技術進步方向轉變對要素收入分配的影響,我們進一步模擬政策對資本收入份額和社會不平等的影響方向和作用強度,其中資本和勞動收入稅率的變化范圍均為(0.1,0.3)。

圖4 稅收政策對收入不平等水平的影響

表5 稅收政策對資本收入份額的影響

表6 稅收政策對收入平等性的影響
由圖3—4和表5—6數據可知:
(1)不同稅收政策可以有效調節要素收入分配結構。首先,若在勞動收入稅不變時征收資本收入稅,將降低資本收入份額,如當勞動收入稅分別處于0.1 到0.3 水平時,資本收入稅率從0.1增加到0.3 時,資本收入份額分別下降了0.05左右。其次,若在勞動收入稅可變的情況下,從表格對角線數據可以看出,在勞動和資本收入稅共同作用下,資本收入份額下降趨緩,在同等降幅內資本收入份額僅下降0.02。表明,勞動收入稅抵減了資本收入稅對資本收入占比的影響。再次,若資本收入稅率保持不變,提高勞動收入的稅率,伴隨勞動收入所得稅率增加則資本收入占比上升,即提高勞動收入稅率,有利于提高資本的收入份額。這與前述預期判斷相符,因為對提高勞動稅率相當于降低了勞動的收益,同時也降低了勞動供給的積極性,因而總體上會降低勞動的收入份額提高資本的收入占比,這也是西歐許多發達國家勞動者不愿過量供給的原因。
(2)不同稅收政策對收入不平等水平產生非對稱影響。首先,在勞動收入稅率保持不變時,資本收入稅率的提升降低了收入不平等水平,表明征收資本收入稅有利于提高社會平等程度,這可能源于資本和勞動在收入分配過程中不平等地位,資本強勢地位的減弱有利于勞動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地位的提高。其次,若資本收入稅率不變,勞動收入稅率提高也明顯有利于抑制社會不平等,且其作用明顯優于資本收入稅,這主要是勞動收入所得稅更有利于平衡異質性勞動報酬分化,尤其是控制高收入者與低收入者收入分配差距。第三,不同勞動收入稅率點對社會收入不平等的抑制效應不同,在較低的勞動收入稅率上,社會相對收入不平等水平下降較慢。勞動收入稅率越大,越有利于降低不平等水平。第四,若同時征收資本和勞動收入稅,則對社會不平等的作用最大,從資本和勞動收入稅率結構為(0.1,0.1)時收入不平等程度為0.278,到收入稅率結構為(0.3,0.3)時收入不平等程度為0.194,使社會相對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30%。
當然,政府稅收政策可以在短期內直接通過改變要素收入水平方式調節社會收入分配。但我們應該看到,在現實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稅收政策在改變要素收入分配結構的作用有限,長期要素收入分配結構的轉變最終將依靠技術進步。為此,模擬政府稅收政策轉變技術進步方向,考察稅收政策如何通過改變技術進步方向,影響要素收入分配結構和收入不平等。政府稅收政策變化對穩態收入分配結構和社會相對收入不平等水平的影響結果見圖5—7和表7—9所示。

圖5 稅收政策對中性技術水平的影響

圖6 技術進步內生時稅收政策對資本收入份額的影響

圖7 技術進步內生時稅收政策對相對不平等水平的影響

表7 稅收政策對中性技術進步的影響

表8 技術進步內生約束下稅收政策對資本收入份額的影響

表9 技術進步內生約束下稅收政策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
數據顯示:
(1)表7數據顯示,在技術進步內生的情況下,資本和勞動稅率的提升都會增加中性技術進步的水平,不過兩種稅率對于中性技術進步的作用強度不同。同樣,從所得稅結構(0.1,0.1)出發,當勞動稅率增至0.3 時,中性技術進步由39.579增至55.999;同樣從(0.1,0.1)出發,資本稅率增至0.3時,中性技術進步僅為49.889。表7說明在任何所得稅結構上,勞動稅率對中性技術進步的作用都強于資本稅率,其原因為穩態時資本收入份額小于勞動收入份額,所以對勞動征稅的政府收益較大,同樣的政府的研發投入也會變多,所以中性技術進步對勞動稅率更加敏感。
(2)技術進步內生與外生的情況相比,兩種稅率變化對資本收入份額的作用方向相似但作用強度有明顯變化。當政府政策誘發技術創新時,勞動收入稅率對資本收入份額的作用被明顯弱化,而資本收入稅率仍然能降低資本收入份額,主要體現出兩個特點:一是資本收入稅率的作用強度遠大于上一種情況的結果。這是因為技術進步內生時,資本收入稅率提高會通過政府科研投入使資本增進型技術進步增強,在要素替代彈性小于1時技術進步越偏向于勞動,二者共同對資本收入份額產生負向影響,疊加作用強化了這種效果。如所得稅結構為(0.1,0.1)時,資本收入份額為0.325,而當所得稅結構為(0.3,0.1)時,資本收入份額迅速降至0.231,降幅高達29%。二是勞動收入稅率變化對資本收入稅率的影響有限。數據顯示,勞動收入稅率從0.1變化到0.3時,資本收入份額平均只下降9%,降幅小于資本稅率。這表明在技術進步內生環境下,資本收入份額的下降更多來自資本收入稅,政府可以通過稅收政策調整研發投入增加資本增進型技術創新,將有效減少資本收入份額。同時,值得關注的是通過稅收政策調整技術進步方向其效果明顯優于純稅收政策對收入分配的影響。
(3)在技術進步方向內生可變環境下提高勞動收入稅率將明顯有利于收入平等性。無論在何種資本收入稅率水平下,勞動收入稅率增加都將顯著縮小不平等水平,當勞動收入稅率從0.1提高到0.3 時,社會不平等程度平均下降了5.8%。同時,資本稅率的增加在不同勞動稅率水平上對不平等的作用方向不同,在勞動稅率為0.1時,資本稅率從0.1升至0.3使得不平等水平增加了0.9%,而在勞動稅率為0.3處,資本稅率由0.1 升至0.3 使得不平等水平下降了0.8%。原因可能是無論資本稅率還是勞動稅率,其直接作用都是降低收入不平等,但由于中性技術進步同時提高了資本和勞動的邊際生產效率,這使得由財富差距和勞動能力差距產生的不平等水平擴大了。由于勞動稅率對不平等的直接作用要大于資本稅率,所以勞動稅率對不平等的負向作用大于中性技術進步的作用。資本稅率的作用依賴于勞動稅率的水平,在較高的勞動稅率下,資本稅率的作用大于中性技術進步的作用,不平等水平縮小;而在勞動稅率較小時,資本稅率的作用小于中性技術進步的作用,不平等水平擴大。
假定政府科研投入比重τk和τl發生變化,由模型和前述分析可知,此時政策變化通過改變資本或勞動增進型技術進步方式而改變資本收入份額和社會相對收入不平等水平。這與單純模擬技術進步變化影響二者的情況類似,因而沒有單獨列出這一模擬結果。綜合上述數值模擬的結果可知,在要素替代彈性小于1時,資本增進型技術進步即為勞動偏向型,有助于降低資本的收入份額,而通過政府稅收政策調整研發投入增加資本增進型技術創新其效果明顯優于純稅收政策的作用,同時搭配勞動收入稅收政策,又能有效降低社會收入不平等,使我國的收入分配結構趨于平衡。
進一步用數值模擬方法研究何種稅收組合可以使不平等最小。前面模擬結果看出,提高資本或勞動稅率都可以有效降低不平等程度。但是,稅賦水平不可能沒有限制,若一直提高稅率,顯然,當政府對兩種要素收入全額征稅時,個體收入為0,不存在收入不平等。這種“最優”是以政府收入剝奪個體收入形式實現的,這顯然有悖于常理。所以此處在尋求社會不平等水平的最小值時,需要對稅賦整體水平做一限制。前述數據已計算得到我國2012年平均稅率為0.195 2,資本稅率為0.250 0,勞動稅率為0.154 7。為此,保持當期政府收入份額不變,由于在技術進步內生的環境下,θg完全取決于資本和勞動稅率,所以θg為固定常數也就得到了ηl關于ηk的如下方程:

進一步模擬勞動與資本稅率按(17)式所示的函數變化時,資本收入份額、中性技術進步和相對不平等水平的變化規律。其中ηk的變化范圍為其2012年取值的±30%,ηk∈(0.175,0.325)。

表10 適宜性稅收政策的模擬結果
表10數據顯示:當資本稅率不斷升高時,勞動稅率不斷下降。由于固定了當期政府收入份額,二者必然成反向變化,這與(17)所示的公式一致。中性技術進步與資本稅率反向變化,前述模擬驗證了勞動稅率對中性技術進步的影響更大,所以在資本稅率提高而勞動稅率降低的過程中,中性技術進步水平不斷下降。隨著資本稅率的提升,穩態資本收入份額下降,相對不平等水平不斷增加,這與前述模型的結論保持一致。其中,稅率直接作用和間接作用的方向都是負向。就強度而言,技術進步的作用強度要大于稅率的作用強度,稅率直接作用強度隨著資本稅率的增加而提升,中性技術進步的作用強度則隨著中性技術進步水平的降低而減小。穩態相對不平等水平在資本稅率增加的過程中不斷上升,其中中性技術進步的作用強度要強于稅率的作用強度。稅率直接作用強度呈現不斷增強的趨勢,而中性技術進步作用強度則與其水平值的變化方向相反。值得注意的是,若改變稅率,那么穩態政府收入份額也會隨著資本稅率的增加而減少。也就是說,若政府通過降低資本稅率同時提高勞動稅率以降低穩態的收入不平等水平,這種行為同時也能提升穩態時政府的收入份額。
四、基本結論
大量經驗研究關注非技術因素對于短期要素收入占比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響,并未重視不同類型技術進步對長期收入分配和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本文構建了包含技術進步方向和政府政策選擇的理論模型,在技術進步外生和內生兩種情況下討論了技術進步以及政府政策對長期收入分配以及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機制,利用我國1978—2012年宏觀數據,結合數值模擬方法,考察不同稅收強度下均衡收入分配和收入不平等的演化規律。結果顯示:(1)資本收入份額以及由個體收入的變異系數表示的社會不平等水平,在一定的稅率和技術水平下會趨于穩定。一般的,若政府收入份額較小,則外生的中性技術沖擊和資本偏向型技術沖擊均會降低資本收入份額,加劇社會不平等程度。(2)對資本和勞動兩種要素收入征稅對資本收入份額和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可分解為稅率直接作用與稅率間接作用。稅率直接作用體現在政府收入的變化導致研發投入的調整,影響技術水平繼而改變均衡狀態。其中稅率直接作用方向同樣依賴于政府收入份額,較小的政府收入份額使得兩種稅率與相對不平等水平呈反向變化。而稅率間接作用取決于研發成功率以及技術進步本身的作用強度。(3)在保持即期政府收入份額不變的前提下,降低資本稅率同時提高勞動稅率會提升資本收入份額,降低相對不平等水平,而且當經濟處于穩態時,這類政策也會使政府收入份額得到提升。
[1] Pareto V.Cours d'Economique Politique[M].Macmillan Press,London,1897(2).
[2] Caselli F,Ventura J.A Representative consumer theory of distribu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0(4):909-926.
[3] 王弟海,龔六堂.新古典模型中收入和財富分配持續不平等的動態演化[J].經濟學,2006,5(3):777-802.
[4] Acemoglu D.Why do new technologies complement skills?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and wage inequality[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8(4):1055-1089.
[5] Kiley M.The Supply of Skilled Labor and 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Progress[J].Economics Journal,1998(109):708-724.
[6] Galor O,Moav O.From Physical to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Inequality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4(71):1001-1026.
[7] 董直慶,蔡嘯,王林輝.技能溢價:基于技術進步方向的解釋[J].中國社會科學,2014(10):42-60.
[8] 王林輝,董直慶,劉宇清.勞動收入份額與技術進步偏向[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3):3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