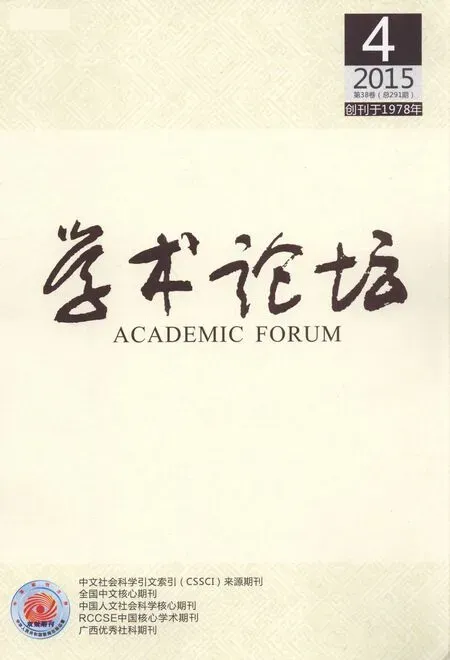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職業態度
傅 薇,李小魯
引言:“知其不可為而為之”①語出《論語·憲問》。子路宿于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現在多理解為明知道做一件事、實現一個目標有困難而仍要堅持去做。——傳教士的職業態度。對于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的關系,學術界一直以來有諸多的觀點和爭論,這些我們可以暫且存而不論。他們長期定居中國,從踏上這片土地開始,就面臨著諸多的困難——語言、經濟、文化以及隨著理性主義在世界范圍的上升而帶來的神職人員群體地位的下降,等等。這些都成為傳教士傳教布道工作中的困難和障礙。20世紀80年代,其事跡曾經被我們黨的領導同志用來教育干部的英格蘭傳教士柏格理,就是一個典型。19世紀晚期,基督教在中國西南遇到了來自于各個方面的抵抗和困阻。而柏格理等人卻通過創制和推廣苗文,開設教會學校,建立麻風病人院積極救治病人等方式,使其所在的石門坎地區成為20世紀初“西南苗區最高文化區”[1]。“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正可以成為傳教士們在職業態度上的鮮明寫照。傳道是人世間職業的一種,盡管宗教思想的宣講及其相關的工作實踐與當代馬克思主義思想政治教育是大不相同的兩樁事,但是從意識形態工作的角度來看,它們存在一定的內在聯系。因此,對于職業態度的思考,能夠為我國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一些借鑒和啟發。
一、對職業態度的認知
職業態度,是從事職業的人對于具體的職業在認同、選擇、堅持等方面的強烈的主觀傾向,作為一種內在的穩定的心理結構,它主要包括職業認同、職業情感、職業意志等三個方面。職業認同是指個體對職業的認識和評價;職業情感是指個體對職業的感情傾注和情感體驗;職業意志則是指個體對職業的忠誠和堅持。在職業態度中,最為主要的是職業意志。職業意志是穩定、持續、堅韌的精神動力,也是建立在職業認同基礎上的職業情感的升華。
職業態度與職業道德具有一定的聯系。職業道德是道德律令在具體的職業領域的體現。職業態度與職業道德都是事關職業的“形而上”的問題。既然它們都是“形而上”的,那么對于職業的具體的“形而下”就有著指導的作用。當職業者對自己所從事的職業具有積極的、正向的職業態度時,職業道德也會在此過程中自覺發揮作用。
職業態度與職業道德都是職業積極、健康發展的保障性因素,但二者也有著明顯的區別。首先,“普遍”與“特殊”。職業道德既然是抽象道德律令在職業領域的具體體現,那么職業道德中不僅包含對于特定行業中從事職業的人進行約束的道德規則,也包含對于人世間一切職業具有道德約束作用的規則。職業道德是通過成文或者不成文的方式對一個群體中的每個人進行規范和約束,因此在一定的意義上,它具有普遍性。而職業態度,是每個具體的人對待具體職業的主觀傾向。主體對于客體的認識并不是作為規則而存在的,作為個體的人對于具體的事物的認識和態度是千差萬別的,就如同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所說,世界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具有極大的特殊性。其次,“公”與“私”。職業道德是對于從事職業的人起道德約束作用的規則,所以它就具有了“法”的性質,更多地關涉公共領域的事。而職業態度,是從事職業的人對于職業的個人體驗。職業態度在職業領域發揮作用,主要是體現在特定的職業態度的指引下所取得的職業成就,而這則更多的是私人領域的事,也即個體存在的深層尺度。職業態度對于從事職業的人沒有約束和規勸的作用。最后,“外在”與“內化”。職業道德作為一種在職業領域的道德律令的具體化,是外在的力量對于人的精神世界的“立法”和約束。職業道德對于個體起作用,要有一個“內化”的過程,使其經由外在的“立法”轉化為自己對自己的立法,從道德他律轉進為道德自律。而職業態度本身就是內生的,是從事職業的人的主觀世界的一部分,它通過在人的精神世界的建構來對客觀世界進行建構。
由上所知,職業態度與職業道德有著極大的關聯,但也有著明顯的區別。在職業者的主觀見之于客觀的過程中,職業道德和職業態度在不同層面發揮著作用。
二、影響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職業態度的幾個因素
當代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政治教育是要為黨“舉什么旗幟,走什么道路,保持什么樣的精神狀態,朝著什么樣的目標繼續前進”的重大問題服務的,特別是其中的“保持什么樣的精神狀態”,直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職業態度。并且,積極的職業態度的養成對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走職業化、專業化、專家化發展道路具有基礎性的作用。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職業態度的影響因素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從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關系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職業認同。對于職業的認識、對于職業的選擇和對于職業的堅持,都涉及到職業認同的問題。對于客觀實在的認識和選擇,繞不過的話題便是人類理性。特別是在“祛魅”以后,“理性”的地位不斷上升,成為人們對于世界進行思考的一條必經之路。作為近代三大社會學家之一的馬克斯·韋伯,在探討人類理性時,將“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作為一組對立統一的概念提出來。工具理性就是把達到目的所采取的手段進行首要考慮、計算的態度。價值理性之“價值”是一定社會條件下的物與人的需要的一種關系,它寓于人的實踐活動的對象中。價值理性通過在動機層面上調動理想自我從而實現對人的行動的導向作用。我們的老祖宗說“君子不器”,又說“道器合一”,盡管前人已經對“道”和“器”作過諸多的解釋,但是我們也可以這樣認為,“道”指的就是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而“器”指的是工具、器物,以及由此而延伸出的方法、途徑和相關的思維方式。這正是可以和西方哲學社會科學語境下所提的 “價值 (理性)”、“工具(理性)”對應起來的。
古人所說的“道器合一”很有啟發意義。這種合一,不是簡單地做加法,而是在價值理性統攝下的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合而為一。就如同傳教士柏格理那樣,是在價值認識基礎上的自覺、堅韌和持續堅定的價值目標踐行。只要堅持這個前提,才能將目標與手段、應然與實然結合起來,在此基礎上,建立對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職業認同,認識到它的本質是對于精神世界的滲透、改造甚至是重建。在這種認同的基礎上,要有投身于此項工作的長久打算和吃苦的決心毅力,但是同時也要充分地依靠現實的條件,創造有利的條件,最大程度地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益。
(二)從 “神圣世界”與“世俗世界”的關系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職業情感。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上所反映的關于職業情感的問題,有可能是許多行業都存在的、具有普遍性的問題。在事實中把握職業情感, 要區分“敬畏”、“關愛”、“諂媚”的區別。對于理想的神圣世界,應該抱有“敬畏”以及與之相伴的“關愛”之情。但是,現在過分依附于“世俗世界”的諂媚之情銷蝕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應有的健康的職業情感。為什么入行者在開始認識和選擇這個職業的時候是帶著膚淺的、短視的眼光去審視的,是帶著功利之心去選擇的,在遇到困難就退縮而沒有堅持呢?為什么在受到一丁點兒困難或外在的誘惑時就選擇逃離甚至背叛呢?這是因為職業者對于自己所從事的這項職業持有諂媚之心,而缺乏敬畏、關愛之心。有的人可能會認為,沒有敬畏之心,正好說明了人類社會的進步,人為什么有宗教,或者為什么會迷信,是因為對未知世界有恐懼!人不再恐懼了,是人的認識能力極大發展的結果。但應該注意的是,人的恐懼與人的敬畏之心是兩回事。恐懼是被動的,而敬畏帶有主動的意思,“畏懼”是一部分,但更主要的是尊重。而真正的關愛與諂媚也是有著巨大差別的,真正的關愛是無條件的,甘于奉獻和犧牲的,而諂媚則是帶有極強的審時度勢的、功利性的阿諛逢迎。對于職業的敬畏、關愛之心,是作為主體的人,對于自己的尊重,對于所身處的社會中自己以外的其他人的敬愛和謙遜,也是對于整個世界中,人類以外的自然界的敬愛和謙遜。歷史不止一次地證明,當人類毫無來由地“大無畏”,甚至是無法無天的時候,也是人類遭到“報復”的開始。誠然,歷史的車輪不斷向前,科技以不可阻擋的趨勢發展,我們的認識手段和認識能力都空前地提高。但認識能力的提高不應該成為人類泯滅敬畏之心的理由,也不應該成為失卻關愛之心的借口。
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所提出的資本主義大發展與新教教義之間的相關性盡管也在后世備受爭議,但是其中揭示了從事職業的人對于職業的敬畏、關愛之心與獲得職業成就的關系,非常值得我們深入思考。從事職業的人對職業抱有敬畏之心,他們努力地不帶世俗雜念地投入到工作中,通過工作來回應上帝的“召喚”[2],而這種對于神圣世界的敬畏導致的其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勤勉同時也使得他們在世俗世界獲得了成功。
(三)從“信仰”和“信念”的關系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職業意志。從事一種職業,特別是從事一種比較艱難的職業,從事一種與人的精神世界、內心世界相關的工作,是需要信仰和信念的。信仰與信念,一字之差,道盡個中的差別與聯系。
信仰,其中的“仰”字,暗含了一種對于崇高的、遙遠的東西的探索、追尋、堅持,比如對某種主張、主義,某個人、某個事物或行為,是一種無條件接受和同意的心理狀況。而信念,是對所向往的東西具有實在意義的肯定。信仰和信念,都有一個“信”字,也就是說,無論信仰還是信念,都是以相信、信任為基礎,是主觀世界對客觀世界的肯定。信仰更多的是主體對精神對象性客體的信賴、認同和向往。信念更多的是主體自身追求的一種堅定的信任、堅持與執著,它的意志成分居多。因此,信仰有著比信念更強的社會性和集群性。信仰以信念為基礎,信仰本身也是信念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支配其他信念的最高信念。
信仰與信念在對于職業的忠誠上,互相依存,缺一不可。信仰,它有可能在主體尚未能以自己的能力來獲得正確認識的時候就已經初具規模。這一點在宗教信仰上就表現得尤為突出。因此,它有可能是脫離現實基礎的,甚至有可能是懸空的。那么,信仰要在人的實踐中發揮指揮棒的作用,或者是有可能發生動搖和困難的情況下發揮“支點”、“支撐”的作用,就有賴于它統攝下的信念。
就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言,最高、最大的信仰便是馬克思主義,但是在實際工作中,僅有信仰,缺乏信念,則信仰就難以落到實處。信念也是一層層推進的:一是要信任。就是堅信馬克思主義必勝,共產主義定會實現。在此前提下,要相信我們的人民特別是我們的青年是好的,是可以教育過來的,人的思想工作是可以出成效的。二是要堅持。任何理論與實踐都有一定的差距。理論也是在實踐中才能不斷地接近真理。在工作實踐中有所堅持,就要求在信任的前提下,哪怕工作實際與理論邏輯有出入,也要以一以貫之的勇氣和精神將工作進行下去。三是要堅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事,就如同天下所有之事,“其不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正確的態度是必須“總在能堅忍耐煩勞怨不避”,然后“乃能期于有成”。宗教的傳道者在市場化和職業化的條件下能虔誠布道,靠的就是信念與信仰結合從而達到對職業生存世俗化的超越。這種超越指向的是一種最堅定的、忠誠的職業態度。無論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隊伍這樣一個群體,還是從事此項職業的具體的個人,職業忠誠都是考核其職業態度的一個關鍵問題。對于職業的不忠誠,甚至 “背叛”是如何發生的呢?原因有很多,但最根本的是,某個人或者一群人,對于這個工作以及這個工作所承載的價值、理想發生質疑,不再相信依托這個職業可以實現自己一直以來的奮斗目標,甚至不相信這個職業可以滿足自己的基本生活需求。對于職業預期的信任感沒有了,信念沒有了,信仰就如同空中樓閣,瞬時間可以轟然垮塌。作為統攝的東西不存在了,因此也就沒有堅持了,對于原來所從事的職業的忠誠也就難以為繼。
三、優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職業態度的思考
黨中央一直以來都沒有放松過對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視,以及對于這支隊伍的關懷,中央8號、16號、59號文件從各個層面上已經體現出了這種重視和決心。培養人至始至終都要以全面素質、人文關懷為主旨,在這個基礎上選拔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才能成為能夠對抗職業倦怠的“合格職業人”。總的來說,應做到以下幾點:
(一)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供一個良好的成長環境和社會氛圍。國家應從制度層面上為所有人構建良好的成長環境和良性的社會流動機制。人事制度改革是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人事制度改革對于職業發展的影響是深遠的。就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言,相關的人事制度設計直接決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職業態度。制度的設計要以理性的眼光去看待作為職業的思想政治教育,處理好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關系。職業尊嚴和體面,是持續保障職業地位和專業精神的必要條件。當代思想政治教育顯得蒼白無力,實效性有限,這不是一個可以在教育領域內就可以完全解決的問題。但是如果說因為不能僅在教育領域內找辦法,就將其擱置起來,一“等”二“靠”也不可能將問題解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職業態度的關鍵是本人如何看待自己所從事的這個職業。這倒不是說要通過人事制度改革來使一項特定的職業獲取高到一個什么程度的地位以及相應的尊嚴,而是在該項制度的指揮棒下這地位和尊嚴與從事這職業的人在物質條件、精神需求和社會交往的主觀期待方面具有一定的匹配、契合程度。
(二)深入思考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轉進,構建當代中國思想政治教育的內生型構建,提高工作實效性。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職業態度與黨的要求還有一定的距離,它有時代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因為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有限所“倒逼”的。工作難見成效,更談不上長效,因此工作難以受到應有的重視,在各級黨委、政府都存在“兩張皮”的現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積極性受到打擊,必然影響到正確、積極的職業態度的樹立。因此,逐步實現外生型思想政治教育向內生型思想政治教育的轉進,是一項具有緊迫性的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隊伍在思考如何構建內生型思想政治教育時應主要解決這樣幾個問題: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對現實的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是當代社會政治的一部分,作為政治生活化的一個主要的路徑,如果脫離了與生活現實的結合,則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對歷史邏輯的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作為特定的社會現象,應該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眼光來對其進行審視,同時進行發生學的探討,從而掌握其規律性。再次,思想政治教育機制對利益平衡的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屬于上層建筑,不僅反映社會經濟基礎,而且對于經濟基礎有著反作用。因此,要注重對于具有不同利益的群體和個人進行平衡性的引導,把社會力量整合到符合國家整體利益的方向上來。最后,思想政治教育理論對于學術理性的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不僅是意識形態教育,還是科學理論的教育,是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統一體,要在教育的過程中遵循科學的規律,夯實學科基底[3]。
(三)正確認識當前中國社會的客觀現實,以崇高的信仰和堅定的信念引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樹立正確的職業態度,確保對于本職工作的堅守和忠誠。作為社會個體的人,其自我價值在于為信仰和信念獻身的過程中得到精神的永生。當前我國的改革正處在攻堅階段,難免會出現急功近利的現象,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敢于正視問題。首先,學會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自己,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澄清問題的根源。其次,正確認識個人理想,個人理想是人生的航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職業理想與工作實效性的提高是密不可分的,這就要求我們研究和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方法和新途徑,確保這項工作的科學性和成效。最后,正確認識職業。正確認識職業是建立在對個人的正確認知之上的。和一般的自我認知強調情感、體驗不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自我認知要密切結合職業要求和定位來開展。正是由于兼具思想性和政治性,它因此而與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相聯系。這也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有了使命感。
[1]趙文娟.清末民初基督教傳教士在西南民族地區的宣教活動——以循道公會傳教士柏格理為個案[J].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1).
[2]陳涯倩.召喚與職業:駁韋伯對基督教職業觀的理解——從克爾愷郭爾的基督教思想出發[J].現代哲學,2007,(1).
[3]李小魯.反思與重建: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內生型構建[J].學術研究,2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