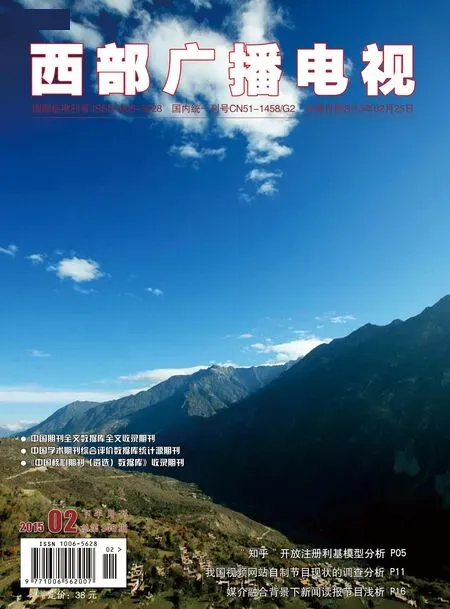《今日說法》新媒體創新的本質化探尋
摘 要:隨著新媒體的快速發展,國內電視節目逐漸吸收新媒體技術元素來打造全新的電視節目播出形式。電視節目創新便成為了電視節目實踐的一項系統工程。在復雜激烈的媒體競爭下,為了符合受眾的心理以達到更好的傳播效果便需要對節目形式進行改進。隨著傳統媒體的播出平臺受到新媒體的影響,自身不得去尋求更大的發展平臺,而要發展就需要創新。但究其原因為何要對對原來的電視節目進行創新,則需要探索電視創新的本質。它包括新媒體與電視融合背景、電視受眾的心理機制的變化、電視主體的創新性提高、社會語境背景下改革的動力等等。
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在互聯網的推動下,當今媒體已從報刊、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發展到網絡及其他新媒體。媒體是交流和傳播信息的工具,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新媒體,都離不開自身的傳播語言體系。新媒體的出現與發展,形成了新的媒體傳播格局,使傳媒業態尤其是電視行業發生了新的變化。互聯網的發展促進了新媒體在藝術領域的蔓延,它逐漸改變著電視藝術的傳播方式和受眾接收傳播的意識。新媒體的發展是以互聯網為依托的,自身具有較強的開放性、交互性特征。覆蓋范圍與傳播影響都不容小覷,因此它逐漸成為了發展勢頭猛烈的傳播技術載體。新媒體的發展與成熟雖然拓寬了中國社會的輿論空間,放大了電視發展的范圍。但是它卻極大地擠壓了傳統電視媒體的生存與發展空間。
電視節目的創新不僅需要有豐富多元的素材,還需要有較高的傳播平臺和節目系統,因此要對一檔播出已久的電視節目進行新的改造是一項復雜的系統任務。2013年《今日說法》節目推出了一檔全新的周播欄目《撒貝寧時間》。節目中新媒體的運用貫穿了節目的始終,虛擬結合的演播室、角色轉化的主持人以及特殊的敘述結構和推理方法都印證了這版新節目的強大創新力量。
1 新媒體與電視融合背景探究
電視節目必須加快自身改革的步伐。在不斷的探索與發展中在新媒體環境下找到中國電視節目的未來發展方向。新媒體的發展在近年來以雷霆萬鈞之勢席卷傳播領域,其中“三網融合”的勢頭最為猛烈。“三網融合”不僅是新媒體發展的重要依托,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構了傳統媒體格局。新媒體的發展必然為觀眾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收看方式與更加豐富的傳播內容,因此也會對中國電視行業的傳媒形態與收視習慣產生重要的影響。傳統電視媒體的改革與突破迫在眉睫。這是一個眾聲喧嘩和大眾狂歡的時代,話語權的設置變得越來越隨意,“把關人”的作用也隨之削弱,傳播速度快速提高,傳播路徑也變得越來越廣闊。隨著傳播方式的發展,受眾的接收方式不再依賴于傳統電視媒體的格局,渴望自由與隨意的呼聲越來越高。傳統電視媒體很難在傳播平臺上吸引更多的受眾,反而更將自身的局限與禁錮凸顯出來。因此就亟待建立新的創建體系。新媒體的發展以及新媒體藝術的介入與新媒體技術的介入都能使電視節目的質量與格調提升,因此新媒體環境下電視節目的發展也成為了一項重要的議題。
2 電視受眾審美機制的訴求
英國美學家、藝術批評家克萊夫·貝爾在《藝術》一書中,極其強調形式,貝爾認為一切審美方式的起點必須是對審美情感的親身感受。而貝爾“有意味的形式”卻恰恰符合了當代電視的審美需求——視覺的重要性。當代的電視受眾是一個龐大的概念,它是由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不同職業與不同文化水平的人組成的一個集體,這個集體表現出一種復雜性和多樣性。世界一體化進程使不同的文明、文化在不斷交融、碰撞、整合,這種社會環境的變化必然會影響人的審美理念。日常化的審美慢慢地不再能吸引觀眾的眼球,這就需要在電視節目的改版中融入陌生化的元素,讓觀眾能隨著節目的推進而一步步解開陌生的面紗。《今日說法》周播欄目《撒貝寧時間》的推出,正是契合了電視觀眾對法治節目的審美訴求。這也是央視綜合頻道系列創新項之一。電視節目受眾的心理狀態有兩種,一方面追求大幅度的熟悉與認同,另一方面又追求新穎和奇特。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大眾的審美與欣賞都趨于一種消費,不再需要用冗雜的思維去構建一種場景,也不需要過多地思考一些情節,觀眾需要的是一種直觀感受,視覺上需要的是一種刺激與真實。同時,在電視受眾日益分化的今天,不同受眾的要求表現出一種差異化和個性化的趨勢。傳統的法治節目中演播室的功能是敘事、討論、與觀眾互動,主持人的作用被隔離在案件偵破之外,大有隔岸觀火的味道。《撒貝寧時間》的演播室一改傳統演播室的單一實景或單一虛擬設計。在虛擬的演播室的左側安排部分實景,作為小撒的刑偵工作室。右側則通過電腦技術,再現出一個又一個的案發現場。既可以讓主持人從現實穿越時空進入案發現場尋找破案線索,也可以讓主持人從現場回到現實當中,在實景部分的“刑偵工作室”分析研究從“現場”帶回來的證據。因此為受眾打造一款個性電視節目產品貫穿在節目生產的整個環節。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電視產品也呈現出多元的形態,電視節目在升級開發的同時,必須要滿足觀眾的個性化需求。節目融合了大量的新媒體元素,是互聯網的支撐下新媒體與電視融合的絕佳案例。這就契合了受眾的審美品位與審美要求,在進行陌生化接受的同時又融合進了熟悉的生活場景,最主要的是節目改變了傳統的制作方式與傳播方式,新鮮感來襲,必然引起關注。
3 表現空間與新“視閾”的訴求
“場域”一詞見于布爾迪厄的場域理論與文化西行研究中,布爾迪厄認為:“每一個場域都是一個獨特的空間、一個獨特的圈層同樣也是一個具有不同規則的游戲圈,這種游戲圈使得藝術場和經濟場以及法律場具有完全不同的游戲方式。”若將“場域”的概念與范圍縮小到新媒體中。在新媒體快速發展的時代,藝術與技術越來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此時的場域自身具有了一種自主性,所有外部權利的滲入只有通過場域的獨特形式的特殊調解后才能間接地影響到行為者身上。新媒體能通過視覺、聽覺、觸覺等立體的傳達方式來促使欣賞者享受到更現代化的藝術,而這也吻合現代人類不斷提高的藝術欣賞水平要求。電視藝術也不例外,如果想在電視節目中達到完美的傳播效果,就必須要營造出一個小的“場”,也就是空間。《撒貝寧時間》就營造了一個“場”,它穿越了時空,使不同時間與空間之間的穿梭成為了可能,這是一種真實的再造與延伸,它超越了空間也超越了真實。因為節目中所營造的空間是流動的,是真實物質空間的虛擬再現,在技術元素的幫助下,它能夠移動這個“場”因此能在這個固定的演播室中,帶領觀眾走進不同的現場。
在每一期的節目中,主持人撒貝寧都擔任著不同的職務,主持人、現場記者、偵探、分析員、講解員等,多重身份的設置使節目更加具有吸引力。如2014年6月19日《火場疑云》這期節目,從節目開始的音樂設置、三維講解、虛擬現場的再現以及主持人在“現場”的分析,都造成了觀眾的“最熟悉的陌生化”,本不與自身相關,但又緊緊地吸引著受眾。與以往法制節目用同類題材MV代替現場不同的是,該節目用新媒體技術將現場還原,重新組合場景,使傳播效果達到最大化。此時的觀眾會凝神屏氣,似乎回到了最初的“儀式化”的場景,但與儀式化場景不同的是此時觀眾的欣賞是自由的,而這種儀式化也是觀眾自身營造出來的。電視觀眾需要引導,而在新媒體技術的發展背景下,對觀眾的引導不再只是主持人在主播臺去實現,而是需要主持人帶領觀眾走進所講述的事件中去引導,撒貝寧在節目中既擔任了主持人的角色也擔任了“偵探”的角色。這檔節目最大的亮點在于新媒體的運用,虛擬演播室與真實演播室的交互、主持人撒貝寧身份的置換,都能將節目的始末形象化的娓娓道來,給觀眾造成一種現場感與真實感。面對這在場的缺席,正迎合了電視節目觀眾的審美趣味,既在觀眾的審美經驗之中,又能吸引觀眾,達到了一種熟悉的陌生化的高度。比如節目中的兇案現場、車禍現場、溺水現場等不同的案發現場都是通過新媒體技術還原,成為了真實現場的“鏡像”。
4 市場語境下改革動力的訴求
市場需求的動力是電視節目創新的一個支撐點,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與變化,必然存在競爭后的洗牌與資源的重新配置,更大的動力是一種求得生存與發展的動力,是一種需求與競爭的動力。競爭的不斷加劇使電視節目創新的成本和風險都有所提高,但是面對電視傳媒的同行競爭,傳媒業的同業競爭就必須要做出大膽的改革和創新。世界上引領電視技術創新的主要是美國、日本和西歐少數國家。就中國大多數電視臺而言,幾乎沒有技術創新,只有技術設備的更新,甚至比西方國家電視媒體的技術更新速度還快。對中國大多數電視臺來說,除了宣傳制度,幾乎所有的管理制度都是移植而來,少有創新。在打造出“差異與個性”相統一的節目之后在傳媒領域占領高地。社會問題的多樣化與法治社會存在的癥結也是這檔節目創新的現實支點與動力。社會問題的發生往往會通過電視呈現在屏幕上,因此也為這檔電視節目的制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創新的時機。各種問題一經披露便會引起社會的反響與關注。在這樣的現實情況下,電視創作主體融合進新媒體技術與新媒體藝術,使得電視節目的制作更加真實可觀。調整之后,節目在社會價值的體現與重構方面起到了更強大的引導作用。新媒體是科技發展的產物,它賦予了新媒體藝術新的活力,并催生了藝術發展的革命。技術引領的創新必須受經濟實力和科研實力的支配。競爭壓力催生了兩種創新的表現:一種是分析現狀主動創新,另一種是面對壓力的被動創新。很顯然《今日說法》這檔節目是主動創新,力求在電視節目尤其是法制節目中占領新媒體下的科技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