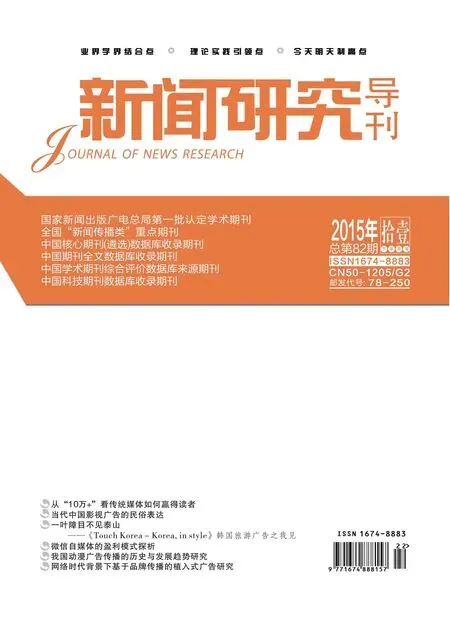正確對待“責任”
——現代媒體人眼中的責任意識
張文龍
(長春廣播電視臺,吉林 長春 130061)
正確對待“責任”
——現代媒體人眼中的責任意識
張文龍
(長春廣播電視臺,吉林 長春 130061)
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以及社會政策、輿論環境的變化,媒體人對于社會責任的認知以及自身責任的界定正在悄然發生著變化。而這種變化對媒體工作的開展以及社會責任的承擔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責任;雙重屬性;輿論監督
一、“責任”一詞的定義與發展
對于“責任”一詞的解讀,按照新華字典的解釋,分為兩層意思:一是分內應做的事,如教育下一代是父母與教師的共同責任。二是沒做好分內事而應承擔的過失,如倉庫物品丟失管理員要承擔責任。在當前的社會環境和輿論環境下,責任問題已經成為面對突發事件以及意外事故時人們首先關注的問題。由此衍生開來,人們在做事之前,首先要考慮的就是責任的劃分。雖然這樣的做法有助于人們提高自覺意識,做好分內之事,不逾矩,不越界,但同樣,如此思維容易切斷事物或人之間的聯系。俗語說,“只管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說的雖然是一種極端個人主義的現象,但實質上也是對過度關注責任問題的一種擔憂。對于責任問題,我們只有既分清了第二層次——對過失的劃分問題,也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第一層含義——分內應做之事上,才能真正把“責任”變成做事的動力,而不是像眼下的社會這樣,人人談責任而色變。
二、對責任理解的偏差,會影響政策的執行與工作的開展
作為一名媒體工作者,接觸的人和事涉及社會的方方面面,但無論是哪一領域的問題,無不存在著對責任的認識問題。例如,無證養老院的問題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由于我國人口眾多,長期以來政府都把計劃生育工作作為一項基本國策來執行。這項政策雖然緩解了我國的人口壓力,但同時也在客觀上造成了目前的養老難題。老年人口的增長速度超過青年人的增長比例。根據我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為1.78億人,占人口總數的13.26%。而從長春市的情況來看,60歲以上人口所占的比例已經超過了16%。目前中國家庭趨于核心化和小型化,每個家庭平均僅有3.1人。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中國的老齡化進程,與城市化、工業化以及經濟發展程度是不同步的,社會物質財富積累和精神文明程度、養老服務體系、社保水平還遠遠沒有準備好,即“未富先老”。在此背景下,我國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已然受到了沖擊,即一對年輕夫婦沒有同時承擔雙方四個老人外加一個孩子的撫養能力,社會化養老勢在必行。而從目前來看,養老院這一主要的社會化養老模式正在受困于“責任”劃分這一難題,而處在不健康發展的路上。
由于顧客群體的特殊性,養老院的運行風險是比較大的,食品衛生問題、防火問題、醫療問題等等,這些都涉及相關管理部門的責任劃分。而從目前來看,正是由于片面的責任意識,導致了目前大量的養老院處于無證運行狀態。從調查中記者走訪的無證養老院來看,它們辦不下來證照的原因主要就是消防不達標。作為監管部門,對這類弱勢人群密集場所,最關注的就是安全問題,因為如果安全出了問題,相關部門要承擔責任。所以在制定準入門檻時,監管部門最想達到的效果就是萬無一失。這樣一來,就造成了養老院建造成本及維護成本的直線上升,而目前,選擇養老院養老的老人們大多是生活困難的群體,他們的收入只能保證自身的基本生活需求,這也就導致了眾多小型養老院處于微利運行狀態。而面對這種現實情況,相關部門往往缺乏主動作為意識,有意無意地忽略掉責任的第一層含義,即做好分內之事,只會關注出現意外時的責任劃分問題。一紙規定,一定了之。對于相關部門的標準設定而言,是從消除自身責任出發,還是從百姓的實際情況出發,決定了這個標準能夠有多少機構達到。如果是為了擺脫責任,自然是標準設定越高越好。不達標,就發整改通知,整改不合格,就取締,取締有實際困難的,就默認帶病運行。這樣的一個循環讓標準失去了實際意義,能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在發生意外時撇清責任。
除了養老之外,醫患糾紛、教育糾紛、學校場館開放等等問題都在責任這一問題上打上了一個死結。但此時人們所談論的責任并非責任真正的、全面的含義。當病人送到醫院,出現意外,可能有醫院的責任,但全力地救治,更是醫院的“責任”;患有疾病或者存在某些問題的孩子來到學校,受了意外傷害,可能是學校的責任,但全心全意、想方設法地教育好這個孩子,照顧好這個孩子,同樣是學校的“責任”;學校場館開放,出現了打架、器材損壞等情況,學校會覺得責任難以確定,但利用現有設施,為周圍百姓服務,也是學校應負的“責任”。做好分內之事與承擔過失,二者相輔相成,同為“責任”的組成部分,不可片面強調。
三、全面理解責任問題,實現雙重屬性的有機統一
做好分內之事,首先要搞清楚何為首要職責。當醫院首先關注醫療責任而不是病人的治療,當學校首先關注安全問題而不是孩子的教育,當管理部門首先關注自身的規定而不是被管理部門的實際情況,那么在做事的過程中就必然走向僵化。這樣的說法類似于法律上我們所講的實質正義與程序正義,程序正義的缺失,必然會導致實質正義的受損,但從長遠來看,程序正義恰恰是為了更好地實現實質正義。如果對任何事情的判斷首先的出發點都是程序正義而非實質正義,那么長此以往,所謂的程序正義必將成為實質正義實現的絆腳石。只有在實踐的過程中,時刻反思程序在實質正義的實現中所起的作用,不斷地修正、發展,才能讓二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維護真正的法律尊嚴。
當然,這樣的比喻和劃分并不是把責任的兩層含義對立起來,而是說對于首要關注點的確立,將決定我們在面對一件事時會采取何種態度、何種做法。從媒體來看,同樣面臨著責任難題。輿論監督是媒體的天然屬性,但如何做好監督則并不簡單。若只強調責任的第二重屬性,即沒做好分內之事而應承擔的過失,那么無疑監督就成了一件高風險的事,尺度的把握、輿論的引導,這些不宜掌控的方面讓監督容易變味,這樣看來,似乎不做就能規避風險。但反過來,從責任的第一重屬性來看,輿論監督恰恰是媒體的分內之事,如果不做,更是失職,應承擔更大的責任。只有當一件事不得不做,又必須做好時,才能迫使、推動從業者不斷提升業務能力以及掌控能力,把這件事真正做好。
[1] 周勇.電視新聞編輯教程(第二版)[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2] 潘知常,林瑋.大眾傳媒與大眾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G206
A
1674-8883(2015)22-006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