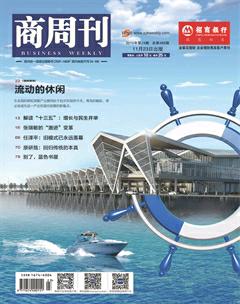苗煒:夜里想了千般路
我最初的焦慮來自年幼時讀過的一篇文章,在一本略微破舊的《燕山夜話》中,我看到那篇文章,題目叫《生命的三分之一》,大概意思是說一天有24個小時,人們要睡8個小時,生命的三分之一就在夢鄉中度過,這是生命中最大的浪費,一個積極向上的人應該在夜里讀書。那時候我剛具有“自我提升”的意識,看課外書,學下象棋,讀了這文章,忽然認識到,每晚睡八九個小時外加午睡,生命的一小半就浪費掉了。那時候人們普遍睡得早,晚上8點,收音機里是“各地人民廣播電臺聯播節目”,半小時節目過后,人們就關門閉戶洗洗睡了。那時我并沒有什么“夜讀”的經歷,只有如死亡一般沉重的睡意,夜里極安靜,鬧春的貓是最大的噪音,也沒有光亮,家家戶戶都黑洞洞的。我肯定做過夢,夢里偶爾會有杜甫的詩句飄過,我爹要求我把“三吏三別”全背下來,我只能背下《石壕吏》,盼著夜里能把剩下的篇章背會。應該有不少人設想過“睡學”——睡著覺,躺著就把外語學會了。
最近我在“萬古”雜志上看到一篇文章,題為《夜校》,該文作者Kenneth Miller,孩提時學法語,年輕時在墨西哥學西班牙語,他有一個機會去意大利,幻想著睡夢中聽聽錄音,就把意大利語學會了。文章說,百余年來,科學家都認為,睡中學習在生理上是不可能的,但最近的研究結果表明,睡覺興許真地能用來吸收知識。如今世界這么亂,信息這么多,白天腦子忙不過來,夜晚大腦處于“離線”狀態,要是睡覺時,我們的大腦也“在線”,那會怎么樣?
這篇《夜校》介紹了一系列科學試驗,而作者的擔心是,如果我們能控制自己的睡眠,把睡眠用來自我提升,那我們失去的是什么呢?在這個混亂而忙碌的世界中,良好的睡眠是最可靠的安慰,我們真地需要把這生命的三分之一用來讀書嗎?
有一個笑話,說小明第一天上學,放學回家后,媽媽問他:“小明,今天在學校過得怎么樣?”小明回答說:“還不錯,就是學的不夠多,明天還得去。”這個笑話的笑點在于,小明還不知道,他要學的東西非常之多,明天要去,此后千百個明天還要去。從讀到《生命的三分之一》,到讀到《夜校》,30多年過去了,我養成了夜讀的習慣,不過,讀的時間越來越短,拿起一本書看幾頁就昏沉沉要睡去。有許多夜晚非常焦慮,為白天的工作焦慮,為睡不好覺焦慮,不為什么事就平白無故地焦慮。從夜晚的陽臺望出去,街上燈火通明,遠處的高樓上,霓虹燈和大屏幕閃爍,深夜的電視里有本地的娛樂節目和英國的足球賽,手機里有專供夜宵的app,我們可以向夜晚借用很多時間,不睡覺似乎象征著“不老”和“不死”。
有數據說,20世紀初,美國人的平均睡眠時間是10個小時,上一代人的平均睡眠時間是8小時,今天的美國成年人,平均只睡6.5個小時。我不知道咱們這里的統計數字,但我隱隱覺得,在一種極為普遍的認知里,睡得少,精神抖擻,是成功者的標志,彼得大帝、拿破侖只睡三五個小時,喬布斯夜里會冥想,那是最具創造力的時刻。一方面,工作侵占生活,生活侵占睡覺,我們渴望睡覺;另一方面,夜晚樂趣多多,沒有夜晚的獨處,幾等于喪失自我,我們不想睡覺。在這個想睡和不想睡的纏斗中,我們又晚睡了一個小時。美國學者喬納森·克拉里著有一本《24/7》,這個符號是一部分人的工作模式,克拉里說,我們生命中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睡夢中度過的,這讓我們得以從欲望的泥沼中解脫出來。這是紛繁思緒中的一次豁免,一次釋放。“白天我們攝入的東西會在睡覺時代謝掉,睡眠還可以排泄把人淹沒的負面情緒:焦慮、恐懼、懷疑、覬覦、朝不保夕的憂慮或一夜暴富的妄想。”他說,睡覺是對抗全球化資本主義的革命行動。
周五晚上,我8:30到家,吃了飯,買了一張晚上10:20的電影票,去看007。一點到家,回工作郵件。凌晨1:45,上床睡覺。我不想在睡夢中學習或提升自我,只希望能睡到7:45,其間6個小時沒有夢,沒有記憶重播,似乎能從現實世界中逃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