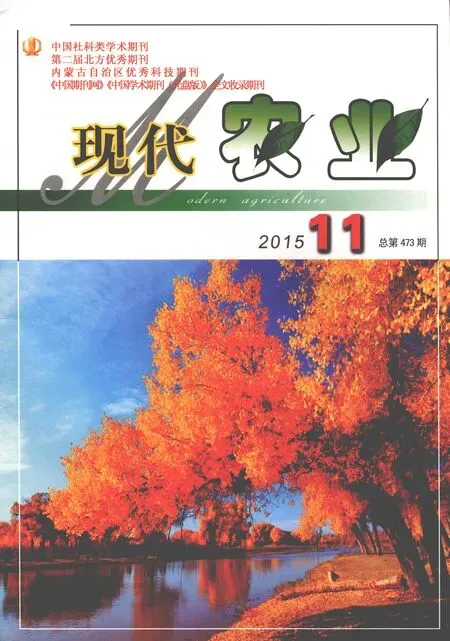農(nóng)村學前教育供給中政府職能的經(jīng)濟學分析
曾婭琴 嚴均平
重慶三峽學院公共管理學院
政府職能的缺失被認為是當前我國公共服務領域出現(xiàn)供需矛盾的直接原因,尤其是在農(nóng)村,政府作為公共服務供給主體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發(fā)揮,這導致農(nóng)村公共服務長期供給不足。作為公共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農(nóng)村學前教育的供給已無法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需求。2011 年《國務院關于當前發(fā)展學前教育的若干意見》出臺后,各地政府紛紛發(fā)布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皆提出將加大對農(nóng)村學前教育的投入。 在學前教育大發(fā)展的背景下,我們有必要厘清政府在農(nóng)村學前教育供給中的職能邊界以及履行職能的途徑和方式, 這對于完善農(nóng)村學前教育服務體系,實現(xiàn)城鄉(xiāng)公共教育服務的統(tǒng)籌發(fā)展有著現(xiàn)實的意義。
一、農(nóng)村學前教育供給面臨的市場失靈
著名經(jīng)濟學家斯蒂格利茨認為,教育并不是純公共物品, 因為多一個小孩的教育邊際成本遠遠超過零,而且在技術上,為教育服務而向私人收費沒有任何困難。[1]因此學前教育是可以通過市場來供給的,然而學前教育市場上存在著一些可能導致市場供給失敗的因素,這為政府的干預提供了合理性。
1.學前教育具有正外部性
通常人們認為學前教育是一項公益事業(yè),用經(jīng)濟學的術語來說,便是學前教育存在著正外部性,不僅對兒童自身的發(fā)展及其家庭帶來益處,而且具有普遍的社會效益, 這一點已經(jīng)得到諸多研究的證明。Verry 和Donald(1992)認為學前教育能夠支持婦女就業(yè),提高工作能力,有利于減少兒童母親對家庭的經(jīng)濟依賴,提高經(jīng)濟獨立能力,追求性別平等。[2]有關佩里方案的追蹤研究表明,學前教育給社會帶來的收益遠大于給私人帶來的收益,學前教育投資個人的回報率大概是4.17%, 而社會的回報率則高達12.9%,其中社會回報率的88%源于犯罪的減少、4%源于教育開支的減少、7%源于收入稅的增加、1%源于社會福利開支的減少。[3]可見,學前教育是典型的具有正外部性的服務。
正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學前教育的一部分收益被第三者或整個社會所獲得, 卻沒有支付相應的成本,扭曲了市場主體的成本與收益的關系。學前教育的私人邊際收益小于邊際成本,會導致消費者對學前教育的投入缺乏動力, 貧困家庭甚至會放棄接受學前教育,從而造成兒童受教育機會的不公平。
2.學前教育市場面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
信息不對稱是指的交易當中各人所擁有的信息不同。當消費者與生產(chǎn)者在產(chǎn)品和服務的質(zhì)量上存在著明顯的信息不對稱時,消費者難以準確判斷廠商所提供的產(chǎn)品或服務是否達到了承諾的標準,這就會導致市場機制無法有效地發(fā)揮作用。
學前教育市場便存在著明顯的信息不對稱。 首先,家長在兒童入園之前,往往難以獲得完備的關于學前教育服務的成本與質(zhì)量的信息,只能在兒童接受學前教育服務的過程中逐漸地感受幼兒園提供的服務的質(zhì)量。 其次,學前教育具有消費者和支付者分離的特征,是一種典型的代際轉(zhuǎn)移支付,即父母替子女支付教育費用,而兒童由于認知能力有限,缺乏對其直接享受的學前教育服務質(zhì)量的評價能力。 再次,由于缺乏客觀的質(zhì)量評價標準使得家長也難以對學前教育的質(zhì)量做出準確的評價,學前教育不同于中小學教育,不可以通過標準化的試卷在一定程度上對教學效果進行評價,使得人們對它的評價產(chǎn)生困難,因此人們常常選擇其他一些信息來代替對教育質(zhì)量的評價,例如幼兒園的環(huán)境建設和硬件設施。
可見,在學前教育市場上,公眾處于信息劣勢方。追逐私利的幼兒園完全可以在虛假宣傳的背后通過聘請低成本的教育和保育人員提供劣質(zhì)的服務從而獲取高額的利潤。尤其對于創(chuàng)辦歷史不長的民辦幼兒園而言, 消費者無法及時全面地了解其服務品質(zhì),將不利于家長做出理想的選擇。因此學前教育市場的運行需要由政府出面進行管制,采取措施削減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否則公眾的利益和行業(yè)的發(fā)展就會受到損害。
3.市場運行出現(xiàn)的分配不公
市場本身是以效率為歧視標準的競爭,它并不關心結果是否公平。完全由市場機制來分配學前教育資源,會導致只有能支付得起幼兒園費用的家庭才能享受學前教育,而貧困兒童等弱勢群體則會被排斥在幼兒園的大門之外。然而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是人們不懈努力的目標, 教育正是實現(xiàn)社會公平的重要途徑,學前教育有利于弱勢群體的兒童更好地融入小學,對于兒童以后教育成就的獲得有著重要的作用。 OECD的教育測量(PISA)研究表明兒童學業(yè)成就的落后在一定程度上與家庭貧困有關,兒童早期的貧困會阻礙基礎技能的獲得,對兒童的人生造成嚴重的影響。 對于弱勢群體的兒童而言,在早期可能難以找到成功的榜樣,缺乏學習的基本技能和動力,例如概念和語言的掌握、交流的自信、自我表達等等。可見學前教育的公平與否是教育公平的基石和起點,政府應當對市場運行的結果進行適當?shù)母深A,保證低收入家庭的兒童在教育成就方面不至于落后太多。
二、政府在學前教育供給中的職能分析
上述種種學前教育的市場失靈,需要政府以政權組織者的身份執(zhí)行國家的社會管理職能,避免因?qū)W前教育的市場缺陷而出現(xiàn)不能有效供給。政府通常采取以下措施進行干預。
1.財政支持學前教育
通常而言政府主要通過財政補貼來解決正外部性帶來的市場失靈問題。 政府補貼的途徑一般有兩種,一是補貼家庭,例如英國從1996 年開始試行學前教育券制度, 對所有4~5 歲的幼兒給予每人每年1000 英鎊的補助; 在美國家庭用于兒童照顧的費用可以獲得稅費抵扣。 二是補貼學前教育機構,美國幼兒園只要通過了全美學前教育協(xié)會(NAEYC)的質(zhì)量認證, 不論公立還是私立都可以獲得政府的補貼。2005 年,OECD 國家公共教育經(jīng)費中, 平均有15.3%用于資助私人部門提供的教育, 其中8.3%用于直接資助私立教育機構,7%則是通過資助學生的方式間接資助私立教育[4]。
2.監(jiān)控學前教育市場的服務質(zhì)量
學前教育正外部性的發(fā)揮有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即幼兒園提供的學前教育必須達到一定程度的質(zhì)量標準,換句話說學前教育的公益性只能通過評估這種教育是否達到應有的教育標準來衡量[5]。 政府應該承擔起信息生產(chǎn)和提供的職責,建立有效的信息披露體系,改善市場的信息結構。 例如OECD 致力于建立兒童學前教育和保育的數(shù)據(jù)系統(tǒng),監(jiān)控各種類型的學前教育服務,收集的數(shù)據(jù)包括生師比、學前教育和保育的支出等,并試圖通過制定一些兒童成就的目標來評估學前教育的效果。美國嘗試開發(fā)成本分析模塊使公眾能夠及時了解教育機構的成本信息,從而做出正確的選擇。各國政府都在努力地通過各種方式增加學前教育市場上的信息供給,使家庭能夠獲得更多的關于學前教育成本和質(zhì)量的信息,以便在信息充分的情況下做出正確的選擇。
3.為貧困兒童提供免費的學前教育
為貧困兒童提供學前教育具有明顯的補償作用,為了促進社會公平,各個國家都在針對輟學兒童和不具備基本技能的成人補償教育干預上花費不菲,積極支持貧困兒童接受學前教育成為政府義不容辭的職責。許多國家都專門開設了針對這類群體的學前教育項目,例如英國的“確保開端”項目,是英國政府為改善處境不利地區(qū)兒童的生活環(huán)境、消除貧困和預防社會排斥而采取的行動。參與該計劃的兒童可享受每周15 小時的免費學前教育, 以及醫(yī)療保健和家庭支持等服務。 類似的還有美國的“提前開端”(Head Start)項目,通過向處境不利的兒童及其家庭提供免費的教育、健康、營養(yǎng)和社會服務,為貧困兒童的入學做好準備,縮小其與同齡兒童之間的差距,以實現(xiàn)政府的反貧困宣言。
三、我國政府在履行農(nóng)村學前教育職能中面臨的問題及對策
在我國農(nóng)村學前教育服務的是處于相對貧困中的農(nóng)村兒童。 與城市兒童相比,農(nóng)村兒童處于更加不利的境地中:他們的家庭收入不高,對教育服務的支付能力相對不足;家長文化水平較低,缺乏科學的養(yǎng)育知識。對于中西部農(nóng)村地區(qū)大量存在的留守兒童而言,由于缺少父母關愛和適宜的教育環(huán)境,使得他們更可能在將來的生活和學習中面臨失敗。因此農(nóng)村兒童在發(fā)展的初期便處于劣勢地位,為農(nóng)村兒童提供學前教育具有明顯的補償作用,政府應當義不容辭地承擔起農(nóng)村兒童的學前教育。目前我國政府正著手將學前教育列入財政預算, 加大對農(nóng)村學前教育的投入,但是政府在履行農(nóng)村學前教育職能的過程中仍存在以下一些問題。
1.供給模式單一導致公平缺失
當前各地政府履行農(nóng)村學前教育職能的方式尚未突破通過建設鄉(xiāng)鎮(zhèn)中心幼兒園、中心校附設園來提供學前教育服務的制度設計。然而不同于城市人口居住集中的特點,農(nóng)村人口分布較為松散,而由于年齡的原因,兒童不可能到很遠的地方去上幼兒園,在這種情況下鄉(xiāng)鎮(zhèn)中心幼兒園能夠發(fā)揮的輻射作用有限,這導致只有居住在鄉(xiāng)鎮(zhèn)以上的兒童能夠有機會進入公辦幼兒園,而鄉(xiāng)鎮(zhèn)以下的兒童則只能進入民辦幼兒園(班),出現(xiàn)了公共資源分配上的不公平。 事實上只要達到質(zhì)量標準,社會也能從民辦園提供的學前教育服務中獲益,因此民辦園或進入民辦園的兒童也理應獲得政府的補貼以矯正外部性問題“確保開端”和“提前開端”也接受營利或非營利組織的申請,通過競爭性的程序,成為項目的代理機構,從而獲得政府的補貼。因此在農(nóng)村地區(qū)為了實現(xiàn)公共教育資源的公平分配,政府可以考慮通過學前教育券或者機構補貼的方式來多渠道地履行學前教育的供給職能。這一方面可以拓展現(xiàn)有機構的服務范圍,獲得規(guī)模效益;另一方面政府的補貼也有利于民辦幼兒園緩解資金壓力,改善辦園條件,激勵民辦園提供達到質(zhì)量標準的學前教育服務。
2.對農(nóng)村學前教育市場服務質(zhì)量的監(jiān)控不足
多年以來,我國政府對農(nóng)村學前教育市場的監(jiān)控以“入口”監(jiān)控為主,制定了較為嚴格的進入標準,而對服務過程的監(jiān)控相對不足,這體現(xiàn)在以下兩方面。
第一,服務標準的缺乏。 在存在信息不對稱的市場上,服務標準的供給是政府履行市場監(jiān)管職責的重要方式,也是監(jiān)控服務績效的一個重要尺標。 學前教育服務內(nèi)容的核心便是課程的設置。 早在2001 年我國教育部門就頒布了《幼兒園教育指導綱要(試行)》,將幼兒園的教育內(nèi)容劃分為健康、語言、社會、科學、藝術五個領域,但由于缺乏具體的評價標準和監(jiān)督手段,許多農(nóng)村幼兒園的課程設置仍然十分隨意,甚至為了迎合農(nóng)村家長的需求而片面地注重兒童認知能力的發(fā)展忽視情緒和社會性的培養(yǎng),出現(xiàn)"小學化"傾向,不利于兒童的全面發(fā)展。 政府亟需對農(nóng)村學前教育的服務內(nèi)容進行規(guī)范。 值得注意的是,2006 年聯(lián)合國兒童基金會曾對我國9 個貧困縣的3514 名0~6 歲兒童的發(fā)展狀況進行了基線調(diào)研,發(fā)現(xiàn)項目縣兒童輕度和重度營養(yǎng)不良的比例非常高。兒童的發(fā)育不良不僅與這些地區(qū)的貧困有關,更和這些地區(qū)家長缺乏兒童養(yǎng)育知識有關。[6]利用宣傳、講座的方式增加家長養(yǎng)育兒童的知識, 改善家長教育兒童的態(tài)度和方法,應當成為獲得財政資金資助的機構必須履行的公共職責。
第二,信息供給的不足。 目前民眾主要通過幼兒園的級別來判斷其服務質(zhì)量。幼兒園等級評估是由教育行政部門根據(jù)一定的評估標準對幼兒園進行檢查、評估、定級,對符合標準的幼兒園頒發(fā)等級證書。 然而,僅僅是等級制度并不能告訴民眾,幼兒園在哪些方面需要改進。 同時由于評估標準的城市傾向,鄉(xiāng)鎮(zhèn)幼兒園很難達到最低標準,對于沒有等級的幼兒園農(nóng)村居民也無從得知其服務在哪些方面尚未達到標準,從而無法獲得做出適當選擇的足夠信息。 政府應當將幼兒園等級評估以及每年年審的內(nèi)容等具體信息公開提供給民眾,或者通過信息公示等制度建設督促幼兒園自動公開其辦學成本、 辦學質(zhì)量等相關信息,使幼兒園的收費與其提供的服務質(zhì)量相符,才能保證市場機制的正常運行。
總之,農(nóng)村學前教育因其補償性的特征,其供給是政府應當履行的職責。 當政府意識到這種責任,往往容易通過加大投入, 建設機構的方式來履行職責。然而在市場經(jīng)濟的條件下,政府還應當學會與市場共處,通過發(fā)放學前教育券或機構補貼,推行基準化服務,加大質(zhì)量信息的供給等方式,最終實現(xiàn)農(nóng)村公共學前教育資源的公平分配與農(nóng)村學前教育供給體系的健康運行。
[1]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公共部門經(jīng)濟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359.
[2]Gordon Cleveland, Michael Krashinsky. Financing ECEC Services in OECD Countries[EB/OL].http://www.oecd.org/edu/earlychildhood,2003-1-30.
[3]崔世泉,袁連生,田志磊.政府在學前教育發(fā)展中的作用[J].學前教育研究,2011(5):3-8.
[4]陶西平,王佐書. 中國民辦教育發(fā)展報告(2003-2009)[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384 頁.[5]陳桂生. 中國民辦教育問題[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1 年,第167 頁.
[6]OECD . Starting Strong II-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R].2006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