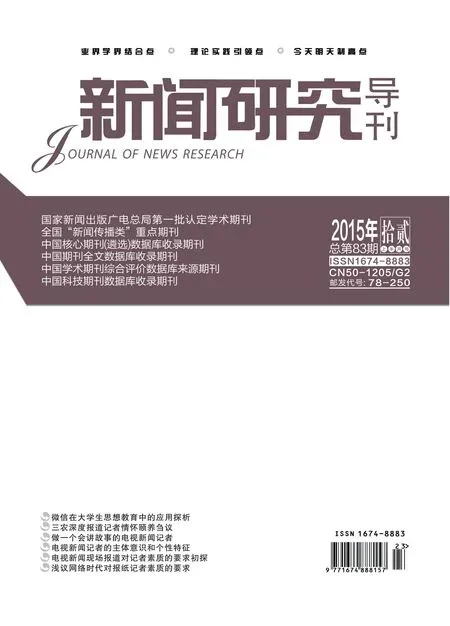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眾傳媒發(fā)展特點及反思
沈 樓
(浙江工商大學 國際教育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 )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眾傳媒發(fā)展特點及反思
沈 樓
(浙江工商大學 國際教育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 )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媒體的蓬勃發(fā)展發(fā)展也在某種程度上解構了改革開放之前以及初期整個社會所共有的價值共同體,使得一部分普通老百姓在面對各種渠道來源的媒介信息時失去了自我。通過梳理并分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眾傳媒的發(fā)展特點,可以看出加強媒介素養(yǎng)教育,健全非政府組織,促進多元文化與傳統(tǒng)文化的融合對于我國大眾傳媒的未來發(fā)展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改革開放;大眾傳媒;媒介素養(yǎng)
一、我國大眾傳媒的發(fā)展背景
自改革開放以來以及90年代互聯(lián)網(wǎng)在中國城市的大規(guī)模普及,各種各樣的媒介信息開始呈現(xiàn)爆發(fā)式的大幅度增長。根據(jù)歷年的全國國民閱讀調查報告所提供的數(shù)據(jù)顯示,“1999年第一次全民閱讀普查時我國國民上網(wǎng)率僅有3.7%,電腦以及互聯(lián)網(wǎng)在當時還不能被大眾所熟悉和使用,網(wǎng)上閱讀就更為鮮見。2001年,網(wǎng)絡閱讀率發(fā)展為7.5%,2003年該數(shù)字為18.4%,2005年為27.8%,2007年為44.9%,2008年為36.8%,2009年為41.0%。2008年,除了網(wǎng)絡閱讀之外,手機閱讀、手持式閱讀器閱讀等數(shù)字媒介閱讀也開始普及,成年人各類數(shù)字媒介閱讀率為24.5%。2009年,我國18~70周歲國民中接觸過數(shù)字化閱讀方式的國民比例達24.6%。而在最新的第十次全民月度調查中,數(shù)字媒介閱讀率達到了40.3%,其中網(wǎng)絡在線閱讀和手機閱讀成為兩大主要數(shù)字化閱讀方式”。[1]
可以說,數(shù)字媒介正在迅速改變國民的媒介習慣與媒介態(tài)度。該數(shù)據(jù)同時也指出,2012年我國18~70周歲國民包括書報刊和數(shù)字出版物在內的各種媒介的綜合閱讀率為76.3%,比2011年的77.6%下降了1.3個百分點。國民綜合閱讀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即是在改革開放以來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的指導思想下,國民對媒介閱讀的功利性思想依然存在,尤其是在目前的年輕人中,“書中自有黃金屋”的傳統(tǒng)思想逐漸為“不為功名不讀書”的思想潮流所取代,從而使國民的整體思維模式都呈現(xiàn)出一種功利化模式。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將梳理并分析改革開以來我國大眾傳媒發(fā)展特點并反思其中可能存在的問題。
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眾傳媒的發(fā)展特點
長期以來,我國的大眾傳媒一直是黨和國家的宣傳陣地,承擔著“喉舌”功能,它不提倡媒介使用者對媒介信息進行分析和批判,而是無條件地接受。在計劃經(jīng)濟時代,這種意識形態(tài)具有很強的整合能力,在當時的中國社會環(huán)境下作為稀缺資源的媒介曾經(jīng)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成為訴求目標,因而單方面試圖減低或者肅清媒介副作用的“堵”作用越來越小,其作用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
(一)大眾傳媒的市場化,意識形態(tài)的整合能力減弱
在市場經(jīng)濟體制下,一元化的官方媒體進行了改革,而媒介開始實行企業(yè)化管理。因此,官方媒體要面對市場和權力的雙重壓力,而在這一過程中,媒體也出現(xiàn)了許多負面現(xiàn)象,大眾的受眾辨別力急需提升。尤其是對于認識能力還較為模糊的青少年群體,圖解化、感性化的媒介內容使這一群體越來越多地被置身于“媒介暴力”之中。根據(jù)北京市海淀區(qū)法院少年法庭的隨機調查,75%的少年犯受到暴力和色情媒介信息的影響。[2]而我國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大約占了3.67億,媒介暴力和色情對我國青少年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
(二)大眾傳媒發(fā)行量急速上升
伴隨著中國經(jīng)濟的持續(xù)增長,新生媒介開始出現(xiàn)并得到普及,媒介不再成為官方壟斷的稀缺資源,普通百姓也可以面對海量的信息資源。“1978年前,我國報紙基本上是各級黨報,另有少量的行業(yè)報、企業(yè)報,再加上幾張晚報,品種相當單調。截至2009年,全國的報業(yè)集團數(shù)目達到了39家,報紙2119家,雜志9038種,媒體總量是改革開放前的十幾倍”。[3]在這種激烈的競爭下,媒介逐漸從“傳者本位”向“受者本位”轉變。這在擴大社會效益的同時,卻也出現(xiàn)許多媒體打著“一切從觀眾的喜好出發(fā)”而熱衷于明星緋聞、性丑聞、兇殺暴力,甚至是假新聞從而提升發(fā)行量,卻忽視了受眾的真正需求和利益。
(三)重大社會信息的透明化與公開化
傳媒技術的發(fā)展使的信息流動已經(jīng)越出了國家邊界,我國國民不斷呈現(xiàn)價值多元化趨勢,也越來越重視“公眾知情權”問題,因此單一的意識形態(tài)所形成的思想壁壘難以見效。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的危機新聞事件多采用“封鎖消息”的政策。以我國的唐山大地震為例,“在地震發(fā)生的第二天,《人民日報》只對地震災情的詳細情況僅用‘震中地區(qū)遭到不同程度的損失’一句話輕輕帶過,直到1979年媒體才首次對社會披露具體傷亡數(shù)字。”[4]而隨著1998年長江抗洪救災的報道,2003年“非典”報道等一系列危機新聞的報道,我國媒體面對危機新聞時的態(tài)度才逐漸有所改善,突破了單一輿論導向思維以及單向的僵化報道模式,顯得更有“人情味”,更“人性化”。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我國媒體及時、有序的新聞報道則為公眾交出了一份滿意的答卷。
(四)社會主義市場化和民主化環(huán)境也對公民素養(yǎng)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公民更加需要依賴媒介信息從而對自己的生存環(huán)境進行監(jiān)測,由此形成公民行動網(wǎng)絡,推動社會發(fā)展,離不開對媒介信息的綜合與批判能力。目前安徽省“兩會”上,“網(wǎng)絡問政”被首次寫進政府工作報告,重慶市率先對官員啟動網(wǎng)絡問責,武漢市長要求各單位工作計劃上網(wǎng)公開讓市民監(jiān)督等等一系列舉措,就是利用網(wǎng)絡媒體為民主化環(huán)境尋找了新的實現(xiàn)途徑。
三、我國大眾傳媒發(fā)展過程中的問題及反思
在我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對于大多數(shù)百姓而言,大眾傳媒是直接獲取外界信息,保持對政府政策及時消化吸收的最主要渠道。在大眾傳媒的發(fā)展過程中,有如下幾點需要我們反思和注意:
(一)如何強化國民的媒介素養(yǎng)教育
20世紀30年代,英國學者對以新興電子傳播媒介為核心的大眾傳播媒介所代表的流行文化泛濫現(xiàn)象,以及隨之而來的對社會文化傳統(tǒng)、價值觀念以及生活方式所帶來的沖擊表示關注及擔憂。就我國而言,改革開放以來一個復雜的歷史性問題是既要加快速度實現(xiàn)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體制的轉型,又要防止重走資本主義市場經(jīng)濟發(fā)展過程的老路。在這體制轉變的巨變過程中,我國的倫理道德建設同時存在“道德爬坡”與“道德滑坡”的復雜現(xiàn)象,并借由大眾傳媒而迅速擴大。因此,以何種倫理道德建設作為標準以促進國家經(jīng)濟建設和國民道德水平的同步發(fā)展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課題。應當看到的是,我國是一個民主集中制的國家,與之相對應的教育制度也是自上而下的。因此,我國教育行政部門在媒介素養(yǎng)教育中應該發(fā)揮其主導作用。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門要通過法律的手段將媒介素養(yǎng)教育納入到教育體系之中,形成系統(tǒng)的媒介素養(yǎng)教育體制,使大眾傳媒呈現(xiàn)出良性的發(fā)展態(tài)勢。
(二)健全非政府組織,強化傳媒倫理規(guī)約
我國的非政府組織發(fā)展不夠健全,沒有傳媒方面的專門組織或協(xié)會,缺少社會關聯(lián)項目的推動,使得大眾媒體對于當代的媒介道德意識尚存在理論和實踐的誤區(qū),不少新聞媒體從業(yè)人員誤認為傳媒倫理就是“新聞從業(yè)人員的職業(yè)道德”、“主要是新聞單位的自己的事”,在實踐中也拘泥于培養(yǎng)媒體從業(yè)者的職業(yè)素質。學者周直指出當前形勢下我國的倫理論綱主要以“以經(jīng)濟倫理建設為主導,抓住黨政機關、社會團體、大眾傳媒、基層單位這四個環(huán)節(jié)”。[5]因此,在當前形勢下,有關部門應當轉變心態(tài),將網(wǎng)媒體的強制控制轉變?yōu)槿鐣e極、主動的管理模式,積極引導社會力量參與到大眾傳媒建設中來。
(三)促進多元文化與傳統(tǒng)文化的融合
如果說資本主義興起之初是西方社會新舊觀念的轉折點與交匯點,那么改革開放就是我國傳統(tǒng)思維與現(xiàn)代社會交流與碰撞的交叉口。改革開放加速了我國接受西方思想潮流的速度,然而我們也應當試圖從我國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中尋找其現(xiàn)代意義及訴求。因此,一方面,我們要積極引入并借鑒國外發(fā)達國家——如美國和日本的大眾傳媒經(jīng)驗,以更開放的心態(tài)來吸納全球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當將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多樣化的大眾傳媒相融合,從而促進中華民族文化的發(fā)展與創(chuàng)新。
四、結論
中國目前正處于由傳統(tǒng)社會向現(xiàn)代社會轉型的歷史階段,大眾傳媒的迅速發(fā)展已經(jīng)成為我國國民經(jīng)濟的第四支柱產(chǎn)業(yè)。在改革開放之后,我國傳媒業(yè)的蓬勃發(fā)展在某種程度上解構了改革開放之前以及初期整個社會所共有的價值共同體,也使得一部分普通老百姓在面對各種渠道來源的媒介信息時失去了自我。因此,充分發(fā)揮社會輿論機關——大眾傳播媒介的作用,形成有利于社會主義倫理道德建設的氛圍具有重大的現(xiàn)實意義。
[1] 楊嘉.全民閱讀之變[EB/OL] . http://www.pep.com.cn/cbck /6x/201101/t20110106_1010423.htm.
[2] 韋爾伯·施拉姆.大眾傳播媒介與社會發(fā)展[M].北京:華夏出版社,1990.
[3] 李軍林.信息時代的媒介素養(yǎng)[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4] 周直.體制轉換時期倫理道德建設論綱[J].南京社會科學,1996(08):7-13.
[5] 吳廷俊,夏長勇.我國公共危機傳播的歷史回顧與現(xiàn)狀分析[J].現(xiàn)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0(06):32-36.
G206.2
A
1674-8883(2015)23-0114-01
沈樓(1989—),男,浙江杭州人,浙江工商大學國際教育學院哲學碩士,研究方向:當代中國思想道德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