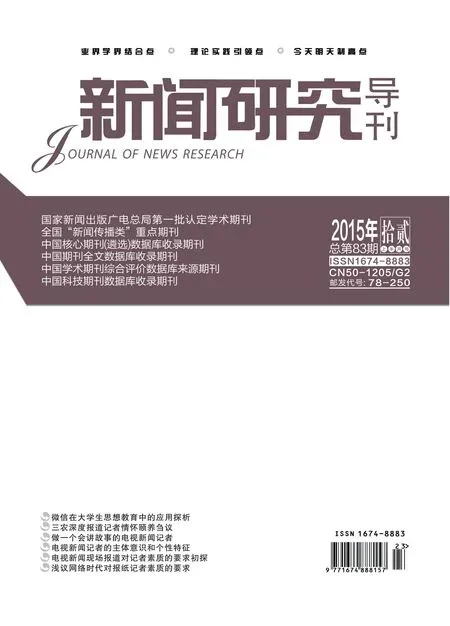重審“李杜之爭”:網絡環境下的公眾輿論
馮 壯
(西北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陜西 西安 710127)
重審“李杜之爭”:網絡環境下的公眾輿論
馮 壯
(西北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陜西 西安 710127)
20世紀20年代,在美國文化界由李普曼和杜威掀起了一場“公眾問題”的辯論,在看待公眾和媒體以及民主的關系上,前者持精英主義民主觀,后者持傳統的自由主義民主觀。本文試圖對雙方的辯論觀點作一梳理和比較,也借此來簡要分析網絡化的今天公眾和媒體以及民主的關系,以更好地認識二人的理論對于今天的意義。
公眾;媒體;民主
這場辯論始于李普曼1922年出版的《公眾輿論》,探討人認識外部世界面對的屏障以及新聞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三年之后,他出版的《幻影公眾》提出了對于美國民主政治的質疑和建議。杜威隨后發表《經驗和自然》(1925)、《公眾及其問題》(1927)以及《追求確定性》(1929),并認為雖然科學高于主觀和政治,但解決問題的手段在于通過傳播讓公眾進行社會參與和意義共享,使公眾、新聞媒體和民主成為一個緊密聯系的整體。本文主要分析李普曼和杜威理論在各個方面的分歧所在,最后簡要說明在網絡化的媒體環境下對二者理論的新認識。
一、爭論的分歧
對于李普曼和杜威之間的爭論,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作一番觀察:
(一)公眾輿論是否真正存在
在《公眾輿論》中,基于對歷史經驗和人性的深刻洞察,李普曼表達了他對傳統民主理念的質疑,這種質疑建立在他對“公眾”神話的深刻剖析之上,在“美國式民主”中,“公眾”經常被高調掛在大眾的嘴邊,被賦予“政治正確”的光環。而在李普曼看來,“公眾”是一個現代神話,其現實處境和民主理論之間的想象存在很大的落差。李普曼選擇把公眾當作普通的個體去看待,而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的子民。每個個體局限于自己特定利益需求的小格局中,只關心同自己的利益息息相關的事情,對社會公共事務也缺乏足夠的興趣,在面對外部復雜多變的環境時,不可能具備集體協作參與解決公共事務的能力。李普曼拒絕把公眾作為有機的整體來看待,如同勒龐筆下的“烏合之眾”一樣,公眾的本質是非理性的。
不同于李普曼的觀點,杜威在《公眾及其問題》中堅持從社會有機體的角度來看待公眾,杜威不認為公眾是原子式的個體,雖然認為真正代表“理性”的公眾尚未出現,但一方面,杜威認為各種各樣的公眾是人類協作的必然結果,不可強異為同;另一方面,杜威認為只要充分傳達知識和科學,一個真正有組織的公眾就將形成。值得注意的是,李普曼從對公眾的主體性的質疑入手,從而得出“幻影公眾”的結論的,而杜威關注的是,傳播作為一種溝通個體的技術手段,如何使公眾成為存在利益關聯的共同體。
(二)專家和公眾的關系
李普曼指出,在媒體制度與公民互動形式的關系中,必須有一群精英的專業人士,代替公眾觀察政治與信息。公民政治的本質已發生變化,現代文明的規模太大,社會制度已變得極為復雜,已非舊式的大眾所能治理。科學、經濟學、外交、法學以及其他領域,要求具備錯綜復雜非常精密的專業知識,使得能力一般的普通公眾無法勝任。因此,有效治理現代政府的唯一希望,只能寄托于培養一批訓練有素的專家,讓他們管理國家的公共事務,公眾只能扮演被動旁觀者的角色。公眾的價值只在介入不同利益派別的沖突,進行選擇時才存在。
杜威指出,公眾雖然不能像職業管理者那樣處理公共事務,但是公眾和精英同樣應當成為政治的行動者。參與社會的過程本身就是一項意義傳播的過程,公眾必須親自參與才能實踐成為真正的公民。他強調健全的公民和自治過程,至少與有效的結局同樣重要。即使公民能積極介入到所有社會必須做的重大決定中,也不能保證那些決定的結果沒有瑕疵,但作為政府和媒體的工作者,有責任去尋找讓公眾能長期參與社會的機制。此外,李普曼沒有解釋專家與公眾這種“局內人”和“局外人”的區分是怎么產生的,而杜威卻從教育和傳播的角度思考了導致這種身份差別的原因。
(三)新聞媒體和民主政治的關系
李普曼作為社會記者和美國政府的政治顧問,他從國家治理的視角出發看待問題,因此持一種民主的功利觀,他把民主看作是應該由人借助科學手段精心設計而能取得實踐功效的一種政治制度,通過精英治理無疑可以減少這種治理的成本,取得直接預期的效果。李普曼關注的重點是公眾獲取媒介傳播的信息內容對社會政治的影響,他認為新聞是一種有選擇性的事實報道。因此,公眾不可能掌握全面準確的消息。傳統的民主理論基于人們對其周圍世界有直接的經驗和理解這種假設,李普曼向我們展現的是,在一個龐大的現代社會中,人們通過主觀經驗很難接觸到準確無誤的信息,新聞媒體的傳播只會加深人們理解世界時持有的刻板成見。
杜威作為社會學芝加哥學派的學者,他從社區研究的視角出發,持一種民主的理想觀,他把民主看作一種借助媒介的傳播和教育促進每個人對公共事務的參與的生活方式。媒介傳播的信息質量固然重要,但信息互動的過程才是更重要的。在杜威看來,傳播不只是把信息從一個人傳到另一個人的簡單過程,杜威認為,傳播本身是一套社會構造的符號系統,是分享社會意義的系統,傳播的成果是社會參與和意義分享。杜威對以李普曼所謂的精英群體的“科學”素養去抵制媒體的觀念偏見和信息誤導不以為然,認為真正的措施是全力保障公眾的各項權利,使其在自由主義報刊的環境下廣開言論,自由交流、發現、聆聽并尊重公眾的合理需求。
二、網絡環境下重審二人的爭論
(一)網絡時代的公眾輿論
網絡空間作為一個虛擬世界,體現的正是李普曼所說的一種“擬態環境”,而且這種擬態環境具有異常復雜的特點,今天許多人已經習慣在虛擬與真實共在的交互場景中生存。這種虛擬生活的主體經驗是如此豐富而無所不在,網民的現實行動都難以擺脫其影響。例如,各類網絡論壇,它們類似于“意見的自由市場”,各種意見在網絡論壇上可以得到充分自由的表達,雖然尚未驗證“沉默的螺旋”在網絡輿論的形成過程中發揮的作用,但在意見的競爭過程中必然會產生強勢輿論對弱勢輿論的壓力,對話語環境形成控制。社交網絡實現了現實生活中的人際關系在網絡上的延伸,其較為透明和真實的氛圍加強了信息傳播的順暢度和有效度,但信息在網絡上的制作、編碼、傳播機制和現實環境仍然有本質的區別,所營造的擬態環境也只是不同于傳統媒體而已,完全符合李普曼對于現實環境擬態化的洞見。
(二)網絡時代的公眾與精英
公眾和精英之間的知識鴻溝可以通過互聯網得到縮小,這類技術樂觀主義的話語是符合公眾對網絡的期待和想象的。在虛擬的多元網絡空間中,各種不同于主流意識形態的意見話語得到了自由的表達,迅猛如潮的信息在弱把關的空間中沖擊著精英對話語的主導地位。然而,借由網絡,公眾和精英之間的隔閡依然沒有消弭的趨勢。一個重要原因是作為公共領域的網絡充當得更多的是一種營銷工具的角色,而非一些公共知識分子對其公共領域化的期待;另一個原因是網絡空間中對討論議題的控制從未改變,對資本和權力的遵循使得網絡主流話語的同質性和宣傳性接近傳統媒體,自由討論的缺乏影響了議題的深入討論,長期也影響著精英和部分公眾對于自由理性地參與公共討論的熱情,交流的缺乏使得公眾和精英之間不同的觀點難以理解和協調,共識的達成更為困難。
(三)網絡、新媒體與民主參與
網絡由于其開放性、匿名性、虛擬性的技術特點,容易成為非理性情緒滋生的溫床,非理性言論的產生固然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信息審查,民意表達渠道不暢,是網絡非理性言論產生的重要原因,但是這種情緒的表達對網絡環境的良性發展并不具建設性,只有合理地處理好規制網絡非理性言論和捍衛公眾的知情權和表達權的關系,才能將對網絡的現實批評減小到最少,一如杜威所說,“不能因為批評而否定新聞在促進公眾民主參與時的作用”。
在網絡化時代回顧這場論戰,李普曼對民主理想和社會現實之間落差的懷疑并未得到消除,但是新媒介技術的發展顯然更符合杜威對于傳播媒介對公眾成長和民主參與的促進期待,李普曼對于公眾和媒體的思考角度具有創新性,卻不免悲觀和極端,而杜威對于公眾和民主抱有一種漸進平和的態度,是可取的。雖然李普曼對于如何實現民主的觀點有精英主義的傾向,這并不意味著李普曼是反對民主制度本身的。杜威認為《公眾輿論》“可能是目前用文字表達的對民主制最有力的起訴”,但是,很少有人會注意到這句話出現在第一段的結尾處,而這一段充滿了對該書“輝煌的,有啟發性,客觀性”的贊譽。杜威將《公眾輿論》和《幻影公眾》這兩本在今天看來是反民主的著作,評價為“論述的是對修正的、有節制的民主理論的信仰”。(蘇·延森,2009)因此,只有同時維護民主的理想并直面民主政治的現實處境,才能更好地面對我們所處的時代。
[1] 沃爾特·李普曼.公眾輿論[M].閻克文,江紅,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 沃爾特·李普曼.幻影公眾[M].林牧茵,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
[3] 約翰·杜威.公眾及其問題[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
[4] 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M].夏鑄九,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5] 單波,黃泰巖.新聞傳媒如何扮演民主參與的角色?——評杜威和李普曼在新聞與民主關系問題上的分歧[J].國外社會科學,2003(3).
G206.3
A
1674-8883(2015)23-014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