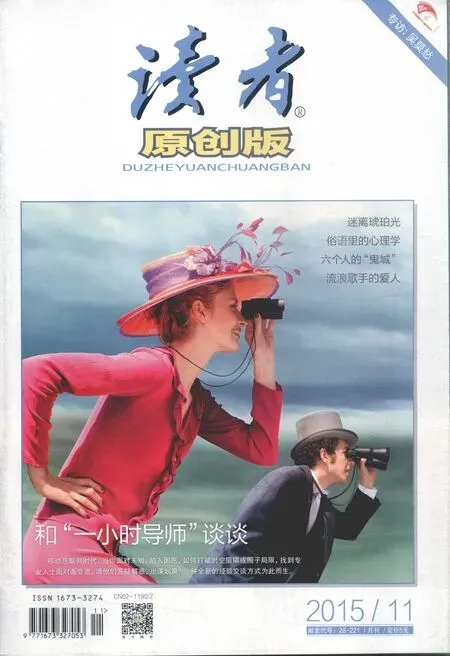鳳凰涅槃
文_吳克成
鳳凰涅槃
文_吳克成



我喜歡靜謐的事物,比如一幅叫“午休”的照片。照片里的這些巴黎人并不是無家可歸的流浪漢,他們在休息,也是在曬太陽:帽子遮著臉,窄窄的一條布就是容身之處,空間逼仄,身心卻舒展。墻老舊,樹影投上去,顯得越發斑駁。整幅照片,波瀾不驚,沒有風云—靜謐大權在握,喧嘩與騷動歸隱了田園。
照片的作者是安德魯·柯特茲。他1894年出生于匈牙利的布達佩斯,早年任職于布達佩斯股票交易所,并開始拍攝照片。1925年遷居巴黎后,他結識了一批畫家朋友,并用5年時間在歐洲打出了自己的天地。43歲時,柯特茲為履行工作合同前往紐約,從此走入人生的低谷:二戰爆發后他無法回到法國,作品又在美國備受冷遇,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在1956年舉辦大型畫展《人類大家庭》,選用了全球273位攝影家的作品,柯特茲沒有一幅作品入選;1961年,赫爾穆特·基爾希姆編寫攝影史,書中對柯特茲只字未提。直到1964年,紐約的現代美術館才想起展出他的作品。
柯特茲的作品大都表現尋常百姓的生活,翻看他的照片,仿佛走進了充滿煙火的日子,比如《蒙德里安的家》《埃菲爾鐵塔腳下》《叉子》。與這些家常的內容相吻合,他所用的手法也大都是隨意的,不像布列松,非要等到一個“決定性瞬間”才出手。
內容與手法看起來雖都是信手拈來,但細品又有風味,這是因為他在拍照時很注重作品的構圖。比如在《蒙德里安的家》里,垂直的門線,樓梯扶手與臺階的圓弧,桌子的水平線,圓形的花瓶,平鋪開來的墻以及花瓶的陰影收在一起,組成了簡潔的畫面。日常,讓他的作品貼近大眾;注重構圖,讓作品看起來協調簡潔;協調簡潔,又讓日常生活顯得韻味悠長。
難怪柯特茲紅遍歐洲,卻在美國坐了將近20年的冷板凳。歐洲是個優雅之地,尤其是巴黎。1925年,31歲的柯特茲從匈牙利移民到法國,兩年后他在巴黎辦了首次個展,立刻就被時尚的巴黎人接受,連向來戴著有色眼鏡看攝影的藝評家對他也不吝贊美之詞。40歲時,他成為歐洲的攝影大師—他作品里的優雅與詩意,暗合了歐洲人的審美情趣。
相對于巴黎,柯特茲踏上美國的土地時,美國正處于百廢待興時期,用柯特茲自己的話說,“美國的攝影界只懂得技巧性地記錄照片,而不懂表達性的創作”。他的審美趣味在美國水土不服,所以將近20年美國人沒有理睬他。到美國的攝影漸漸發展到歐洲多年前的水平,美國人意識到柯特茲的價值時,柯特茲已經74歲了。
很多人把柯特茲歸類到結構主義攝影家里—通過奇特的視角、特寫、陰影、線條等表現景物與人,以突出一些需要重點表現
的部分,讓照片呈現出明顯的結構形態。
也有人把柯特茲歸類到超現實主義攝影家的行列,因為在1933年前后,他曾經拍攝過一個人體變形系列。他在一個特殊的房間,用了一面類似于哈哈鏡的鏡子,將女性的身體投射到鏡子里,其局部被放大或者縮小—有時屁股成了綿延的山丘,有時大腿成了細絲……這些照片里有畢加索立體派繪畫的影子,但是它們只是些隨意的鏡頭,像小孩子一時興起玩的過家家,并不像立體派繪畫那樣充滿隱喻。柯特茲對自己超現實主義攝影家的頭銜也持否定態度,他說:“我不是超現實主義者,而是現實主義者。現在這個組織—超現實主義—居然在使用我的名號。”
1972年,在他出版《攝影生涯六十年》之后,連跟他并無多少交集的攝影界泰斗布列松也寫信來祝賀。他說:“謝謝您出了這么偉大的一本書,您才是我真正的老師,我以身為您的學生為榮。”


總之,柯特茲的照片簡約而不簡單,司空見慣的家常題材,他卻總能化腐朽為神奇。有時翻看他的照片,掩卷后會想起明清時的文人淑女。任憑外面濁浪滔天,他們的屋內總是靜謐溫婉的,清淡的日子,在他們的妙手中變得有了聲色。
當然,這靜謐溫婉需要素養,更需要孤高的信念為基石,否則,外面的重壓一來,立馬會一敗涂地。美國女詩人狄金森生前只發表過7首詩(她現存詩作有1800余首),但是她說:“我的詩一定得亮著自己的光芒,無須他人的擦拭。”她堅信:“今天世界將黃金當成垃圾,但時間只會讓它更珍貴。”
柯特茲也是這樣的人。他終其一生都堅守自己的創作理念,用他始終溫婉內斂的鏡頭擦亮了所有的清淡日子,他獨特執著的視角讓日常的物什脫胎換骨,宛如鳳凰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