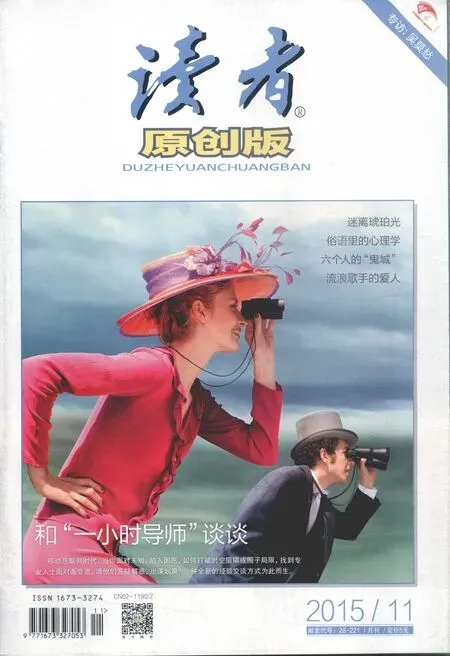記一家倒掉的燒餅店
文_王這么
記一家倒掉的燒餅店
文_王這么

最好吃的燒餅,是剛出爐的。
我家這邊流行“蒙城燒餅”。鞋底狀的油酥燒餅,剛出爐的時候熱氣騰騰的,繃起金黃油亮的脆殼,那殼一碰就碎,一咬,落一地芝麻和碎屑,嘴角上、臉頰上還狼狽地粘著幾粒。餅里頭卻是叫人心安的柔軟,仔細看,面被分成了一層又一層,可以用手扯開,透過它能看見對面的人影。
一爐剛出來的好燒餅,涼起來也快,要立刻吃,邊走邊吃,顧忌形象準得后悔。等帶到家里就涼了,而且捂在塑料袋里,熱氣與水氣將外面那層寶貴的脆皮都變得綿軟了,還有什么吃頭。
最難吃的燒餅,是第二天回爐加熱的。
做燒餅的材料不過幾種:香油、豬油、面粉、鹽、芝麻、五香,可能還有蔥花,想做得好卻是極難。本地滿街掛著“淮南牛肉湯”招牌的小店里,必然會賣蒙城燒餅。有些大飯店,也會很親民地做一做。
但到目前為止,只有兩家店的燒餅令人滿意。一家已經倒閉了,他們家是專做阜陽菜的,偶爾有一次路過,進去吃,吃完了叫好,就隔三岔五地去。總是傍晚過去,從東向西,迎著正往下落的太陽。穿過人車擁堵、兵荒馬亂的市區主干道—有一陣子還在修橋封路,必須從高聳的瓦礫堆上翻過去,再鉆過一排遮天蔽日的腳手架,一邊鉆,一邊縮著腦袋,擔心上面掉鋼筋下來。
到了地方,不禁嘆一口氣,想如此歷經艱難,就是為了吃兩個燒餅,喝碗羊肉湯,似乎領略到一點兒平凡人生的歡愉,以及別人看不上眼,自己也覺得拿不出手的歡喜。
進了門,到柜臺前面點單,固定幾樣,先付錢。
一堂的木頭桌子,有方有圓,上著暗紅色的漆,漆掉了色,又糊滿了油。服務員一個箭步過來,在你坐下之前,搶著用抹布狠狠一通抹,臨走,又把桌上的筷盒整一整。走幾步,又從隔壁空桌上拿了兩個醋碟過來,往這邊一放,才很放心地走了。
這家店除了收銀員是個神氣的瘦姑娘,服務員全是中老年婦女,都講著一口安徽話。老板是個穿背帶褲、挺胸凸肚的大胖子。三天兩頭,看到服務員們就在大堂里頭沖老板吆喝,粗魯的方言,說得快,聽不清內容,只聽得出語氣不善。老板站在那里,忍耐地皺起眉頭。
大概都是鄉里鄉親,沾親帶故,又都是女的,說不得打不得。
我們坐在那兒吃著,陸續進來些食客,要的東西也差不多。燈光不夠明亮,每張桌子之間,不知為什么距離隔得很遠,講話都像在竊竊私語。
空氣里有種奇怪的沒落而家常的氣氛,明明是在鬧市區。
除了蒙城燒餅,他家做得好的
還有菜饃、卷饃、油茶、豆雜面、牛肉板面。
菜饃不是饃,是夾著青菜的幾層軟面餅,層疊之狀,有點兒像有名的西點拿破侖。菜切碎了拌上鹽和油、面同時蒸,面熟了,菜仍保持著青綠,吃時配一小碟辣醬或小菜。
卷饃也不是饃,是用春卷皮一樣的薄面餅,卷著豆芽、黃瓜條、油面筋,外帶一根炸脆的油條,倒挺像肯德基的老北京雞肉卷,但素淡得多。
油茶也不是茶,是一種酸咸微辣的稀面糊,很像在河南吃過的糊辣湯,但味道沒那么重,還加了切得細碎的海帶、豆腐皮、干絲、花生仁,湊在碗邊喝,鼻端傳來很好聞的咸鮮之氣。
他家的燒餅,層次做得豐富、細嫩而有韌性。我喜歡再要幾串烤羊肉,夾進餅子里吃。
早年在北方吃論斤賣的大餅,表層滿滿地鋪著芝麻,極飽腹。買完餅后再到另一家熟食店買帶著赤褐色醬汁的醬牛肉,讓賣家切好了,帶回家慢慢地夾餅吃—就是熱愛這種吃法。從前北京的三輪車夫,大概也是這樣吃的。熱騰騰的熟面餅里,悄悄裹著大塊的肉,狠狠咬下去,有輕松的富足感,就好像同奢侈品牌云集的高檔商場相比,總還是露天的菜市更讓人產生對生活的熱愛,更有天下太平的安全感。
本地最多的就是飯店,但很難找到幾家味道過得去的。偶爾發現一兩處好點兒的,多去幾次,也就失望了。要說原因,不外乎原料太差,菜急于上桌而偷工減料,大多數只靠所謂“川味”的麻辣調味料撐著,糊弄越來越重口味的食客。這種情況下,偶爾能吃到真正面、油、米的本味,反而是驚喜了。
越簡單的東西越吃不厭,就好比越平淡的感情越能長久。
吃飽了出門,已經過了掌燈時分,燈火滿城。
半年之后,這家店令人措手不及地倒閉了。站在馬路邊,看著緊閉的玻璃門上用紅色油筆寫著的“招租”兩個字,感到很是悵然。
再次吃到好的燒餅,居然就在家門口。
父親過生日,想附近還有哪家店沒去過,就找到了這家。
不設大廳,只有裝飾得極俗氣的包廂。大白天拉著白紗與醬油色的雙層窗簾,玻璃吊燈低低地垂到頭頂,燈光暗淡,墻上都包著厚厚的隔音棉,讓人感覺不大像正經吃飯的場所。服務員又從來不敲門,總是大大咧咧地闖進來,飯菜的價格比周邊所有飯店都貴。總之,是家有點兒古怪的店。
出乎意料的是,菜的口味比周邊所有飯店都好一點兒,燒餅尤其好。和倒閉的那家比起來,他們的燒餅層次要少一些,但外皮更脆,脆到怎么輕拿輕放都掉屑的地步。所以雖然嫌貴,還是給自己找各種借口,接連去吃了幾次。直到最后一次,他們端上來了回爐的燒餅。
真是好生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