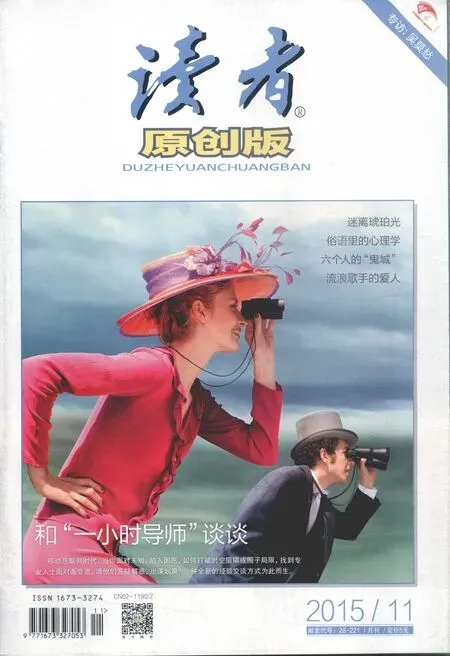生活的苦是藝術的財富
文_李書喜
生活的苦是藝術的財富
文_李書喜

巴山新路 68×136cm 2001年
Q=李書喜,A=趙振川
Q:我知道你對甘肅的感情很深。
A:是的。甘肅的農民都熱愛藝術,對書畫的偏愛讓人很感動,這在全國少有。我少年時期下鄉的地方離甘肅很近,那里的“花兒”很高亢,站在山頭上、曠野里能體會到那種天人合一,讓人充滿遐想。
Q:你的弟弟、著名作曲家趙季平是在甘肅出生的。
A:1945年,抗日戰爭時期,我們全家躲到了甘肅平涼,我的弟弟趙季平就是那時候出生的。
Q:你的父親趙望云先生多次深入西北地區寫生,河西走廊的戈壁、沙漠、草原、雪山,嘉峪關、祁連山、敦煌莫高窟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跡。他進入新疆寫生時,黃胄作為趙望云先生的學生隨他第一次接觸新疆風情。趙望云先生以《大公報》記者的身份開始西北寫生,到從中國畫本體尋找國畫的出路,西北的人文歷史、民族風情是他藝術創造、創新的源泉,這些都成了奠定了長安畫派的基石。
A:他在《大公報》時,最早用畫作做新聞報道。他刊登在《大公報》上的農村寫生,社會反響很大。當時的中國,外來的繪畫方式與風格占了相當重要的地位,徐悲鴻、劉海粟主張用西方畫改造中國畫,我父親沒有走這條路。他是通過生活的體驗去改造中國畫的。他是用藝術的視角—以前精英文化表現的都是亭臺樓閣、名山大川、達官貴人,他畫的都是窮困潦倒的百姓、破敗的農村、西北的荒漠和窯洞。黃胄是我父親的入室弟子,在我家生活了很多年,我們的感情很深。他隨父親去了新疆,這是父親大西北寫生的又一次征程,也是黃胄藝術的啟程。

趙振川,1944年生于西安,祖籍河北省束鹿縣。國家一級美術師,中國美協理事,中國美協國畫藝委會委員,黃胄美術基金會常務理事。陜西省第四屆文聯副主席,陜西省美協名譽主席,陜西長安畫派藝術研究院院長,陜西省政協委員。任北京大學藝術學院高研班導師,中國人民大學客座教授,西安美術學院客座教授,西北大學客座教授。國務院授予突出貢獻專家,陜西省“德藝雙馨文藝工作者”。陜西省委、省政府授予“第二屆陜西文藝大獎藝術成就獎”。作品先后入選第四、七、九、十、十一屆全國美展,經常參加當代中國山水畫提名展、綜合性畫展、國際水墨畫交流展等國內外大型邀請展,作品被中外美術館、博物館及個人大量收藏。

欄目主持_李書喜
Q:長安畫派曾在畫壇獨領風騷,甚至影響了中國美術史的發展。你是怎么認識長安畫派的?
A:長安畫派有一手伸向傳統,一手伸向生活,堅持面向生活,堅持中國畫的優秀傳統,它將傳統和現實生活相結合,把古老的中國畫進行了精神上的改造,使它走向了現代,走進了生活,并為中國畫注入了新的情感。長安畫派對中國畫最重大、最根本的影響是用生活的情感去改造中國畫。當代中國人對待民族文化是崇敬的,對外來文化,我們可以借鑒,但不能照搬。長安畫派的老先生們都很開放,又對自己的文化充滿信心,他們的思想和精神是屬于這個時代的。他們是革新者、革命者,同時熱愛自己的文化,但是在繪畫上又不會止步于前人的成就。
Q:你可否具體講一下長安畫派幾位主要畫家的特點和成就,他們都從哪些方面影響過你?
A:我的父親寬厚、仁慈,對勞動人民充滿感情,熱愛藝術,熱愛祖國。他辦過抗戰畫刊,民族責任感很強。他經常對我說,中國畫的根本在于其中包含的精神,在這個問題上,他的認識是深遠的。石魯先生評價他“尊美重德,藝為人民”,我認為是很中肯的。石魯先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去研究中國畫的學問,比方說認識論和實踐論。我是從他那里開始從這兩方面去研究中國畫的,我的藝術理念受石魯先生的影響比較大,他是一個犀利敏銳、天賦極高的人。我的師兄黃胄就像我的精神偶像一樣,他對藝術的追求很執著,病倒了都還在畫畫,他總是在否定自己中提高自己。他強調藝術家要有生活,即創作的實踐
和生活的積累,說最偉大的藝術家是從泥土里滾出來的。方老(方濟眾)是一個能看見別人優點的人,無論是生活中還是藝術上。他的小品畫都很精到,很有趣味。何海霞先生給我講過筆法、墨法,在傳統的學習上,是他手把手地指導我。

隴東人家 175×135cm 2004年
Q:你可以說是成長、生活在大師、大家的圈子里,但你上學時讀的是統計學,能講一下你的這段經歷嗎?
A:我的成長有一個很好的文化氛圍,說我是在大師的圈子里長大的并不為過。我的父親在那個困難的年代培養了許多學生,他不僅培養了個人,也為中國畫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中國畫有像黃胄、徐庶之、方濟眾這樣有成就的人,和他是分不開的。我上學的年代,個人選擇不自由,學校讓學什么就學什么。學統計學、政治經濟學、運籌學等這些科目對我也是有好處的。自然災害的時候,學校實在辦不下去了,我們就畢業了,正好美協當時辦了一個中國畫學員班,我就去學畫了。后來我下鄉到隴縣,雖然鄉下很苦,但是對生活、對藝術有了更多理解。我把生活的苦轉化為創作,變成了一筆財富,對于生活和藝術的理解也更為深刻了。藝術家就要有感悟生活的能力,能在生活中尋找美。
Q:在你早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你對長安畫派幾位重要的畫家做了系統性的研究,可以說是集長安畫派之大成。你提出的“泡菜理論”得到了理論界的廣泛贊同。其實也是長安畫派“一手伸向傳統,一手伸向生活”的繼承和延伸,也是進一步的探索和嘗試。

巴山旋渦 136×68cm 2006年
A:泡在生活中是什么?就是一種深刻的改變,所謂“泡菜理論”,就是要從精神深處去改變。深入生活的方法就是親力親為,就像泡酸菜一樣—把菜泡酸了,發生質的改變,這是我對藝術的理解,也是對長安畫派理論的一種發展。
Q:你認為一幅好的山水畫應該是怎樣的?你如何看理論和實
踐?中國畫的發展最應該注重的是什么?
A:一幅好的山水畫一定要有故事、有內涵。故事是創作作品時思維的過程,是生活的感受。我通過不斷實踐、探索,認識到藝術是一個復雜的體系,其中有不少哲學問題。藝術是精神層面的,不是世俗的。我反對用理論指導創作,我個人的理論學習遵循的是通過實踐尋找真知,有針對性地提高自己的綜合素養。我們要認真研究傳統,但不能被傳統嚇住,畫起畫來應該所向披靡、無所忌諱,要以“自我”為主,“自我”是藝術家非常重要的一種素質。
Q:你和家人把趙望云先生的三百多件作品捐獻給了中國美術館。
A:我們當時捐了352件作品,我們覺得這些作品不應該是我們一家的財富,應該貢獻出來,方便有需要的人研究。
Q:發現你的一枚新的印章上面刻著“七十從心”,這有什么寓意?
A:是我的外甥女幫我刻的,源于孔子的“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說我可以在藝術上更自由一點兒了。

漢水寫意 83×152cm 2007年

額旗印象 90×98cm 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