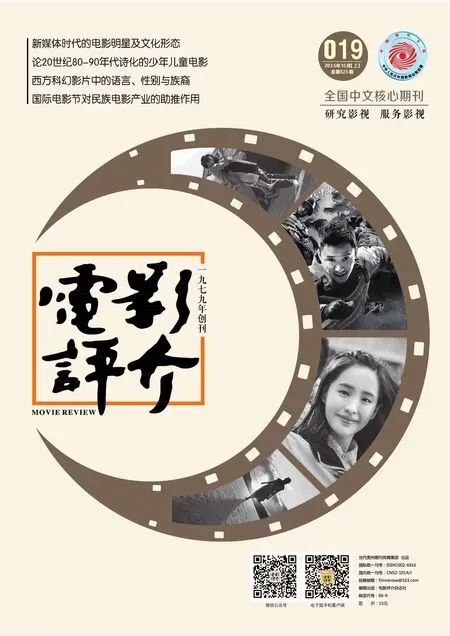現代派電影的哲學研究
王松巖
現代派電影的哲學研究
王松巖

電影《現代啟示錄》劇照
一、現代派電影與哲學的結合
電影哲學研究指以電影現象的意識形態實質為主題的研究。在所有學科中,美學與哲學的關系可以說是最緊密的。許多西方學者都明確指出,藝術首先是哲學的存在,其次才是藝術本身。電影美學是電影哲學的一個分支,從藝術的觀點審視哲學,然后從“人”的角度去看待藝術,是電影美學的存在意義。從電影美學視角來看,電影實際上是人類思想意識與電影情節的完美融合。用布萊希特的話說,電影是電影藝術哲學的產物,它可以使人們的思維由哲學角度引入到藝術角度。與以個體生存處境為關注焦點的戲劇相比,電影的哲學品格主要表現在對人類生存處境的理性思考,人類能夠知道什么?希望什么?該做什么?是電影美學反復追問的命題。現代派電影在美學思想上比較接近西方現代派文學,其影響力和傳播的內容也更加哲理化。
現代派電影深受西方哲學思想影響,薩特的存在主義、柏格森的直覺主義、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學說,都給現代派電影帶來了深遠的影響。20世紀60年代,現代派電影在情感表達、哲學觀念表現等方面進行了積極嘗試,電影藝術與哲學的無限接近性也受到了人們的廣泛認可。后來,隨著電影藝術向及時性、具體性方面的不斷靠攏,現代派電影中所體現的科學哲學世界觀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如電影對人與自然、社會的關系的描述視角更加獨特,它也越來越善于通過直觀的影像表達人們的情感危機、揭示人在不同環境中的三重異化。它從不回避對人、對人本、人存在的困境的關注,現代派電影史上的許多杰作,無不是創作者們對世界對人類存在高度審視的結果。如英格瑪·伯格曼的《野草莓》是對人生終極意義的思考,美國電影《現代啟示錄》是對越南戰爭的關注。可以說,現代派電影對現實存在的關注,在這一點上,與哲學的主旨——哲學要思考和關注世界不謀而合。
二、現代派電影的生存美學范式
馬克思主義美學及其異化的思想,是電影存在主義的根源,也深刻影響了電影美學藝術的內容和電影的審美形式。其中,直接給現代派電影造成影響的,是以海德格爾和薩特為代表的存在主義學派。說起西方存在主義,不能不提到西方存在主義的先聲盧卡奇,盧卡奇是西方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也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推動者。他曾在《歷史和階級意識》一書中對馬克思主義做出了新的解釋,并廣受西方哲學界認同,這也為西方社會批判理論、馬克思美學、存在主義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盧卡奇認為,藝術雖然與哲學相似,具有一定的認知功能,但是,要想創造出既忠誠于現實又忠誠于馬克思主義的美學作品,還需要創作者堅守歷史唯物主義觀,以馬克思所提示的方法為指引,以生活為基礎,對現實進行客觀察和加工。[1]進一步來說,藝術是生活的反映,每一種藝術都指向人的整體,其存在形式是第一性的,人的心理是第二性的,無論是哲學研究還是電影藝術創作,都以本體存在為前提。現代派電影就繼承和發展了這一哲學思想,并積極從認識自我的角度契入對藝術和生活本質的思考。
馬丁·海德格爾是存在主義哲學的一面旗幟,他堅信哲學就是對“存在”的思考。所謂已在的東西,就是“在者”。所謂存在,是先有“在”,其次才有“在者”,而要解決“存在”必須先追溯“存在者”,把握“存在”的“在場”“發生”的時刻。如何把握在場呢,那就是在“前思狀態”下“去思”。與那種對客體范疇化的思考不同,海德格爾的“去思”強調的是對存在到場的召喚,關注的是召喚與自身的交付。因此在他看來,人的存在是生命強加的,人類對“無”有著先天畏懼之情,而且,人總是不斷與外物發生著各種關系,這是人痛苦的根源,這種憂患意識將持續到生命結束,這也是人無法選擇的。然而,從姻緣性的角度來看,世界上的任何用具都不是孤立的,各種事物之間客觀存在的姻緣關系組合到一起,就構成了生活“境域”。而只有借助藝術的形式,用具的可靠性才能被啟示,才能體現出來。概括來說,海爾格爾的哲學思想就是:“物本身”是不可知的,我們必須通過藝術作品才能接近物本身,感受物之存在。我們要對物的存在泰然任之,要敢于接受不可改變的事實,并用非客觀化的“思”與“言”解釋事物的真相。[2]海德格爾的濃郁憂患意識和反思精神哲學思想,實質上是對人及其根源的關心和思考,這一關心人本存在、帶有詩思合一色彩的美學思想,也給后來的哲學家和現代藝術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對事物本身存在的思考,并克服人與事物之間的屏障,真實接近事物,也成為現代派電影的美學追求。
讓·保羅·薩特,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哲學家之一,他也是存在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受胡塞爾現象學思想影響,薩特提出了“現象學的本體論”,他認為,人是自為的存在,人是先于人的本質特征而存在的。人是自由的,人必須自由地為自己做出選擇,世間所有,甚至人本身,都要靠人本身來選擇和建構。在薩特存在主義哲學體系中,“存在”指人的是人自我感覺到的存在,是個體非理性的情感體驗,而物只能用“有”來表示。如果人不存在,感覺消失,一切也不復存在。換而言之,人就像一粒無根的種子,在人存在之前,人沒有任何本質可言,而人要想證明自己的存在,必須確立自己的本質,用行動來證明一切。這一點,與物明顯不同,物不能選擇和造就自己的本質,其本質是人按照自己的需要來給予的。[3]借助人與物的不同,薩特揭示了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可貴之處,肯定了人的價值和尊嚴,它可以引導人們采取積極行動去創造本質。因此,也有人將薩特存在主義哲學視為行動哲學。世界荒謬,人生痛苦,是薩特存在主義哲學對人類生活狀態的基本觀點。自由選擇則是薩特存在主義的精義和核心。薩特認為,人只有按照個人意志作出自由選擇,才不算失去“自我”,才能稱得上真正的存在。從中可見,薩特自由主義還帶有人道主義的色彩。掌握自己的命運,通過自由選擇和自主創造實現自己的價值,是薩特存在主義給現代派電影的啟示。
三、現代派電影的現在存在
現代派電影是在特定的社會思想環境中產生的:兩次世界大戰,動搖了人們對文明和宗教的信仰,持有同一種宗教信仰的人、處于文明中心的人們竟然會相互殘殺。人類非理性的心理狀態,也引起了西方思想界的高度關注。現代派電影正是在西方現代主義哲學和文藝思潮影響下產生的。以非理性主義思想來掌控創作活動,并在創作中擺脫理性束縛,借助非理性的原始直覺、本能、潛意識等彰顯創
作者的自我意圖,是現代派電影的共同原則。如果說法國電影是現代派電影的先鋒,那么,意大利電影可以說是現代派電影中的佼佼者,許多意大利電影大師如安東尼奧尼、費里尼等,都是善于電影藝術時空轉換來體現唯我主義的非理性主義思想者。確切來說,對西方現代派電影的產生和發展影響深遠的因素有: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歐洲表現主義和超現實主義先鋒電影運動,40年代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運動,精神分析法、現象學、現代主義等影響。其中,現代主義思潮更是直接促使了現代派電影的產生。
從哲學的視角來看,博格曼和安東尼奧尼最具研究價值的現代主義大師。瑞典現代派電影大師英格瑪·博格曼與費里尼(意大利)、塔可夫斯基被稱為電影藝術的“圣三位一體”。博格曼是世界影壇上少數將電影納入嚴肅哲學話題的人物之一,他一生都在探究人生的意義,他也喜歡在電影中討論生活與靈魂,他的電影從不以將故事為主題,幾乎他所有的影片講述的都是自己的思想觀點以及耐人深思的哲學問題。博格曼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就站在哲學立場去思考上帝的存在、死亡、生命、孤單等一些敏感問題。他用影像詰問生存的意義、永恒的沉默,并通過對存在、虛無的反思,去糾正一些人對“他人即地獄”的誤解,在他的電影里,各種失真的物像和潛意識經常交叉在一起,心理式的敘事結構比比皆是,人的狀態都是非理性的,人與人的關系糟糕而扭曲,人本身就活在雙重地獄里。海德格爾曾將生存的時間特征定義為“煩”之根本,博格曼在這一點上與他非常接近,終其一生,博格曼都沒有走出自己的童年,他一生都被時間和記憶捆綁。借助非理性的表現,博格曼深究了現代人生的終極意義,其作品在思想和存在上也突破了時空限制。
意大利現代派電影大師米開朗琪羅.安東尼奧尼是全世界公認的電影泰斗,安東尼奧尼年輕時曾傾心造型美術和喜劇,這是他寫實主義思想的根源,他擅長揭示人與人在相互隔閡的存在狀態下的內心世界。20世紀60年代,西方國家已經邁入現代化生活階段,不過,在繁華的社會表像下,宗教、冷戰沖突暗流浮涌。在技術化社會里,在享樂化文化引導下,人類將走向何方,是安東尼奧尼關注的問題。安東尼奧尼用悲觀的眼神將人類的存在狀態進行了視覺化描寫,在他的電影中,攝相機鏡頭總是不帶任何感情,人與人的關系總是很遠,并且,幾乎所有人物的行為都帶有哲學色彩。一般商業電影中常見的特寫鏡頭和花哨的電影技巧,在人的作品中都極其少見,演員也總是按照他的要求盡量做最少的外部效果來表現真實的生活和沖突。雖然安東尼奧尼的簡約風格與開放結局的敘事方式并不被包括博格曼在內的電影大師和許多電影評論者所看好,但是,安東尼奧尼始終堅守自己的創作原則:用本真的表演,去揭示客觀存在。這種過于客觀的客觀主義,是其“內心現實主義”的真實寫照。從薩特存在主義的角度來講,他是因為對存在的懷疑,才通過自我符號化來描述存在的不確定性。而安東尼電影中人與人之間的“疏離”,與其說是人與人之間的無法溝通,不如說是“他人即地獄”的影像化。
結語
由上述可知,現代派電影其實就是運用現代主義創作原則進行影片創作的電影流派。早期的現代派電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觀的關聯性較強,早期現代派電影幾乎所有關于哲學問題的討論,都會涉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真理觀。不過,如今,哲學逐漸回歸現實,從生活存在的視角審視馬克思主義哲學,用電影藝術去反映個體存在,詮釋個體情緒性的體驗,逐漸成為現代派電影美學思想的內核。今后,現代派電影研究理論涉及的范圍也會越來越廣,電影理論研究者要正視文化實情,深入探索人的本質、人與世界的關系等問題,只有這樣,才能促進社會哲學研究和電影美學研究的共同進步。
參考文獻:
[1]格奧爾格?盧卡奇.審美特性[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41-47.
[2]馬丁?海德格爾.海德格爾選集[M].孫周興,譯.北京:三聯書店,1996:403-416.
[3]讓-保羅?薩特.存在與虛無[M].陳宣良,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87:13-38.
【作者簡介】王松巖,女,吉林公主嶺人,白城師范學院講師,博士,主要從事哲學方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