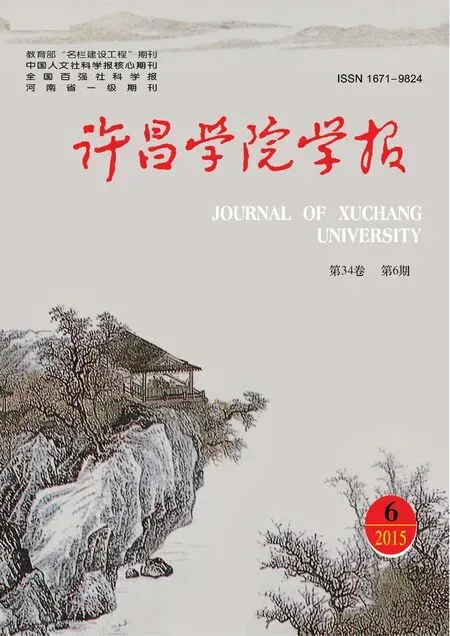曹魏屯田與周口社會經濟發展
王國民
(周口師范學院文學院,河南周口466001)
曹魏屯田一直受到史學界的重視,并且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然而,周口作為曹魏屯田的中心區域之一,學術界的關注仍然不足。有鑒于此,本文以地處潁河流域的周口為研究范圍,以屯田與周口社會經濟發展為視角,通過文獻梳理,結合歷史地理、歷史遺跡考察等,對曹魏時期的周口屯田進行初步的探討。
一、曹魏周口屯田的時間和特點
周口,古稱陳,地處豫東要沖,無山水之隔,交通便利,自古便是兵家必爭之地。清代顧祖禹說,陳地“控蔡、潁之郊,綰汴、宋之道,淮泗有事,順流東指,此其經營之所也。……又其地原隰沃衍,水流津通”,[1]2174-2175漢武帝時汲黯為淮陽太守,修陂塘以灌溉民田,三國時賈逵為豫州刺史,修運渠二百余里,鄧艾又在淮北潁河流域大舉屯田,促進了周口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
(一)周口是曹操最早屯田的地區之一
曹魏的屯田始于東漢后期的曹操時期。棗祗是屯田的最早倡議者,還是早期的領導者。《三國志》記載,建安元年(196年),“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2]14《資治通鑒》也記載:“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為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谷百萬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谷,倉廩皆滿。”[3]1990
棗祗屯田的許下在哪里呢?束世澂認為許下在襄城,陳家麟認為許下在潁陰。[4]18多數學者主張許下在今天的許昌市及其周邊地區。
周口與許昌接壤,周口西華縣黃橋鄉有棗口村,就是棗祗當年屯田留下的遺跡。1993年出版的《西華縣志》記載:“相國曹操以羽林郎棗祗為屯田都尉,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西華屬其范圍(西華今有其遺址——棗口)。”[5]10
民國版《西華縣續志》也記載:“按今西華縣西十五里潁河東岸有棗祗口。《河南通志·水利篇》載稱:“棗祗河,在縣西南十八里,三國時棗祗鑿井灌田。乾隆舊志亦稱為漢棗祗屯田引潁水遺跡。臨潁之石梁河即潩水,由臨潁至西華合河口入潁,其地距臨潁之棗祗河甚近,然則棗祗口與棗祗河皆屬于棗祗許下屯田之范圍明矣。”[6]19
綜合上述記載,周口是曹操最早屯田的區域之一,周口屯田始于建安元年(196年),建安二年(197年)周口大部分地區都有了屯田。劉靜夫說,建安二年(197年)“屯田便在當時的轄區內推廣了。曹操當時的轄區還只限于司、兗、豫三州,見諸記載的屯田區有潁川、許昌、襄城、汝南、西平、西華、睢陽、梁國、陳國、譙郡……。它們主要分布在今河南省及其與鄰省交界地區。……其后,曹魏在統一北方過程中和統一后又新設立了一些屯田區。”[7]18
(二)曹操時期的屯田以安置流民和強制生產為特點,具有明顯的時代性
周口是中國農業文明的發源地之一,從夏商周至兩漢,人口稠密,一直是重要的農業區域。但從黃巾起義到三國初年的30多年里,由于戰爭、天災、疾疫和流移遷徙,人口驟減,土地荒蕪,“自遭喪亂,率乏糧谷,……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蕭條。”[2]14面對凋蔽的經濟、動亂的社會和大量的無主荒地,曹操認識到,要安定國家,首先就要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夫定國之術在于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8]783
潁河流域是黃巾起義軍活動的主要地區之一。活動在潁川(今河南禹州)、汝南(今河南汝南)、陳國(今河南淮陽)一帶的起義軍,由波才、彭脫等領導,是黃巾起義軍的主力之一。建安元年(196年)活動在豫州潁川、陳國、汝南的黃巾軍被曹操鎮壓,“及破黃巾定許,得賊資業。”[2]489“資業”就是從黃巾軍手中奪得的耕牛、農具等生產工具,也包括大批勞動力,這些是曹操推行屯田的基本條件。借助這些“資業”,曹操采納棗祗的建議,在潁川郡、汝南郡、陳郡就地組織屯田。荒蕪的土地得到了開墾,流離的人民得到了安置,動蕩的社會因此穩定。曹操屯田是對漢代屯田的繼承和發展,在屯田實施的過程中,曹操又進行了一定調整和完善,以后則在中原廣大地區逐步推廣。陳家麟認為曹魏“民屯幾乎集中于內郡,特別是黃河以南,淮河以北的汝水、潁水、渦水諸流域,亦即曹魏統治中心的司州、豫州、兗州一帶,尤以司州最為集中。”[4]21所以,曹操在潁河流域的屯田是具有實驗和示范雙重意義的。
民屯的管理者分別稱為典農都尉、典農校尉、典農中郎將等,組織形式也仿效軍隊系統,屯田民沒有自耕農民的自由身份,不能自主經營,生產具有強制性的特點。西晉建立后,由于民屯實施的條件已發生了變化,加之屯田民的生產積極性不高,才正式廢止民屯。
今周口各縣有眾多以“屯”為通名的村落。商水縣民間流傳“南屯北營”的說法,南部的固墻、魏集、袁老、胡吉4個鄉鎮有17個以“屯”為通名的村落。進一步的調查發現,這些以“屯”為通名的村落來源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和曹魏時期屯田有關,屯田的管理者是司馬,通常多以這些屯田單位小頭目的姓氏冠以“屯”字,其后裔久居此地而沿用至今;二是和明初移民屯田有關。
(三)曹魏后期的屯田與興修水利相結合,具有明顯的軍事性
曹操時期的屯田以民屯為主,而從曹丕建國到魏末,軍屯、民屯并重。營是軍屯的基層組織,軍屯的各級將領就是軍屯的管理者。《三國志·鄧艾傳》《三國志·諸葛誕傳》《晉書·食貨志》《太平寰宇記》卷十一等材料中都記錄有曹魏周口屯田的記載。
1.疏通漕運,開鑿河渠,灌溉農田。鑒于潁河流域“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2]775和軍事漕運的迫切需要,曹魏周口屯田的特點之一,就是重視興修水利,把疏浚河道、興建陂塘等放在屯田的優先位置。
討虜渠。魏文帝黃初六年(225年)三月,“行幸召陵,通討虜渠。”[2]84《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七載:“討虜渠,在縣東五十里。曹魏黃初六年行幸召陵,通討虜渠,謀伐吳也。”[1]2191三國時代的郾城縣,在今河南郾城縣西南,漯河市以西。此渠溝通汝水、潁河,既有利于調節潁河水流,又較方便地將南陽地區的糧食從汝水通過討虜渠送達潁水,然后由潁水順流而下送至壽春(今安徽壽縣),最后轉運至合肥、廬江一帶對吳作戰的前線。
賈侯渠。魏文帝時豫州刺史賈逵所修,“外修軍旅,內治民事,遏鄢、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溪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余里,所謂賈侯渠者也。”[2]482賈侯渠長二百余里,溝通潁河和洧水,“賈侯渠所在的地理位置可以確定為西起今河南西華縣,東至今河南淮陽縣北,是一條呈東西向的運河。”[9]377
百尺渠。又名百尺溝、八丈溝。《水經注》卷二十二《渠·沙水》記載:“沙水又東而南屈,徑陳城東,謂之百尺溝,又南分為二水,新溝水出焉。……又東南注于潁,謂之交口。水次有大堰,即古百尺堰也。”[10]535-536譚其驤先生在《中國歷史地圖集》中提道:“在今河南沈丘標有百尺堰,與《水經注》所記載的廣漕渠位置一致。”[11]7-8
2.組織士兵屯田。正始元年(240年),鄧艾受命巡行陳、蔡,著有《濟河論》,他認為:“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佂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于西,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2]775-776
正始三年(242年),司馬懿“奏穿廣漕渠,引河入汴,溉東南諸陂,始大佃于淮北。”[8]14廣漕渠在今淮陽縣,是蒗蕩渠的一部分,是對蒗蕩渠的中段的修治。據《水經注》卷二十二《渠·沙水》記載:“沙水又南與廣漕渠合,上承龐官陂,云鄧艾所開也。”[10]535《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七《河南二·陳州》賈侯渠條下載:“又州南有廣漕渠,《水經注》以為鄧艾所開。”[1]2177《中國方志叢書·淮陽縣志》也記載:“廣漕渠,在城南,鄧艾所開。”[12]110
正始四年(243年),司馬懿命鄧艾“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于潁南、潁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8]785
今周口市有大量以“營”為通名的村莊。項城181個,淮陽51個,沈丘192個,商水91個,西華81個。調查發現,這些以“營”為通名的村落來源有三:一是和歷代駐軍有關;二是和曹魏屯田有關,商水、項城、沈丘、西華等軍屯發達的地區,以“營”為通名的村莊較多,項城、沈丘以“營”為通名的村莊占村莊總數的10%左右;三是與其他特殊原因有關。
總之,在曹操死后,曹丕及其繼任者繼續貫徹執行了曹操制定的“修耕植,蓄軍資”[2]374的國策,十分重視屯田積谷和改善水運條件,形成了以蒗蕩渠為骨干,溝通淮河北岸各支流的水運交通網。
二、曹魏屯田與周口社會經濟發展
王夫之說:“曹孟德始屯田許昌,而北制袁紹,南折劉表;鄧艾再屯田陳、項、壽春,而終以吞吳;此魏、晉平天下之本圖也”。[13]21曹魏對潁河流域的屯田,為國家積累了大量糧食,奠定了對吳軍事斗爭的物質基礎。屯田使潁河流域的水田空前發展,對周口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
(一)疏通河道,興修水利工程,減少了自然災害,改善了農業生產條件
先秦時期,周口農田和林地尚未大規模開墾,自然災害相對較少。秦漢時期,由于墾荒耕地數量增加,一定程度上破壞了生態平衡,致使水土流失嚴重,土地肥力下降,自然災害頻發。結合《史記》《漢書》《后漢書》《資治通鑒》的記述,兩漢時期潁河流域河水不斷決口,水災較多,淹沒農舍,甚至“壞鄉聚民舍,及水流殺人”。
水害嚴重。前186年、前185年,淮陽、西華、扶溝、太康連續兩年大水,淹沒民舍800余家。前86年,淮陽、西華、沈丘、項城大雨水。前73年,“霪雨,壞官民舍”。前39年,淮陽、太康、沈丘、項城大水,水流殺人。前32年,淮陽、扶溝、太康、沈丘大水。21年,淮陽大水60日。65年,淮陽、扶溝、沈丘、項城大水。
河水決堤,泛濫成災。前185年,汝水溢入潁,淮陽大水。前177年,黃河決口,淮陽、西華、扶溝、太康大水。前130年黃河溢,淮陽大水成災;前7年,沈丘大水,潁河溢。1年,“河汴決壞,黃河間有南侵之害”,許多年后水患才得到遏制;23年,沙潁河大水。58年,西華、太康、沈丘河溢。65年,洧水泛濫,危及周口多縣。89年,太康河溢,漂害民眾。106年,洧水盛漲,西華、淮陽傷稼。
商水縣境內地勢低洼,湖陂星羅,坡洼棋布,有“五湖十八陂”之稱,大雨大災,小雨小災,無雨旱災,鄧艾在此屯田,將湖陂水引入河道,縣境內西部洼地積水就開渠多道入潁水東流,縣境東部洼地積水也開渠多道入溵水(今汝河)匯入淮水。今鄧城東的飲馬臺、灌溉渠,都是當年鄧艾所開。
周口市川匯區有“溉灌城”。《元和郡縣圖志》卷八《河南道四·陳州》溵水縣(今商水縣南)條云:“溉灌城,縣東北二十五里。本魏將鄧艾所筑。艾為典農使,行陳、潁之間,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盡地利,遂開筑陂塘,大興溉灌,軍儲豐足,因名此城。”[14]214溉灌城就是今周口市川匯區的水灌臺遺址,原名為觀水臺,傳說大禹治理水患,曾在此筑臺觀水象。
西華縣有鄧門陂。《讀史方輿紀要》記載:“鄧門陂,在縣西。唐神龍中縣令張余慶因廢陂復開,引潁水溉田,蓋以鄧艾故址而名。”[1]2180艾成河當時也是一條鄧艾修建的引潁河支流灌溉的工程。該渠自許昌東秋湖分流,經臨潁縣東北,然后折向東南,延伸到西華縣境內。
由于曹魏時期重視河道疏浚,自然災害相對較少,三國時期周口沒有發生大的河水泛濫,水災明顯減少,整個晉代150多年周口也只有1次河水泛濫。于鵬飛說:“三國時期,由于局部地區實現了統一,加之統治集團注意社會經濟的恢復與發展,故自然災害比起東漢末年來說,大大減少了。”[15]97
(二)屯田大量種植水稻,促進了農作物品種多樣化,改變了農業耕作方式
周口地勢平坦,土壤疏松肥沃,氣候溫暖濕潤,境內河流縱橫交錯,擁有發展農業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自夏商周以來,周口一直是重要的農業生產區域,粟、黍、稷、梁、秫一直是這一區域最主要的糧食作物。
水稻在潁河流域的種植始于殷商時期,歷經西周、春秋、戰國、秦漢。盡管潁河平原并沒有廣泛種植水稻的條件,但由于“谷中之美莫過稻”,稻米為上層社會所鐘愛,因而從東漢開始推廣種植水稻。東漢末到三國初年,周口人口驟減,土地荒蕪,人地矛盾得到緩解,這就為水田的開辟,水稻的廣泛種植提供了條件。
鄧艾在沈丘屯田種植水稻。“司馬宣王使鄧艾于此屯田種稻,以備東南。”①王炳慶:《三國后期鄧艾屯田開渠考略》,《東南學術》,1999年第3期,第112-113頁。《讀史方輿紀要》記載(陳)世修言:“陳州項城縣界蔡河東岸有八丈溝,或斷或續,迤邐東去,由潁及壽,綿亙三百五十余里。乞因故道浚治,興復大江、次河、射虎、流龍、百尺等陂塘灌溉,數百里內復為稻田。”[1]2176西華縣有種植水稻的記錄,《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七《河南二·西華縣》記載:“城側有陂,魏鄧艾營稻陂時柳舒為陂長,后人因目為柳城。”[1]2180高敏先生說:“建安元年的許昌屯田,以后淮水、潁水南北一帶的屯田,沁水流域的屯田等都是水稻田。”[16]117
由于水稻的大量種植,人們開渠、筑塘,既用水灌溉,也用水畛草。耕作方式的變化,使水稻產量得以迅速提高,晉人傅玄說:“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旱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數十斛。”[8]1321
金家年說:“鄧艾在兩淮間屯田為五萬人,按百分之二十的比例安排輪休,常年出勤的實際勞力只有四萬人,而耕種二萬頃土地,平均每個勞力承擔五十畝,同漢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趙充國上屯田奏所說的每人分耕三十畝土地相比較,實際提高勞動效率40%。……可見,曹魏軍屯每個勞力的實際勞動效率比起原有自耕農的水準提高了百分之三十。這說明,在當時是適合生產力發展水準的,有著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17]86
(三)新運道的開辟,奠定了周口中原水運中心的地位
周口最早的運河可以追溯到西周周穆王時期的陳蔡運河。戰國時期有魏國溝通黃河、淮河的鴻溝運河。三國時期,曹魏為了運兵、運糧和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在黃河、淮河之間,開鑿和整治了多條運河,形成了以蒗蕩渠為骨干,溝通淮河北岸各支流的水運交通網。
沿潁河東向,可以直達合肥。黃初五年(224年),“秋七月,行東巡,幸許昌宮。八月,為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幸壽春。”[2]84
由潁河入渦水,入譙梁運道,可以達至淮河。譙梁運道,起于譙郡(安徽亳州),止于石梁(安徽天長)。建安“十四年(209年)春三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2]32
由潁河向西可達許昌和南陽。曹丕遷都洛陽以后,許昌是南征孫吳的后方軍事重鎮。周口泛舟而上,西至許昌;轉汝水可達南陽;經洧水,可達新鄭、嵩山。
由潁河向北可達開封和洛陽。由潁河在沈丘入百尺堰,過淮陽,經廣漕渠,西北經浚儀(河南開封市),向西經圃田澤,達滎口入黃河,沿黃河西行,達洛陽。
曹魏在周口大力興修渠道,利用汝、潁、洧、沙四水,形成四通八達的運河網,大大提升了周口中原地區水運、轉運中心的地位。
(四)促進了潁河沿岸小集市的發展
隨著中原社會經濟的恢復,水運的發達,周口出現了多個駐兵、屯糧和商品交易的中心。
鄧城,位于商水縣城西北16公里的鄧城鎮,毗鄰沙河,北與西華縣隔沙河相望。《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七《河南二·汝陽城》記載:“魏正元中兗州刺史鄧艾擊毋丘儉于項城,進至樂嘉,作浮橋于潁水上以待司馬師。師遂自汝陽潛兵就艾于樂嘉是也。志云:今縣北有鄧城,蓋鄧艾屯田時所筑者。”[1]2178鄧城從三國時期開始,由于毗鄰沙潁河,位置重要,是兵家必爭之地。
柳城,三國時有南北柳城。《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七《河南二·西華縣》記載:“城側有陂,魏鄧艾營稻陂時柳舒為陂長,后人因目為柳城。志云:今縣東北十五里有北柳城,縣東南三十里有南柳城,皆以柳舒為名。”[1]2180南柳城位于西華縣西南17公里的葉埠口鄉,四周皆有城墻,城內南高北低,東南隅建有柳城寺廟,遺跡至上世紀七十年代尚在。經考古鉆探,該墻為夯筑而成,城址內發現石箭頭、銅箭頭、漢代陶片、銅鏡、錢幣、石印、建筑構件等,在城西發現有漢代墓群,西北是屯兵馴馬場,和史書記載相符。
集糧城,位于今西華縣城西北6公里紅花鎮護當城村。《元和郡縣志》卷八《河南道四·陳州》西華縣條載:“集糧城,在縣西十里。魏使鄧艾營田,筑之貯糧,故名。”[14]215相傳城上原有涼亭,為鄧艾夏季乘涼之所。村南有涼馬臺,是鄧艾操練兵馬的地方。
沈丘縣的磚城,也是鄧艾屯田所筑的儲糧城。《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七《河南二·沈丘縣》記載:“又磚城在縣東北四十五里,魏鄧艾屯田置戍處也。今城址猶存。”[1]2182
這些新興的儲糧城,緊鄰水運航道,交通便利,既是屯田的糧倉,又是駐軍要地,還是區域商品交易的中心。這些小集市的出現與發展,對促進潁河流域經濟發展,尤其是當地商業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綜上所述,曹魏周口屯田,解決了當時嚴重的糧食問題,安置了降卒和流民,穩定了社會秩序,促進了潁河流域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曹魏屯田留下了大量的歷史遺跡,是寶貴的歷史文化資源,在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應該注意保護。
[1]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M].北京:中華書局,2005.
[2]陳壽.三國志[M].北京:中華書局,1959.
[3]司馬光.資治通鑒[M].北京:中華書局,1956.
[4]陳家麟.曹魏屯田的幾個歷史地理問題[J].汕頭大學學報,1987(4).
[5]西華縣地方志編篡委員會.西華縣志[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6]中國方志叢書·西華縣續志[M].臺北:成文出版社1934.
[7]劉靜夫.中國魏晉南北朝經濟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8]房玄齡.晉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9]嵇果煌.中國三千年運河史[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8.
[10]酈道元.水經注校證[M].北京:中華書局,2007.
[11]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M].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0.
[12]中國方志叢書·淮陽縣志[M].臺北:成文出版社1934.
[13]王夫之.讀通鑒論[M].北京:中華書局,2013.
[14]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M].北京:中華書局,1983.
[15]于鵬飛.三國經濟史[M].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
[16]高敏.秦漢魏晉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
[17]金家年.論曹魏江淮屯田與水利建設[J].安徽大學學報,19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