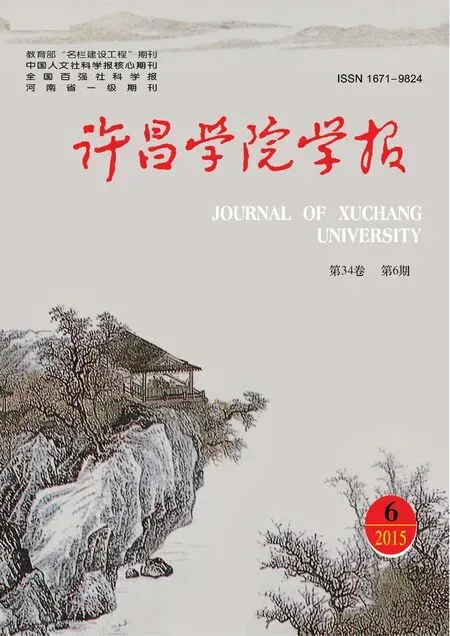《文心雕龍》關于南北文學的差異
杜鵬飛
(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遼寧大連116081)
在《文心雕龍》中,劉勰雖并未明確提出南方文學、北方文學這樣的字眼,但詞句之中已然涉及,而且對于其形成的原因業已給予答案。后世的魏征在《隋書·文學傳序》中提出:“江左宮商發越,貴乎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1]183這段文字是唐人對于前世文風特點及其弊病做出的較為理性的總結。本文擬從南北文學差異方面對其作一淺談。
一、多方合力,南北差異
(一)萬物紛紜對南北文人心理的觸動
《文心雕龍·物色》里說:“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2]222春秋季節不同,風景不同,對人心的觸動自然也是有差異的,加上當時的文人心理不同,所以,“情以物遷,辭以情發”,形成文字之后體現的文風自然不同。
同樣,即便在同一個季節,中國版圖博大,南北風景在同一個季節的表現也會有較大差異。當北方萬物凋零,古道西風之時,南方可能仍然是柳暗花明,煙雨畫橋。當北方剛剛春花爛漫遍山野之時,南方可能已是赤日炎炎似火燒。所以,在心為志,發言為聲,“氣之動物,物之動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鐘嶸《詩品》序),正是南北方不同的物色之動,才引起了文人們或輕或重,或淺或深,或急或緩的心理觸動,形成了文學上或慷慨激昂,或深沉溫婉的文風。故而《物色》中發總結性之句:“屈平所以能洞見《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2]225亦強調了“江山之助”,居功甚偉。
(二)南北文人先天稟賦及后天學習的影響
《文心雕龍·體性》篇說:“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正。”[2]136高才八斗之人除了天資聰穎之外,還在于后天不斷的汲取,而且,一定程度上,后天所接受的教育和熏陶甚至比先天稟賦更為重要些,否則,即便天賦再高,亦必如仲永般泯然眾人矣。
先天稟賦之才有高下之分,內在氣質有剛柔之別。通過學習之后,形成的風格有淺薄和深厚,高雅和淫靡。比如:“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靜;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2]137“叔夜俊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2]138所以賈誼,司馬相如,嵇康,潘岳四個人不同的文風皆是由于其個人情性不同所致。
“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個性歸個性,人能隨心所欲,追逐自己的心不失為一種放達,一種灑脫。嵇康和阮籍為竹林七賢的核心成員,二人同樣以張揚個性,任性自由為傲,同司馬氏不合作,即使面臨被殺危險亦毫不變改,尤其是嵇康,臨決之際,撫畢《廣陵散》,慷慨赴死,作為一代文人,其品行如此,所以我們能夠在其作品中看出一種不羈放縱,遺落世事的高潔。這也是劉勰論及的個人對文風的影響的表現之一。
另外,文學批評家們總是會對文人的作品要求過高,殊不知,文人也是人,不可能寫任何東西都考慮世人的眼光,也不可能任何作品都盡善盡美,因此,劉勰提出,任何文風都應該被給予理解和尊重,“人稟五材,修短殊用……難以求備”,[2]243齊梁之際的劉勰能夠拋開偏見認識到這一點是很難能可貴的,因為但凡批評家們在這方面總是以己度人。這樣一來勢必造成“將相以位隆特達,文人以職卑多誚”的不正之風。劉勰在此提出的觀點是很能警醒世人的。
的確,作為一介文人,風格不同,有瑕疵,這本無可厚非,文壇應該允許各種各樣的作品百花齊放,異彩紛呈,而不應該對個人求全責備。“慷慨者逆聲而擊節,蘊藉者見密而高蹈”,所謂個人風格,即是個人志趣、學識和修養在作品中的自然流露,一般人特別擅長或喜歡與自己性格相符的文風。而較為排斥或者不擅長另一種文風,北人雅好慷慨,南人性喜細膩溫婉,其實這并無優劣之別,都應該予以寬容。
(三)南北君王愛好引起舉國跟風
一種文風的盛行,除了個人因素外,君王的愛好無疑也是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引起一代甚至幾代的文人競相效仿,經久不衰。
“高祖尚武,戲儒簡學……施及孝惠,迄于文景,經術頗興……逮孝武崇儒,辭藻競騖”。[2]213漢高祖,孝惠帝,文帝,景帝,他們的個人喜好無疑影響了當時文人的命運和文風的嬗變,到了三國時期,“魏武……雅愛詩章;文帝……妙善辭賦”。[2]216
“至明帝纂戎……何劉群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嵇阮應繆,并馳文路矣”。[2]216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一變往日文風,將北方文學特有的慷慨悲涼蘊于詩篇、辭賦,由此發起了鄴下文人集團集體創作,一時文風蔚然興盛。到了明帝,仍舊自己寫詩作曲,文人們文采飛揚,交相輝映,隨著以后的年輕皇帝們高蹈于歷史舞臺,其時文風逐漸流于輕浮。
所以,君王作為一國國主,其喜好必然會引起上行下效的連鎖反應,文人們為求進身之階而應酬也好,逢迎獻媚也罷,總之,能引起一定范圍一定時間內的總體文風嬗變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具體在空間范圍內,南北文風也勢必迥然。
(四)社會動蕩及時代變遷
不管南方北方,不論任何一種文學形式,《文心雕龍》里明確指出,“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這話說得很明白,隨著時代變遷、朝代更迭,文學上的表現隨之而變,“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2]218就如這玄學興盛之際,詩歌也好,辭賦也罷,必定以老莊為本。
究其根源,魏晉之際,戰爭連綿不斷,民不聊生,流民四起,“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當此之時,大部分文人們為了活著,親附于達官貴人的文學集團,除了一方面避免被餓死的災厄,還要疲于應對政治斗爭,站錯隊、說錯話隨時都有可能淪為犧牲品。另外的一部分文人選擇歸隱山林的方式,整日縱酒昏酣,遺落世事,其詩作大抵玄學、自然,與政治無涉。
“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文心雕龍·定勢》
“漢室迄今,辭務日新,爭光鬻采,慮亦竭矣。”——《文心雕龍·養氣》
所謂近代,當然是指晉、宋這個時候的文風。自沈約為四聲之后,對于格律、平仄的講究和字詞錘煉近乎瘋狂,寫詩作文極盡繁華之能事,下筆吟詠務求靡麗之音響。但是繁華靡麗之后卻是掩蓋不了的虛空,有文無質,空馳其采。這樣一來的結果就是南朝上下,偏重虛浮,不重實事,文風亦“務華棄實”,這同北方梗概多氣,慷慨悲涼的骨直之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且這在文學發展過程中是偏離軌道的,是一種畸形發展的態勢。因此,劉勰進一步提出了注重感情,注重內容,注重骨氣的創作主張。
二、文質并重,南北融合
劉勰在闡述了南北方文化差異以及文學風格的不同之余,進一步提出了解決南朝浮華文風問題的方案,也強調這是真的文學本應達到的文學標準,即把內容和形式統一起來,做到既有文采又有充實的感情充沛其中,這樣的文章才不至于使人感覺繁采寡情,不至于味之則厭。
除了之前所述的唐代魏征在《隋書·文學傳序》中對南北文學所作的總結,主張“文質彬彬,盡善盡美”,這在文學史上被稱為首次倡導融南北文風,各取其長。其實隋代的李諤在《上隋高帝革文華書》針對齊梁的文華藻飾,指出:“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1]182但是隋代采取的是政治手腕,并未從根本上動搖浮華的基礎,收效甚微。盛唐的殷燔在《河岳英靈集》里說:“文質半取,風騷兩挾,言氣骨則建安為傳,論宮商則太康不逮。”[3]108追溯前朝,劉勰雖并未明確提出融合南北、各取所長的主張,然而細細考據其《文心雕龍》,我們會發現,其實劉勰已經告訴世人,什么是對的,應該怎么做,這一點,劉勰有著超越時代的警醒和客觀。
主張風骨和興寄的陳子昂其實對劉勰的思想理解有著繼承的關系,在《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說:“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1]191-192這段話可謂是對《文心雕龍·風骨》篇的繼承和闡釋。當然,除了《風骨》,在《體性》《情采》里皆有闡發。
(一)因性練才,雕琢成器
不論是擁有著高俊大山和四季分明的北方,還是小橋流水、微雨杏花的南方,孕育的文人及其風格雖大體而言南溫婉、北慷慨,然并非絕對的,關鍵在于后天學習及其周遭環境的變化。
比如庾信,居南朝時多宮體香艷之風,然而一旦北遷,本有大才,加之思鄉之情,再調和以北地特有的自然景物的蕭瑟,多力合作,終于將其文風大變,其情躍然紙上,故而杜甫大贊:“庾信文章老更成”。再如劉勰本身,身處南方,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南人,居于鎮江,理論上來說其文應該帶有很濃重的南風,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原因在于劉勰閱讀了大量的書籍,經史子集非常精通,加之協助僧祐整理佛經,逐漸形成了劉勰自己獨特的取南北之長的文學風格。在《體性》篇中,“夫才有天資,學慎始習……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討葉,思轉自圓……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2]138所以,根據自己的性情來不斷學習,確定某一風格為自己的方向,使才能得以充分施展。并且要做到“辭為肌膚,志實骨髓”。
(二)蔚彼風力,嚴此骨鯁
何謂風骨?文章缺乏風骨會怎樣?“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征也;思不環周,索莫乏氣,則無風之驗也”。[2]141簡單來說,“風”是指文章整體流露的精神狀態,“骨”是指言辭之中蘊含的勁健之氣。只有深諳風骨,才能使文章呈現出與常人不同的氣勢。因此“昔潘勖錫魏,思摹經典,群才韜筆,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賦仙,氣號凌云,蔚為辭宗,乃其風力遒也”。[2]141
在寫作中經常會出現風骨不諧,此起彼伏、此消彼長的現象,比如:“夫翚翟備色,而翾翥百步,肌豐而力沉也;鷹隼乏采,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2]142針對這種情況,劉勰認為,應該“熔鑄經典之范,翔集子史之術”“確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則風清骨峻,篇體光華 ”。[2]142這樣一來,所謂的南北文學差異,只要沿此方向執行下去,必然可以大大降低乃至微乎其微。
(三)心術既形,英華乃贍
在整個《文心雕龍》中,從《原道》到《序志》,五十篇之內有大半都談到了“文”,天地山川風云有“文”,虎豹蟲魚鳥亦有“文”,圣賢文章的文采亦是“文”,然而文需要附于質,質需要待文。具體到文章創作上,就是作為文采的文需要和作為情志的質結合起來,二者相映成趣,共同作用才能使一篇文章散發出感人的藝術魅力,此即情采。
“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后緯成,理定而后辭暢”。[2]153寫文章,是為情志服務的工具和途徑,不能為了寫文章去造情,具有好的情志,才能寫出優秀的作品。南朝文學崇尚輕艷香軟的宮體文學雖然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文辭的錘煉,但是嚴重背離了文學發展的軌道,摒棄風雅,隔絕興寄,毫無情志灌輸其中,屬于文學的細枝末流。所以,劉勰主張,摒棄文質不諧,采濫辭詭的文學形式,反對“言隱于榮華”,提倡“文不滅質,博不溺心”。[2]153
所以,豐富的情思與華麗的辭藻有機結合才能煥發文章的光彩,這才是經國大業,不朽盛事所核準的文章類型,絕非南朝宮體之流。所以,欲要文章千古流芳,當然要“心術既形,英華乃贍”,即情感豐富,辭藻充足。
總之,南方文學和北方文學的差異體現在諸多方面,劉勰身處彩麗競繁的時代能夠以超然的眼光看待這種差異性,并且以一種超越時代的敏銳直覺提出文學形式和內容的關系及其融合理論,這一點即便在今天依然適用。因此,反思文囿,綜觀南北,透視古今,劉勰文藝思想的超然性和預見性都是作為文學學習者和批評家應該學習和敬仰的。
[1]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劉勰.文心雕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傅璇琮.唐人選唐詩新編[M].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