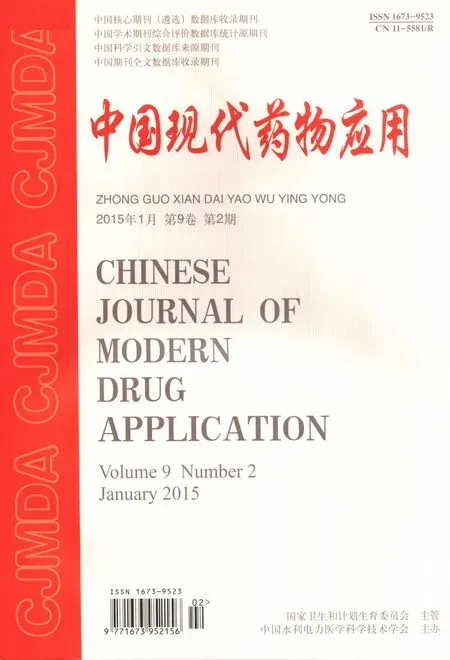頸動脈內膜剝脫術與支架置入術的臨床分析
楊強 郭放
頸動脈內膜剝脫術與支架置入術的臨床分析
楊強 郭放
目的對頸動脈內膜剝脫術與支架置入術的療效及安全性進行分析。方法86例頸動脈狹窄患者, 根據治療方法不同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 其中對照組42例給予頸動脈內膜剝脫術治療, 觀察組44例給予頸動脈支架植入術治療, 對比兩組治療效果及并發癥發生率。結果兩組圍術期并發癥發生率、術后3個月心肌梗死、腦卒中及死亡等主要終點事件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經1年隨訪, 兩組術后1年再狹窄及致殘或致死性卒中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結論在頸動脈狹窄治療中頸動脈內膜剝脫術與支架置入術具有相當的臨床療效, 且安全性均較高。
頸動脈狹窄;頸動脈內膜剝脫術;支架置入術
頸動脈內膜剝脫術與支架置入術是目前臨床應用最為廣泛的中重度頸動脈狹窄患者的血管治療措施[1,2], 為對這兩種方法的臨床療效及應用安全性進行分析, 作者選取86例分別采用這兩種方法治療的頸動脈狹窄患者, 對其手術并發癥及隨訪情況展開分析, 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北京宣武醫院及鄭州頤和醫院2012年7月~2013年9月收治的頸動脈狹窄患者86例, 根據治療方法不同分為兩組, 對照組42例, 男26例, 女16例, 年齡52~75歲, 平均年齡(68.6±3.5)歲;其中左側19例, 右側23例;頸動脈狹窄程度68%~96%, 平均(75.0±3.6)%;觀察組44例,男27例, 女17例, 年齡51~73歲, 平均年齡(67.4±3.7)歲;其中左側20例, 右側24例;頸動脈狹窄程度65%~93%, 平均(72.0±3.8)%;兩組患者均有短暫性腦缺血發作及缺血性腦梗死臨床癥狀, 且兩組患者年齡、性別、病情等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所有患者術前均經頭顱CT及MRI(DWI序列)檢查排除顱內出血及新鮮梗死, 且術前完善凝血功能、血生化、血常規、心肺功能等檢查與心電圖、胸片等輔助檢查, 行全腦血管造影與頸部血管彩超檢查, 在術前3 d給予100 mg/d阿司匹林口服治療。對照組行頸動脈內膜剝脫術:行氣管插管全身麻醉, 在胸鎖乳突肌的前緣做一直切口, 手術全程持續利用經顱多普勒監測對側支循環的代償情況予以判斷;患者經顱內動脈阻斷之后, 大腦內動脈血流速度有60%以上下降, 用轉流管。在阻斷頸內動脈前5 min給予患者4000 U肝素靜脈注射以避免血栓形成, 臨時阻斷頸外動脈分支、頸內動脈及頸總動脈后將頸動脈前壁切口, 促使斑塊顯露, 順頸內動脈內膜利用顯微剝離子將斑塊整塊剝除, 之后對內膜創面殘片予以仔細清除, 如果在頸內動脈遠端有內膜剝離,利用5-0絲線進行縫合固定。對于頸內動脈遠端極為細小的患者應給予頸動脈補片擴大修補。所有患者術后終身需服用100 mg/d阿司匹林腸溶片。觀察組患者行頸動脈支架置入術:術前3 d給予患者75 mg/d氯吡格雷及100 mg/d阿司匹林口服行抗血小板治療。在局部麻醉后在患者頸部頸內動脈比較直且未發生病變的地方放置遠端保護裝置, 且應與頸動脈巖段接近, 保護裝置近端應保持和頸動脈病變遠端相距3~4 cm以上。在手術中常需對患者病變處行預擴張, 從而便于放置支架, 預擴張采用冠狀動脈球囊(直徑為4.0~5.0 mm)進行。按照造影結果選取直徑比治療血管最大處多出1~2 mm的支架, 確保支架可將病變區域完全覆蓋。對于殘余狹窄不足20%的患者可采用球囊支架內后擴張, 所用支架為自膨式鎳鈦合金支架。在手術過程中給予患者持續肝素化, 完成手術后給予300 mg/d阿司匹林與75 mg/d氯吡格雷,3個月后終身服用100 mg/d阿司匹林腸溶片。
1.3 觀察指標 在術后3個月對兩組患者主要終點事件發生情況進行觀察, 主要終點事件包括腦卒中、心肌梗死、死亡等[3], 統計兩組患者圍術期并發癥發生情況, 在1年隨訪時記錄兩組患者再狹窄率及致殘或致死性卒中發生情況。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統計學軟件SPSS17.0分析研究數據。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 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檢驗。P<0.05表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圍術期并發癥發生情況 對照組圍術期并發癥發生率為16.7%, 觀察組圍術期并發癥發生率為18.2%, 兩組圍術期并發癥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2 兩組患者術后3個月主要終點事件發生情況 兩組患者術后3個月心肌梗死、腦卒中及死亡等主要終點事件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1 兩組并發癥發生情況分析 [n, n(%)]

表2 兩組患者術后3個月主要終點事件發生情況分析[n(%)]
2.3 兩組患者隨訪1年期間再狹窄率及致殘或致死性卒中發生情況 在1年隨訪期間對照組再狹窄3例(7.1%), 致殘或致死性卒中2例(4.8%);觀察組再狹窄2例(4.5%), 致殘或致死性卒中2例(4.5%);兩組術后1年再狹窄及致殘或致死性卒中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3 討論
現階段腦卒中已成為成年人殘疾的首要致病因素, 同時其致死率在所有疾病中占據第三位(僅低于心血管疾病與腫瘤), 頸動脈狹窄是造成缺血性腦卒中的最主要原因。現階段頸動脈狹窄主要有頸動脈支架術、頸動脈內膜剝脫術及內科藥物治療等三種治療方案, 其中內膜剝脫術素有頸動脈狹窄外科治療“金標準”之稱, 然而患者在圍術期常有局部血腫、感染及神經損傷等并發癥, 故而該術式并不完美。近年來有研究人員提出, 頸動脈支架置入術在頸動脈狹窄治療中安全性更高, 可取代內膜剝脫術成為頸動脈狹窄外科治療的常用術式[4]。
為對頸動脈內膜剝脫術與支架置入術的臨床療效及安全性進行分析, 作者選取44例行頸動脈內膜剝脫術治療的頸動脈狹窄患者與42例行頸動脈支架置入術治療的頸動脈狹窄患者, 對其圍術期并發癥及3個月主要終點事件發生情況進行分析, 同時展開1年隨訪觀察患者治療效果。經分析, 兩組患者圍術期并發癥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這和國內已有研究[5]結果一致。由于這兩種術式的治療路徑有所不同, 故而其局部并發癥的種類并不相同。本次研究結果顯示, 頸動脈內膜剝脫術圍術期并發癥中神經損傷所占比例比較高, 這是因為該術式常會給患者造成較大創傷, 術中組織分離較多, 很容易造成神經損傷, 而支架植入術并未出現神經損傷并發癥, 說明支架置入術具有不會造成神經損傷的優勢。頸動脈支架置入術圍術期并發癥最常見的是高灌注綜合征, 高灌注綜合征多發生于血管重建手術之后的短時間中, 患者主要有惡心、嘔吐、頭脹及頭痛等并發癥, 部分患者可出現意識障礙, 嚴重者可出現同側顱內出血。高灌注綜合征發生機制為:頸動脈狹窄造成顱內低灌注區域中小動脈長時間保持代償性擴張這一狀態, 患者血管的自動調節能力降低, 在重建血運后血管床并不能與已增高灌注壓相適應,局部腦血液灌注明顯比代謝需求更高, 故而更容易出現腦組織腫脹, 甚至部分患者可發生出血。因此, 在為頸動脈狹窄患者展開支架置入術治療時應對患者血壓予以嚴格控制, 對高灌注所致再灌注損傷予以有效預防。
本次研究通過對兩組患者術后3個月主要終點事件發生情況進行分析, 發現術后3個月心肌梗死、腦卒中及死亡等主要終點事件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經1年隨訪, 兩組術后1年再狹窄及致殘或致死性卒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從這一結果可以看出, 在頸動脈狹窄治療中支架置入術的治療效果并不亞于頸動脈內膜剝脫術, 兩種術式在對頸動脈血供予以改善、對卒中加以預防中均有顯著的效果。因為支架置入術操作更為簡單且為微創手術, 故而近年來其在臨床中的應用更為廣泛, 甚至已逐漸取代頸動脈內膜剝脫術。另外, 支架置入術的適應證更為廣泛, 對于無法耐受內膜剝脫術的患者或高齡患者而言, 支架置入術的應用具有更為明顯的優勢。
[1]刁永鵬, 劉昌偉, 宋小軍, 等.兩種頸動脈內膜剝脫術式治療頸動脈狹窄的臨床分析.中國醫學科學院學報,2014,36(2):131-134.
[2]衛志慶, 楊其鵬, 黃佃, 等.頸動脈內膜剝脫術及頸動脈支架置入術治療顱外頸動脈硬化狹窄術后早期并發癥比較.中國修復重建外科雜志,2011,25(3):337-340.
[3]喬彤, 劉長建, 黃佃, 等.動脈內膜剝脫術治療頸動脈狹窄179例臨床分析.中國實用外科雜志,2012,32(8):659-661.
[4]陳莉, 秦超, 莫雪安, 等.頸動脈內膜剝脫術與頸動脈支架術的療效及安全性的比較.中風與神經疾病雜志,2014,31(1):29-31.
[5]包文, 段永亮, 管圣, 等.血管補片成形對頸動脈內膜剝脫術后再狹窄的預防作用.中華普通外科雜志,2014,29(1):67-68.
10.14164/j.cnki.cn11-5581/r.2015.02.020
2014-10-29]
450047 河南省鄭州人民醫院頤和醫院神經外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