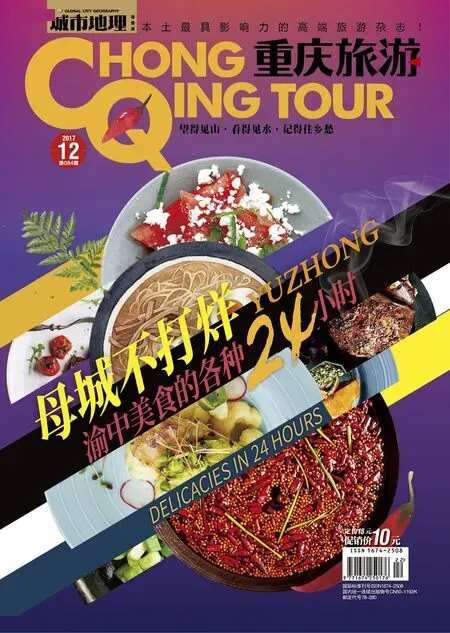讀本尼德克特《菊與刀》
劉 博
(沈陽師范大學社會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1)
讀本尼德克特《菊與刀》
劉 博
(沈陽師范大學社會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1)
本尼迪克特認為,人類文化是由各自相對不同的價值秩序制約著,呈現多樣性,從文化的內部給這些多樣性定性的東西,是那個文化的主旋律,文化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模式,就是因為文化有它的主旋律。
文化模式;文化;差異性
引言
《菊與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 (1887-1948)是美國當代著名的文化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認為,人類文化是由各自相對不同的價值秩序制約著,呈現多樣性,從文化的內部給這些多樣性定性的東西,是那個文化的主旋律,文化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模式,就是因為文化有它的主旋律1。根據本尼迪克特的思路,我們來了解下《菊與刀》這本書中所寫的日本文化。
一、作者一次都未到過日本,卻搜集了日本大量的事實,這些事實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依靠描寫這些事實,寫出了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的全景。“菊花”是日本天皇家族的象征,“刀”是日本武士身份的象征,可見“天皇制”和“武士道”精神在日本文化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同時也代表著日本文化雙重性和日本人的矛盾性格。“研究課題——日本”,1944年6月,作者奉命研究日本,為政府寫一篇報告。作者在第一章論述到:不同文化的差異性和探索比較這些差異性的方法和意義。若用一句話概括就是“戴上日本人的眼鏡”觀察事物,才能對他們看似矛盾的意識和行為有“原來如此”的理解。“戰時的日本人”,戰爭中的日本人認為,只要各國擁有絕對主權,世界上的無政府狀態就不會結束,日本必須為建立等級秩序而戰斗。當然,這一秩序的領導只能是日本,只有日本人才能真正領悟“各得其所”的要領,只有日本才是唯一的真正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級制的國家。戰爭中日本人信奉的是精神至上、不怕犧牲、忠誠天皇的宗旨與美國的那種信賴物質、贊賞救援的行為大不相同。“明治維新”。宣告近代日本到來的戰斗口號是“尊王攘夷”。1868年,倒幕勢力取得勝利,宣告王政復古,“雙重統治”的結束,新政府一上臺就取消了大名在各藩的征稅權,但是這種權利剝奪不是無償的,政府會發給每個大名相當其收入一半左右的俸祿,武士也是這樣;以后的五年,又從法律上廢除了等級間的不平等;還解放了賤民,廢除了禁止土地轉讓的法令。新生的明治政府這些重大的改革是不得人心的,在明治最初的十年間,至少爆發了190起農民起義。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經常考慮到等級制,在家庭以及人際關系中,年齡、輩分、性別、階級決定著適當的行為。明治維新雖然破壞了舊秩序、建立了新秩序,但這種新秩序在政治、宗教、軍隊、產業等各個領域中,都有十分周到的等級劃分。
二、“欠歷史和社會的恩情”,在日本歷史中,一個人一生中最大的恩主就是他那個生活圈中的最高上級,這個人物隨時代在變化,曾經是各地的地頭、封建領主或將軍、現在是天皇。這種“不忘恩情”的習性,在日本人生活中占有最高地位。“報恩與萬一”,在日本對“恩”是債務,必須償還這一概念不同,對日本人來講,一旦接受恩情,是永久存在的債務,“報恩”是積極的,刻不容緩的償還,使用另一系列概念來表達的。“情理難卻”,日本人常說,“情義最為難”。一個人必須報答“情義”,它就像義務一樣,必須報答。 “情義”的范圍包括對姻親家屬應負的一切義務,“義務”的范圍是包括對直接家屬應負的一切義務,凡是發自內心的行動都不能說事“情義”。“洗刷污名”,按照日本人的說法,用適當的方法自殺,可以洗刷污名并贏得身后好評。一個自重的日本人必須堅忍和自我控制,關于武士的堅忍,有很多著名的故事,他們必須能夠忍耐饑餓即使餓的要死,也要裝出剛吃過飯的樣子,并用牙簽剔牙。“人情世界”,日本是一個信奉佛教的國家,但他們不會譴責滿足自己的私欲。日本人一方面培養肉體享樂,另一方面又規定不能把享樂當作嚴肅的生活方式而縱情沉溺。日本人允許“人情”的存在即洗熱水澡、睡覺、性、酗酒。“人情”世界是作為對“義務”這種嚴肅世界的解脫而存在的,“義務”與“人情”的世界是相互獨立的,互不相交,體現了日本文化的“各得其所”。“道德的困境”,日本人的文化是恥感文化,他們將知恥看做是德行之本。日本人的人生觀表現在他們忠、孝、情義、仁、人情等德行規定中,他們似乎認為“人的義務的整體”就像在地圖上劃分勢力范圍一樣,由“忠的世界”、“孝的世界”、“情義的世界”、“人的世界”、“人情的世界”及其他許多世界組成,他們致力于將“忠”變成最高道德。在日本“武士”有很強的的羞恥感,在榮譽面前,生命本身是沒有價值的。
三、“自我修養”,日本人認為,無論是誰都必須進行自我修養。日本人的自我修養分為兩類:一類是磨練意志,這種自我修養具有普遍性;另一類是獲得精神感悟,作者稱為“圓熟”,達到“圓熟”的境界,就會消除一切自我監視,消除一切恐懼和戒心,自身的活動力和注意力不收任何約束,可以勇往直前地去實現目標。“兒童學習”,日本人的矛盾性格是從兒童期開始培養的,在日本允許嬰兒和老人有最大的自由和任性,至結婚前后個人自由降低至最低線,并將持續幾十年。想真正了解日本文化就要追根溯源,從日本兒童教育開始才能夠更好的了解。“投降后的日本人”,日本在戰后對美國的態度急速轉變,許多西方學者認為日本戰敗后會在意識形態方面掀起群眾運動,有的夸大了戰爭期間日本地下勢力并指望他們能在投降前夕掌握領導權,但這些情況都沒有發生,而日本的態度則是積極配合。對于日本來說,戰爭與和平不是一個原則問題,而僅僅是兩種為了實現其目的的手段。
結束語
《菊與刀》不僅僅是一份政府研究報告,它作為一本人類學著作,真實生動地描繪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提煉出了日本文化的諸多特征,為我們深入了解日本人奠定了基礎。
[1](美)本尼迪克特著,北塔譯,菊與刀,上海三聯書店,2007.11
[2](日)綾部恒雄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社會文化室譯,文化人類學十五種理論,北京市: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06
注釋:
① (日)綾部恒雄:《文化人類學的十五種理論》。
劉博 (1989.01-),女,沈陽師范大學,人類學研究生,文化人類學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