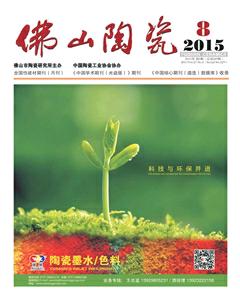淺談紫砂壺作品之竹韻魅力
唐伯琴
(宜興 214221)
1 前言
紫砂是陶瓷藝術中富有特色、最具個性的一類。主要得益于它“五色土”舉世無雙的獨特材質及其精妙入微、巧奪天工的獨特工藝。用以泡茶不失原味,色、香、味皆蘊,紫砂陶是一種介于陶和瓷之間,屬于半燒結的精細炻器,具有特殊的雙氣孔結構,透氣性極佳且不滲漏等特點。在悠久的歷史中,無數的紫砂壺珍品出現又被埋沒,像流星一樣短暫又光芒四射的出現讓不知多少人都著迷,不管是博物館還是收藏家都在追尋著它們。
2 紫砂壺之竹韻魅力
茶器的顏色包括材料本身的顏色與裝飾其上的釉色或顏料。白瓷土顯得亮潔精致,用以搭配綠茶、白毫烏龍與紅茶頗為適合,為保持其潔白,常上層透明釉。黃泥制成的茶器顯得甘飴,可配以黃茶或白茶。朱泥或灰褐系列的火石器土制成的茶器顯得高香、厚實,可配以鐵觀音、凍頂等輕、中焙火的茶類。紫砂或較深沉陶土制成的茶器顯得樸實、自然,配以稍重焙火的鐵觀音、水仙相當搭調。若在茶器外表施以釉藥,釉色的變化又左右了茶器的感覺,如淡綠色系列的青瓷,用以沖泡綠茶、清茶,感覺上頗為協調。從紫砂陶的出現,到紫砂風的盛行,經歷了幾百年的歷史變遷,也經過了好幾代紫砂人的辛勤和努力,從最初的紫砂,到后來的紫砂壺,再到現在的紫砂文化,紫砂壺正用它的故事告訴著人們,歲月的傳說,人生的傳說。
竹段壺可以說是紫砂壺中傳統的不能再傳統的器形了,自明代以來,宜興的歷代紫砂工手就喜歡采用竹子作為紫砂壺的創作題材,除了竹子本身質樸自然、不尚奢華的特點和紫砂陶溫潤精細、含蓄內斂的本質特別契合之外,竹子還寄托了人們心中的美好愿望和理想。據《酉陽雜俎續集·支植下》記載:“北都唯童子寺有竹一窠,才長數尺,相傳其寺綱維,每日報竹平安。”可見竹段壺既有仿生竹子形象而貼切的外形,又有對竹子的剛直、勁節品格的禮頌,以及人們對平安、幸福生活的寄托和向往。
“咬定青松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巖中。千磨萬擊還堅韌,任爾東西南北風。”這是清代鄭板橋著名的《詠竹詩》。“竹”挺拔遒勁,自古以來經常出現在文人墨客的筆下。鄭板橋一生倔強不馴,尤以畫竹、寫竹見長。鑒于對鄭板橋倔強不馴、勁節虛心、高風亮節、剛正不阿的人品的欽佩和受其愛竹畫竹的影響,加之筆者自幼賞竹之“性剛潔而疏直,姿嬋娟似閑娟”,“涉寒暑之徂變,傲冰雪之凌厲”以及“未出土時先有節,于凌云處仍虛心”的君子氣質和風范,萌發了以竹為題材創作的心愿和設想。作品處處緊扣主題,壺嘴竹段造型,數片竹葉點綴壺身,枝盤葉翠,生機勃勃。
竹之君子,壺之君子,《團團圓圓壺》注定了不凡與脫俗,他是文人心境的一種宣泄,是世人品質的一次認同。《團團圓圓壺》將竹與壺的君子之風完美融合,提煉升華,形成一道精神內涵。同時,更是將竹文化與紫砂藝術結合,結合前人精華,塑造出自己的全新感悟。
《團團圓圓壺》作品線條柔和飽滿,有如一個“陶缽”,壺把高企,空靈而古樸,嚴謹而活潑,生動而滄桑,把美好生活寓意與紫砂藝術糅為一體,瞬間把人帶入遠古時代。
《團團圓圓壺》壺鈕塑一生動小熊,光亮的毛色,有力地四肢,高聳的雙耳,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壺嘴從壺身延展出來,以竹子形象示人,壺嘴處又牽出一截竹枝,給人無限清爽之感,沐浴竹林之中,颯颯清風,清新怡人。
又正如筆者的《圈竹壺》,作品可以分明感覺到一股竹的靈氣,彎曲的竹枝為壺鈕和壺把,曲卷翻動勢與度恰到火候;此壺承古而不泥古,在思想和情感的融合中,在品位和格調的提煉中,做到飄逸灑脫,高風亮節。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由此,品格與藝術得到升華。
《圈竹壺》在傳統的基礎上加以創新,以竹為題材,壺身扁鼓,平底圈足,嘴、把、鈕均為竹節形狀,竹節蒼勁疏瘦,頗有意味,竹節造型的壺把竹韻悠悠,呈上粗下細之勢,整壺中正沉穩,飽滿韻致,相得益彰,趣味無窮。品《圈竹壺》,悟心情,一把好壺,帶著我們徜徉在藝術世界和心靈綠洲,原來,這場藝術之旅簡簡單單,沐浴清香,洗滌心靈。若是拿此壺斟上一壺好茶,又該是怎樣的愜意自然呢?茶香裊裊,熱氣騰騰,有生活的希望,亦有藝術的追求,當然,還能傾聽內心的聲音。
3 結語
宜興紫砂陶藝一直是公認的中國“國粹”,在當代國際大舞臺上,紫砂壺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它讓世界更加了解中國和中國文化,它儼然已是中國的一張名片。因而,以紫砂壺來表達國人的愛國之心,情真意切,這是文化的需要,也是紫砂藝術發展的必然。紫砂這種古韻悠然的砂土,一旦被紫砂藝人制成一件藝術品,便不再是藏于山間的一丸土,它有了靈氣,取自天地與人的靈氣,總要流露出一種真實情感,定格成一種精神象征,折射出若干美學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