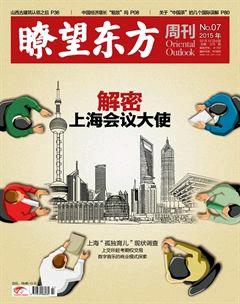中國經濟增長“粗放”嗎
學者唐毅南近期撰文指出: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方向要求客觀評價中國經濟成長的成就和原因。
西方主流經濟學家把國際金融危機的部分原因歸于中國的發展模式。國內不少經濟學家也斷言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發展模式是“粗放增長”,要求中國的結構轉型向西方尤其是美國模式靠攏。
但唐毅南通過比較研究發現:中國經濟是“高投資、高效率、高技術進步”和“低能耗”的高質量增長,其結果是GDP和消費同步高速增長。說中國是“高投資、低效率、低消費”的“粗放增長”這一廣泛流傳的說法沒有多少證據,并不符合事實。
粗放增長是經濟運行主要矛盾
李佐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
低效增長或粗放增長仍是我國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從現有有限的效率指標來看,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相比還有不小的距離。
如,能耗過多。中國工程院院士陸佑楣在2013年能源峰會上提到,2012年我國一次能源消費量36.2億噸標煤,單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國的3.3倍。我國每消耗1噸標煤的能源僅能創造14000元GDP,而全球平均水平是25000元。
地耗過多。國家土地督察系統在2011年例行督察中發現,全國43個城市中共有918個項目存在土地閑置問題,涉及面積共計8.84萬畝。
投資效率低。研究顯示,1978~2010年中國的資本產出比為3.92,美國1965~2010年的比值為5.29,1980~2010年的日本為14.69。
低效增長的原因很復雜,但主因來自一些非市場體制因素,我們還存在一些保護壟斷特權、保護低效落后、抑制公平競爭的制度安排。
必須痛下決心加快治療低效增長癥,治療的基本“藥物”在能提高全要素生產率(TFP)的“三大發動機”(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中。
要推進制度變革,如產權制度、企業制度、干部考核制度、財稅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等,為高效增長創造條件。推進新型工業化、城鎮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產業轉型升級等,優化經濟結構,提高國民經濟的配置效率。
還要通過促進技術進步、推進信息化、增加人力資本、完善基礎設施等,推進生產要素升級,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資本擴張和TFP增長并非必然此消彼長
張軍(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關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流行表述是,中國經濟的增長要從要素驅動的粗放增長轉變為效率驅動的集約增長。
盡管經濟學家們對什么是效率驅動的增長心知肚明,但還是有人干脆把效率驅動的增長解釋成TFP驅動的增長。問題是,如果中國過往增長真可用“粗放”定義,那該如何評價上世紀80年代以來TFP年均4%的增長記錄?如果這一數字不能證明中國是效率驅動的增長,那今天美國1%的TFP的增長率為什么可以是?
《偉大的中國經濟轉型》一書作者曾核算出在1978~2005年間中國的GDP年均增長9.5%,資本增長9.6%,為GDP增長貢獻了44.7%,教育增強型的勞動力增長2.7%,占GDP增長的16.2%,而TFP每年增長3.8%,貢獻了GDP增長的40.1%。
這與我最近所作的核算結果非常相似。由此可見,盡管資本增長對GDP增長的貢獻居首,但TFP增長卻相當出色。這應該不是粗放增長方式可以解釋的現象。
如果我們所說的轉變增長方式是指把TFP對GDP增長的貢獻份額從現有的40%提高到美國的80%,那就意味著中國的GDP增長率要降到5%以下(假設TFP年均依然能增長3%~4%)。一個教條看法是,如果經濟增長主要由投資擴張驅動,就應像蘇聯,TFP不能改善只會惡化,這就是粗放的,會崩潰。但日本也好,東亞也罷,情況相反。資本擴張快時,也是TFP的改善記錄較好之時。中國也如此。這可能是因為TFP的改進事實上在改善投資回報率,因此反而誘導了資本更快擴張。
單位GDP能耗≠能源實際效率
唐毅南(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粗放增長”的第一論據是中國高投資、低效率。但事實是,1950~1979年,中國資本產出比為4.93,美國同期是5.01。從1980年到2009年,中國資本產出比為3.91,而美國為6.82,此消彼長,中國資本效率大大領先美國。
再有,中國勞動增長率和TFP總體增長率也是令人滿意的。
那為何大家還會對中國經濟有高消耗、低效率的印象?一個廣為流傳的說法是,中國每單位GDP的能源消耗比美、日等發達國家高得多。但實際上,把單位GDP能耗等同于能源實際效率是方法論錯誤,得出中國能耗高的結論也是誤解。
“粗放增長”論的最后一個說法是認為中國投資過高,擠占了消費,因而消費不足,是所謂“高投資,低消費”并導致收入分配惡化,即GDP中居民收入與消費占比這一結構問題嚴重。
但消費占比低和消費水平低并不是一回事,關鍵還要看GDP規模總量,即“蛋糕”的大小。今天GDP“蛋糕”的大小,無疑取決于昨天投資的規模與效率。
中國改革三十多年的總體投資效率表現上乘,GDP蛋糕的規模快速增大。這樣,即使消費占比較低,但消費水平較高,這正是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實際情況:高增長率、高投資率、低消費比重與高消費規模四者并存。
用主觀想象的消費拉動論來批判中國的高投資、高增長,制造粗放增長論的輿論,既會對媒體和一般民眾產生誤導,也可能使具體政策制定因失去準確的事實依據而產生偏差。
沒必要將刺激消費作為常規政策
朱天(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教授)
雖然學術界對資本積累與生產率提高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的程度有爭論,但都同意中國經濟的增長是由資本投入的增長與TFP增長這兩個引擎同時拉動的。
不少人擔心中國投資過度導致結構性產能過剩。過去20年里,我們幾乎年年都聽說產能過剩,但中國經濟恰在這期間實現了前所未有的騰飛。
事實上,早在“九五”期間,國家就提出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到集約型的轉變,“十五”計劃又再提調整和升級經濟結構作為經濟發展的重點。但為何沒達到預期?
有人將其歸結為體制痼疾、改革停滯或政策有失誤。但中國經濟恰在過去十多年里得以快速增長,躍升為中上等收入國家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中國的經濟結構并不完全是政府的政策能夠決定的,很大程度上是我國目前經濟發展階段的自然結果。
當前,中國消費過低、儲蓄過高、經濟增長靠投資和出口拉動似乎已成不爭的事實。但從經濟增長理論上看,是儲蓄及由此帶來的投資而非消費才是經濟增長的主推力;持續的消費水平的提高是經濟增長的結果而非原因。所以,沒必要將刺激消費作為常規政策,擴大內需也可不必作為常規政策。
長期的增長不是需求問題,而是供給問題,政府的政策和改革應以增加供給能力和效率為目標。事實上,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并沒受到對消費和投資比例的錯誤認識的影響,這是好兆頭,說明領導層看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