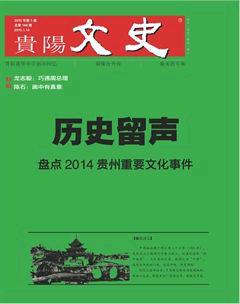貴陽清華中學創辦回憶
回憶當年的創業情景時,大家共同的感覺是:那個時候每個人都是勁頭十足,沒有一點私利;在討論辦學問題時,沒有上下級,非常民主,一起決策;每個人都發揮了自己的特點和長處;大家做事都極其認真,都以最好為目標。
1937年“七七事變”后,我和清華同學王萬福、唐寶鑫從北平逃難到漢口,我的父母也因家中住宅遭日機轟炸受損、城市安全岌岌可危,帶領兄弟和妹妹逃難到漢口和我會合。當年11月9日,家里所居城市因城防司令傅作義抵抗失守,太原淪陷。
面對祖國的烽火連天、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躪、許多學生失學流浪的慘狀,我們幾位同學萌發了利用自己的特長辦一所學校的想法,希望能以自己所長培養人才,實現“教育救國”。我們的想法得到同道的贊許,1937年年底,我們聯系了在校期間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學到武昌開籌備會議,其中包括索天章、徐步墀、孟昭彝、靳文翰等。討論的結果是,以自己的特長,辦一所中學來實現“教育救國”的理想。當時我們提出的辦學宗旨是:訓導青年,培養民力,宣傳抗日,驅逐日寇。這個辦學方向十分契合當時的形勢,目標明確,也與政府的旨意比較吻合。我們馬上開始在漢口、武昌選校址。1938年1月,我們收到了李祖才、徐步墀的父親徐穆青等人的捐款,隨即,我們便開始購買儀器和教具,但多方尋找仍無合適校址。這時,后來的學校基金捐贈人之一、《大公報》主筆張季鸞便向我們建議道:漢口能否守得住還未可知,其中變數會很大。辦學最好還是到大后方,貴州是個合適的地點,而且原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老校長周詒春在貴州省任財政廳長,有實權,他又十分熱心教育,并即將出任貴州省政府委員,到貴州找他,一定會得到他的支持。
幾位同學經過多次的醞釀和討論,決定接受張季鸞建議將學校辦到大后方貴陽去。有幾個因素的考慮:貴陽經濟落后,教育資源貧乏,抗日戰爭爆發后,許多學生流落到那里,無學可上,在那里辦學有生源;辦學需要一個安全的環境,相對來說,貴陽也比較安全;辦學是需要相當資金的,幾個窮學生剛踏上社會,雖然有一腔熱血,但是沒有金錢、缺少足夠的社會關系,辦學只能是空中樓閣,應該借助校友的力量來做這件事。
武昌籌備會議結束,在開展各項準備工作的這段時間里,又有宋士英、冀吉甫、趙永昌加入到隊伍中來。我們這支人馬充滿活力,也十分精干,從學科看,有學文的,也有學理的,而且有幾個清華研究院的研究生,他們都熱心社會活動。
王萬福、唐寶心在創辦清華中學的過程中表現出了活動能力。王萬福特地到湖南長沙拜訪了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遞交了武昌籌備會議的辦學計劃,并斗膽向梅校長提出:學校是否可以叫“清華中學”。據王萬福后來告知,當時梅校長格楞都沒打,接著話茬說:“‘清華兩字又不涉及有關專利,有什么不可以的。”并欣然同意可以擔任未來的“清華中學”名譽職務。有了梅校長的鼎力支持,我們幾位籌建者更加有了信心和底氣,勁頭也更足了。
大約在1938年2月,王萬福、唐寶鑫去貴陽周詒春學長處游說。先是將我們的辦學計劃書呈上,請學長指教。周詒春仔細閱讀后,認為方案很不錯,也對同學的愛國熱情、辦學之舉大加稱贊。隨后,同學委婉地提出,希望貴州省政府方面能提供部分辦學啟動經費,讓學校能運轉起來。周廳長當時沒有直接表態,只是說現在國難當頭,財政經費非常緊張,辦學固然很好,也應當支持,但貴州省是個窮省,財政方面本來就捉襟見肘,現在是戰時,財政越發困難。兩位又進一步向周廳長闡明了辦學的意義及急迫性,再次懇請予以考慮。此時,他們又適時地向周詒春表示已經去長沙拜謁梅校長,梅校長明確表示支持。臨走時,周詒春表示,他支持同學辦學,但學校最好是“民辦”而非“官辦”性質,因為民辦可以更有自主性,可以實現教育主張,至于經費他會積極籌措,努力促成。兩位回來向大家傳遞周學長的信息,大家都稱是。
另一方面,同學們各自利用自己的關系,尋找辦學資金來源。首先是求得清華母校學長的支持,校長梅貽琦、教務長潘光旦、秘書長沈履等帶頭解囊支持開辦清華中學,名教授馮有蘭、吳有訓、顧毓琇、陳岱孫也欣然解囊。在清華前輩的帶動下,社會人士也紛紛捐資辦學,商務印書館總經理朱經農、政界吳國楨、新聞界張季鸞等紛紛捐款。那邊,貴州省政府也有回應,支持清華同學到后方辦學。周詒春學長在創辦清華中學上出了大力,他利用各種關系,動員國內外清華校友和熱心教育人士為清華中學籌募基金,出面邀請貴州省名士任可澄、省府主席吳鼎昌、貴陽市首任市長何輯五、省交通廳長葉紀元,以及翁文灝、吳澤霖等社會名流擔任校董。學校最終由周詒春出任董事長,梅貽琦任名譽董事長。
1938年初,我將父母、兄弟、妹妹安排經廣東到香港躲避戰火。1938年3月,我和王萬福、唐寶鑫、索天章、徐步墀去貴陽(孟昭彝、靳文翰因在武漢有工作沒有前來),緊鑼密鼓地進行清華中學的籌備工作,周詒春學長慷慨地讓出省政府提供給他的住房給我們居住。我到達貴陽旋即按照商議決定的,主要開展了招生工作。1938年4月中旬,趙永昌、冀吉甫等到筑。根據先前已在貴陽選址的同學提出的方案,大家進行了商議,決定暫時租賃貴陽龍泉街復圣祠為校址,根據現實情況,決定先招初一、高一年級各一個班,另招生高中年級補習班(一個班級),只招男生。當時租借復圣寺,主要考慮一是租金比較便宜,二是地點適中。按照分工,在一次會議上我匯報了有關招生開展事宜,要點是:書寫了招生通知在市內張貼,另外通過政府教育廳的支持進行宣傳。招生工作是比較順利的,主要是“清華”這塊金字招牌很有號召力,另外就是名人的支持。會上,還就開學開幾個班級進行了討論。大家的意見是:開學之初以大班為宜,等上了軌道再分成小班進行教學。以后,又有李宗瀛(一二·九運動北平學聯負責人)、王達人等同學到貴陽,參加清華中學建設。大家推舉王萬福出任清華中學校長。
最終,我們共計招了115名學生(含補習班)。在開學之前,我們在貴陽又招聘了幾位教師。私立貴陽清華中學終于在于1938年5月1日正式開學。
到了1938年年底,學校的運轉開始正常,教育教學開始步入正軌。我們又有了進一步的打算,就是盡早遴選新校址,擴大招生規模。因為我們的辦學已初步得到市民的認可,人們通過各個渠道來打聽學校今后的招生規模,希望子女進入清華中學就讀。王萬福、宋士英、唐寶鑫在選址方面出力最多,他們常常在禮拜天放棄休息,四處尋覓新的辦學地址,最終把眼光落定在貴陽郊區的花溪。這個地方山清水秀,地處郊外,學生受到的干擾少,比較適合辦學。我們十幾人齊聚花溪,大家七嘴八舌闡述自己的意見,除了有人認為學校地點遠了一些、不利于招生以外,矛盾的集中點為是否要馬上搬遷。討論的結果是由于日機的轟炸,辦學規模的擴大,應該盡快搬遷,于是開始了行動。當時,我們中也有人反對搬花溪的,理由是學校各項教育活動剛開展,應該有一個適應期,新校舍的建設經費等也沒有落實,是不是緩一緩搬遷的速度,眼下先把教育做實。不過,多數同學還是有一股激情,認為事不宜遲,應該趕快上馬。教育工作與學校搬遷并不矛盾,可以并行不悖,至于校舍的經費,已經部分落實,不夠的部分可以促發大家去動腦腦筋加以解決。大家統一認識后,新校址的報告幾天后就上交貴州省政府,同時托校友關心這件事。在董事長周詒春的關心下,清華中學基建經費籌集終于到位,他又邀請清華校友、名建筑師童雋義務規劃學校建設和校舍設計。1939年3月,學校在花溪新校址上課。印象中有5個班級,130多個學生。學校最初遷到花溪時,學校購了當地幾處民房和40多畝土地作為教室、辦公和宿舍用地。另外,在毗鄰學校的花溪鎮租借一些民房作學生宿舍。
我們都知道教育質量是學校的生命,我們也知道光有分數的質量是片面的教育質量。在辦學之初,我們就有把清華大學的辦學理念移植到貴陽清華中學的想法。加上周詒春學長的指點,學校提出“智、德、體、群、美”的教育方針(群育指要有合作精神)。參加開學典禮訓話時,周詒春董事長向同學提出“愛國、誠實、自立、合作”的教育主張,提出“十年后同學們都能成為國家的棟梁”, 這是非常高的要求。清華中學也沿用清華大學“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校訓。記得當時學校的學生守則上規定,在校期間必須學會游泳,這和清華大學的要求一致,即強調體育對人發展的重要。學校規定了每天下午有1小時40分鐘的“強迫活動時間”,要求學生必須到戶外鍛煉。這些要求對育人很有必要。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先后有4所清華中學成立,分別是抗戰期間成立的貴陽清華中學、重慶清華中學、成都清華中學和抗戰勝利后孫立人將軍(清華校友)在東北創建的清華中學。這4所清華中學,貴陽清華中學最早成立,辦學成績最好,名氣也最大。那時候貴陽清華中學辦學聲譽反映在學生近悅遠來,一些家長紛紛把孩子送來就讀。當時梅蘭芳先生避難在香港,得悉貴陽清華中學的名氣,硬是將子女梅保玖、梅保琛從香港輾轉多地到貴陽清華中學讀書。抗戰中犧牲的戴安瀾將軍的兒子戴復東也就讀于貴陽清華中學,后來他是同濟大學教授。一些南洋僑胞子弟也有多人在此讀書。
根據8人所學專長,我們進行了分工。王萬福除教算學外,承擔學校日常管理工作;經濟系研究生唐寶鑫教英語、公民課,另兼會計主任(出納、會計僅他一人);經濟系畢業生王達人教歷史(兼教務主任);外語研究生索天章教英語;我是清華研究院語言研究所研究生,學的是語言學,但根據需要擔任算學教員;數學系畢業生徐步墀教算學;化學系畢業生冀吉甫教物理、化學;外國政治系畢業生宋士英教英語;西南聯大歷史系畢業的李宗瀛教歷史。另外,還分別聘請了北京大學、廣州中山大學、上海圣約翰大學、上海東亞體育專科學校的畢業生任教。當時,校董會開給我的月薪是70塊大洋,工資是不低的,萬福、寶鑫也是70大洋;達人管教務又教書,工作比較繁重,月薪80大洋;記得上海東亞體專畢業的吳淵薪酬較高,月薪也是80大洋。
我1939年上半年接到西南聯大的擔任助教的聘書,于是去昆明履新。我在清華中學待了1年多,時間雖然不長,但是這段人生經歷對我來說彌足珍貴。這段時間里,有機會比較深入地接觸了社會,對中等教育有了了解,收獲更多的是鍛煉了我與人打交道、與社會接觸、綜合分析事務、判斷事務、獨立處理事務的能力。
后來,隨著王萬福的離開,宋士英曾當過校長。1941年后唐寶鑫開始當校長,寶鑫在任時間最長,對學校的建設貢獻最大,他一直干到1950年方才離開心愛的教育崗位去天津一家毛呢廠工作。1957年他蒙冤被打成“右派”,這些是“文革”結束以后,我們在北京開全國政協會議見面時他告訴我的。
1977年開始,我和索天章、唐寶鑫恢復書信聯系。1979年春節前,唐寶鑫兒子唐北非旅行結婚到上海,曾在我們家住了幾天。索天章是1943年離開貴陽清華中學到復旦大學(四川重慶)任教的,1946年隨復旦復員回上海,上世紀50年代,被調至張家口軍事外語學院;上世紀80年代調回復旦重新進行他的莎士比亞研究,這期間我們一直保持來往。宋士英當年是國民黨員,曾因“政治歷史問題”發配到新疆,吃了不少苦。1978年,我收到他從新疆寄來的信,信封上僅寫了“上海復旦大學李振麟收”。信中告知了他將獲得平反的情況,我回了信,希望他有空到上海。以后他曾到上海我的家,老同學、當年創業的老同事劫后余生,相聚十分高興。
在與上述同學回憶當年的創業情景時,大家共同的感覺是:那個時候每個人都是勁頭十足,沒有一點私利;在討論辦學問題時,沒有上下級,非常民主,一起決策;每個人都發揮了自己的特點和長處;大家做事都極其認真,都以最好為目標。當然,清華前輩的支持也非常重要。正是有了以上這些因素,貴陽清華中學成功了。
(盧慈和、李北宏整理)
注:李振麟(1914—1993),語言學家,生前系復旦大學教授;盧慈和系李振麟夫人,高齡95,系愛國民主人士,原國民政府貴州省省長、中共中央立傳烈士盧燾之女。李北宏系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