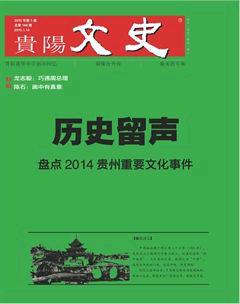1961年春節(jié)回鄉(xiāng)見聞
趙福書
沒(méi)有吃過(guò)蒿子、蕨根、枇杷樹皮乃至高嶺土、龍骨石等等的人,是體會(huì)不到那種疾苦生活的。
1961年2月15日(農(nóng)歷辛丑年正月初一)傍晚,我乘61次特別快車(北京——廣西憑祥)離開北京,到柳州轉(zhuǎn)乘普客,第六日清晨抵達(dá)貴陽(yáng)。在貴陽(yáng)火車站下車后,再乘公共汽車到貴陽(yáng)客車站買到開陽(yáng)的汽車票。當(dāng)時(shí)交通很不方便,貴陽(yáng)到開陽(yáng)的汽車每天只有一輛,而且是用一輛解放牌貨車改裝的,里面安的是木條椅子,可容納30名乘客。當(dāng)時(shí)乘客不多,去售票口就能買到票,每張票好象是二三元錢。
我到汽車站旁一家國(guó)營(yíng)面館準(zhǔn)備買碗面條吃,吃面要排隊(duì)。排在我前面的是一名身體單薄、約有50歲的婦女,她的兩碗面條剛抬在手上,旁邊一名瘦骨嶙峋、衣著襤褸、蓬頭垢面約20來(lái)歲的男子突然竄上去,伸出兩只又臟又瘦的手,同時(shí)抓起兩只碗里的面條往嘴里塞。那婦女見狀忙將碗放在窗臺(tái)上,用兩個(gè)拳頭像擂鼓一樣在那人的背上邊打邊罵:“你這個(gè)狗日的餓死鬼!餓死鬼!老娘都沒(méi)有得到吃啊!”那人躬背由她打,自己只管抓起吃,吃了面又將面湯喝得一干二凈才轉(zhuǎn)身若無(wú)其事地邊抹嘴巴邊向外走了。其實(shí),那土巴碗裝的面條既無(wú)多大油水、又無(wú)蔥姜等佐料,就是放了一點(diǎn)油辣椒,面條也是黑不溜秋、硬梆梆的,還只有國(guó)營(yíng)飲食店才有賣(當(dāng)時(shí)不允許私營(yíng))。前人說(shuō)“饑不擇食,寒不擇衣”,看來(lái)千真萬(wàn)確。
汽車一顛一簸,到開陽(yáng)已是午后了。是年正月間,天氣尚好,多晴少雨。開陽(yáng)到馮三是沒(méi)車的,原準(zhǔn)備下車后立即步行回家,誰(shuí)知時(shí)間不允許了,又由于一碗面條早已抖光,于是我便到縣委招待所住了下來(lái)。我在招待所吃過(guò)飯,睡了一會(huì)便出門轉(zhuǎn)了一圈,城里的房屋變化不大,城墻已經(jīng)拆毀,街道還是那么寬,只是石板路變成了泥沙路面,加上兩邊的舊式木房,仍顯得爛糟糟的。第二天,我吃過(guò)早飯就步行回馮三,隨身攜帶的是一口帆布箱子和一只“北京牌”旅行袋。箱子里全是裝的食物,有北京產(chǎn)的高級(jí)面條、點(diǎn)心和山西杏花村產(chǎn)的“竹葉青”、北京的“紅葡萄”和蘇聯(lián)產(chǎn)的“威士忌”等名酒各1瓶;旅行袋里裝的換洗衣服。箱子背起很沉重,離開招待所時(shí),招待所朱伯伯很是關(guān)心地叮囑我說(shuō):“路上要小心,現(xiàn)在到處都在餓飯,謹(jǐn)防遇到搶人的!”我頷首表示感謝。
離開招待所后,我信步走出北門,登上望城坡,還以為像當(dāng)年進(jìn)城開會(huì)那樣,從牛滾凼(今干河坡林場(chǎng))分左手下鯉魚坡合公路,這樣走捷徑可減少一些時(shí)間。誰(shuí)知,這條以往的小路早已荒廢無(wú)人走了,處處都是叢生的茅草,青松挺拔,難以辨別方向,一走就走錯(cuò)到了潮水寨子。經(jīng)問(wèn)明當(dāng)?shù)厝罕姴庞址党蹋仡^再?gòu)呐L凼上大路,當(dāng)我走到馮三街口時(shí),天已墨黑,伸手不見五指。
我看見路邊左側(cè)堡坎下有一片黑呼呼的瓦房,瓦房里有微弱的燈光在晃動(dòng),同時(shí)聽見有人說(shuō)話的聲音,于是就尋路走了下去。原來(lái),那里是馮三公社馬江管理區(qū)建的坪上養(yǎng)豬場(chǎng)(當(dāng)時(shí)一區(qū)一社,下分管理區(qū)、大隊(duì)、生產(chǎn)隊(duì)),里面坐著的人都是些熟悉的面孔。他們見我突然而至,真是感到稀奇,忙招呼我坐,問(wèn)寒問(wèn)暖,又問(wèn)吃飯沒(méi)有等等,我疲憊地說(shuō)了還是在縣委招待所吃的早飯,出城把路也走錯(cuò)了等情況。于是,他們就給我端來(lái)一個(gè)我第一次看見也感到很稀奇的瓦罐子蒸的4兩米的飯和兩個(gè)饅頭,一碗白菜湯。飯我沒(méi)有吃,把饅頭吃了,湯喝了,肚子也就飽了。我從正月初一離開北京,到初九才喝上家鄉(xiāng)水,俗話說(shuō)“美不美,山中水;親不親,故鄉(xiāng)人。”是夜,我們幾人圍著火爐擺了很長(zhǎng)一夜龍門陣。第二天早晨,我當(dāng)兵時(shí)的鄉(xiāng)支書夏占云便給三合大隊(duì)打了電話(當(dāng)時(shí)各村都通電話),同時(shí)叫在養(yǎng)豬場(chǎng)喂豬的胡發(fā)亮(是我胡氏母親的舅侄兒,因我們不認(rèn)識(shí),經(jīng)介紹他就叫我老表哥)給我背箱子,送我到三合場(chǎng)去。
我跟胡發(fā)亮經(jīng)十字路下賴子橋,過(guò)了油房剛轉(zhuǎn)拐下坡,便看見大隊(duì)長(zhǎng)宋必書與我小時(shí)候相好的鄭金全陪著我母親接我來(lái)了。當(dāng)走到叫花洞時(shí),我驀然看見石碾盤廢墟邊躺著一具骷髏骨,白晃晃的尸骨令人膽寒。宋必書見我驚異,便解釋說(shuō):“這是個(gè)年輕娃兒,不知什么地方走來(lái)就餓死在這里了。”我沒(méi)有答言,鄭金全補(bǔ)充道:“油房旁邊還餓死得有一個(gè)男嘞,穿件紅衛(wèi)生衣,背靠在土埂上,坐在地上死的。”我問(wèn)他們:“死了怎么沒(méi)有人埋?”他們說(shuō):“哪個(gè)去管茲些外來(lái)人,我們這里死了人,都因餓飯無(wú)力抬不起去埋!真是凄慘得很呀!”
我走進(jìn)闊別六七年的三合場(chǎng)街上,家家關(guān)門閉戶,當(dāng)年那種趕場(chǎng)的熱鬧場(chǎng)面已蕩然無(wú)存。后來(lái)才知道,人們都上山找野生植物充饑去了。家里破破爛爛的,十分凄楚。我進(jìn)堂屋后,一眼看見女兒趙潔蓮、三弟趙平中兩叔侄站在香火旁門檻跟前,手里各拿著一根小木棍在玩。我離家時(shí)小女兒才出生3個(gè)月,母親見我木訥地盯著他們知道分不清誰(shuí)是誰(shuí),便手指趙潔蓮說(shuō):“這個(gè)是你家的……”話音未落,似乎有點(diǎn)憨乎乎的姑娘兒,不知什么原因竟然“哇!”地一聲哭了起來(lái),我連忙伸手去抱她也不讓我抱,反而哭得更厲害了。母親見狀忙說(shuō):“孫兒,是你爸爸回來(lái)了,不要哭哪!”我兩眼滾著淚珠,忙打開箱子取出3個(gè)伍仁餅子,遞給老幼一人一個(gè)。母親說(shuō):“已兩三年沒(méi)有見到過(guò)這些東西了,現(xiàn)在家里無(wú)一粒糧食,吃飯是在集體食堂打,油鹽也差,帶來(lái)的食物就留著自己吃罷!反正我們吃蕨根粉、蒿芝、紅刺根皮、枇杷樹皮、涎朗樹皮等野生植物已經(jīng)習(xí)慣了……”母親正說(shuō)著話,只見父親上山挖了半草籃蕨根,氣喘吁吁、步履艱難地回家來(lái)了,我叫了父親一聲,便包著眼淚問(wèn)起蕨根的吃法來(lái),以免老人家傷心。過(guò)了片刻,我妻子挖了一稀籃背青?樹圪頭(樹根),搖搖晃晃地也回家來(lái)了。
我到家以后,便很快聽到一些消息,說(shuō)中央要逐漸調(diào)整農(nóng)業(yè)政策,每個(gè)農(nóng)業(yè)人口要分給一定數(shù)量的“自留地”,同時(shí)允許農(nóng)民在房前屋后種植一些糧食,也可以在田邊地角適當(dāng)開墾少量邊荒等。
在家期間,我目睹一些人由于吃蕨根、樹皮、包谷核等太多,又無(wú)油水,因此,難排便、肚子脹、浮腫、步履維艱。到集體食堂打飯時(shí),雖然蒸飯罐上標(biāo)明“8兩”,實(shí)裝只有2兩大米。有位參加過(guò)抗美援朝的老兵說(shuō),他數(shù)了罐子里裝的大米,只有3700粒左右。沒(méi)有吃過(guò)蒿子、蕨根、枇杷樹皮乃至高嶺土、龍骨石等等的人,是體會(huì)不到那種疾苦生活的。
村子里沒(méi)有狗叫、雞鳴,房頂上沒(méi)有炊煙,真是與舊時(shí)“白骨露于野,千里無(wú)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dāng)嗳四c”的饑荒年代差不離啊!
在我家附近,田坎上家庭成份是半地主式富農(nóng)的楊毓彬、楊毓貴一家,一連餓死男女好幾口人,只剩下一個(gè)年僅十多歲乳名叫楊叫花的寡崽;我家鄰居楊坤芳,近60歲,臨終時(shí)呻吟說(shuō):“我只要有二兩米的稀飯喝,就不會(huì)斷這口氣啰”;水淹凼的宋必成,一個(gè)曾經(jīng)參加過(guò)抗美援朝作戰(zhàn)的老兵,外出途經(jīng)高云時(shí)鬧肚子,進(jìn)入一片包谷地里解溲,當(dāng)?shù)厝罕娬`認(rèn)為是因餓飯下地偷包谷的,便一輪亂棒將其打死了;還有我家對(duì)面家庭成份是富農(nóng)的楊本世之母黃氏,因去生產(chǎn)隊(duì)開會(huì)遲到點(diǎn)時(shí)間,被扣飯活活餓死了!還有我母親,已年過(guò)半百,只因說(shuō)了幾句對(duì)餓飯不滿的話,竟然被罰下苦力,叫她去給挖在街心的約兩丈長(zhǎng)、丈余寬、五六尺深的滅火坑抬泥巴,還說(shuō)不準(zhǔn)他人幫助,為此,我妻子楊金秀只好趁夜深人靜時(shí)去偷偷幫助挑土。
1958年本來(lái)全國(guó)都是個(gè)大豐產(chǎn)年,而開陽(yáng)是豐產(chǎn)不豐收。眼見糧食爛在坡上(特別是紅苕堆積如山)無(wú)人問(wèn)津,還說(shuō)什么“鏵口耙子掛在墻壁上也要吃3年”等等。正值秋收時(shí)節(jié),卻搞“大煉鋼鐵”,全縣組織十余萬(wàn)勞力上山,不分晝夜,風(fēng)雨無(wú)阻,全縣高爐林立。據(jù)原縣人大一副主任說(shuō),1958年搞大煉鋼鐵,縣委派他到羊場(chǎng)區(qū)去放“鋼鐵衛(wèi)星”,上“黑山”(伐木挖煤炭)當(dāng)“鋼鐵廠長(zhǎng)”,每天組織兩千多人上山筑煉鋼高爐;又遍山挖鐵礦,砍古樹制作風(fēng)箱,砍松樹燒木炭。砍伐山林,破壞了生態(tài)平衡,引得老虎也不客氣了,老虎不時(shí)出現(xiàn),到1961年底羊場(chǎng)區(qū)已被老虎咬吃20多人,全縣被老虎吃掉30多人,還有被咬傷、抓傷的。
人們?nèi)コ阅恰安皇斟X的公共食堂”,全縣搞“大伙食堂”2028個(gè),刮起一陣不可收拾的“共產(chǎn)風(fēng)”。由于大家一哄而上吃“大鍋飯”、“攆伙伙羊”,既助長(zhǎng)了懶漢思想,又挫傷了絕大多數(shù)人的勞動(dòng)積極性,使集體收入、個(gè)人勞動(dòng)所得、公共積累等每況愈下,漸漸地層層倉(cāng)庫(kù)里的糧食就被吃空了。糧食緊張了,又叫大家上山“取寶”,找野生植物,全縣每天平均有3萬(wàn)多人上山找吃的。到了1961年春天,群眾3年缺糧,吃“五五二”,即一日兩餐,成人每餐吃5兩蔬菜、5兩野生代用品(蕨根、樹皮等)和2兩糧食。那些掌權(quán)的干部又跳出來(lái)整農(nóng)民、整生產(chǎn)隊(duì)長(zhǎng),說(shuō)他們“欺騙上級(jí),不如實(shí)報(bào)告糧食產(chǎn)量。”并實(shí)施“刑訊逼供”、“反瞞產(chǎn)私分”,打罵群眾、打罵生產(chǎn)小隊(duì)干部,與此同時(shí),“四類分子”(地主、富農(nóng)、反革命、壞分子)也列入嚴(yán)整對(duì)象,捆、綁、吊、打人成了一些區(qū)社和大隊(duì)干部的家常便飯。
大搞田土“深耕”,翻地三尺,說(shuō)是這樣種出來(lái)的稻子要用斧頭才砍得斷,偏信神話違背自然規(guī)律。冰天雪地,馮三公社馬江管理區(qū)三合大隊(duì)的干部還勒令“四類分子”楊毓彬、楊毓貴兄弟去犁水田,兄拉犁、弟駕馭,犁得不如干部的意還要挨“青?棒棒”。
農(nóng)民們?cè)谝归g下地去拿糧食,并跟隨季節(jié)轉(zhuǎn)變什么成熟就拿什么,剝胡豆、割豌豆、麥子、掰包谷等。有個(gè)叫何樹云的皮匠,住在我家對(duì)面一個(gè)大山溝里,一家老小餓得難熬,除了打山耗子吃外,一天晚上他將附近生產(chǎn)隊(duì)的一頭黃牛偷偷切下一塊后腿肉燒來(lái)吃,結(jié)果被判3年徒刑。干部對(duì)“偷”的問(wèn)題難于管理和處理,只好默認(rèn)地寬恕并冠名為“拿摸行為”,不了了之。有膽大妄為者,則去撬國(guó)家和集體糧倉(cāng)甚至扒竊、搶劫運(yùn)糧汽車等,雖然捉到要挨整,但是為了活命,見“空子”就鉆。據(jù)縣公安局文獻(xiàn)記載:1960年冬到1961年5月21日,全縣發(fā)生偷宰耕牛案件472起,宰殺耕牛83頭。1961年6月8日,城關(guān)公社魚上管理區(qū)杉木莊生產(chǎn)隊(duì)3名11至14歲兒童因饑餓難忍,去偷生產(chǎn)隊(duì)的糧食蔬菜被抓住打死。是年3月至6月25日,全縣農(nóng)民“拿摸”糧食被干部捆綁吊打和扣發(fā)口糧38人,致死13人。
整完這些事,回過(guò)頭又整那些影響社會(huì)治安的人和那些整過(guò)群眾的“當(dāng)權(quán)者”。據(jù)1960年有關(guān)部門統(tǒng)計(jì),開陽(yáng)縣有499名干部因過(guò)“糧食關(guān)”捆綁吊打生產(chǎn)隊(duì)長(zhǎng)、社員受到各種處分,占同級(jí)干部數(shù)的28%。馬江新華大隊(duì)有個(gè)姓楊的“地主分子”在過(guò)年時(shí)沒(méi)有好吃的,便在大門上寫副春聯(lián)云:“兩匹青菜辭舊歲,三個(gè)蘿卜迎新春”,橫批:“也是過(guò)年”。對(duì)此,社隊(duì)干部說(shuō)他對(duì)現(xiàn)實(shí)不滿,用寫春聯(lián)的手法挖苦、攻擊社會(huì)主義制度等將其捆押批斗,并令他打起銅鑼游走村寨檢討“罪行”。
農(nóng)歷二月中旬我回到北京,北京形勢(shì)已經(jīng)開始好轉(zhuǎn)。副食品供應(yīng)很好,機(jī)關(guān)干部不再去排隊(duì)搶購(gòu)那不收糧票的2兩面包片了。我將回鄉(xiāng)所見所聞詳細(xì)報(bào)告給主任,請(qǐng)他有機(jī)會(huì)時(shí)給上級(jí)特別是中央領(lǐng)導(dǎo)同志反映。主任見我情緒比較消沉,便囑咐我好好休息幾天,再去工作。
其實(shí),我哪有心思工作,一心只想回老家,于是遞交了一份《回家申請(qǐng)報(bào)告》。7月下旬,我的申請(qǐng)報(bào)告被批準(zhǔn)了。1961年8月2日,我離開了生活3年的北京,9日上午回到了開陽(yáng)。
但愿我們這一代人經(jīng)歷的那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劇不再重演!
(作者系開陽(yáng)縣公安局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