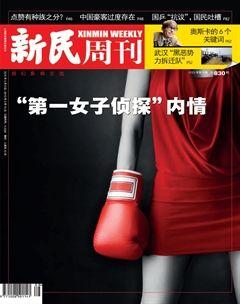唐逸覽:大石嫡傳,德藝雙馨
王悅陽

上圖:唐逸覽攝影/吳軼君
繁梅報春,花樹成蔭。在畫家唐逸覽位于西郊的“勝緣齋”中,到處可見欣欣向榮的草木,雀躍枝頭的小鳥,宛如他筆下的百花百鳥,在這個初春的時節,分外令人心醉。
唐逸覽是當代海派畫壇頗具盛名的花鳥畫家,生性豁達、謙和大氣的他,熱愛生活,廣交朋友,脾氣、性格像極了乃父——海派藝術大師唐云先生。由于家庭環境的影響,唐逸覽自幼受父母熏陶喜愛繪畫,17歲進入上海中國畫院學習國畫。在半個多世紀漫長的藝術創作道路上,他有過坎坷,也有發自內心的愉悅。他寫過一首詩,貼切地道出了他的藝術觀、人生觀:“逸筆縱橫不逾矩,覽觀今古創意新。小事糊涂大事清,獨上云天闊步行。”這既是唐逸覽對個人藝術道路的寫照,同時也是他對藝術不斷追求的心聲。
“逸筆縱橫,小李將軍逢勁敵;覽觀古今,大石居士有傳人。”這是寶島臺灣的老畫家余偉書贈唐逸覽的嵌名聯。作為唐云的老友,余偉在聯中用了唐朝畫家李思訓父子(人稱大小李將軍)的典故,稱贊唐逸覽繼承并發揚光大了其父唐云先生的繪畫藝術。的確,在唐云的幾個子女中,只有唐逸覽習畫,并得其真傳。熟悉他的人都可以感受到,他在師承父親畫風中也繼承了其父治學、為人之道,并將這種精神表現在畫面的意境之中。他的花鳥畫以色彩為主,其所作《海棠小鳥》,色彩熱烈,畫面豐富,把大自然生生的氣息躍然畫面;其所作《繡球花》,以水墨渲染,極具清新之雅味;其所作《紅梅傲雪》,兼融色彩、水墨之韻味,一展梅花清寒不爭春,但又傲骨滿枝之神韻。70歲后,他的畫作愈發顯得色彩鮮亮而不躁動,豐富之中又更顯文靜、富貴、典雅之氣。值得一提的是,逸覽老師年輕時還是一位工藝技術人才,他從搪瓷圖案的繪制到設計、配方、印刷、燒制都能親手制作。由于唐逸覽將傳統美與工藝美的融合,使他首創的搪瓷絲網印貼花工藝獲輕工部重大科技成果獎。又從1980年創匯300萬美元到1987年創匯2000萬美元。這種融合傳統美與現代工藝美的技法,也可看作是唐逸覽對國畫藝術,特別是對其父親唐云所創造的“唐家樣”藝術的又一次創新。
如今,年過古稀的唐逸覽每天以書畫自娛,愛好廣泛的他喜歡收集古董文玩,也喜歡種花養鳥,還頗諳股市沉浮,日子過得充實而滿足。“作為一個畫家,不僅要注重畫品,而且更重要的是注重人品。”唐逸覽說,“父親生前經常告誡我要‘畫如其人’,這無疑是我最為受用的財富。”正是因為以父親為榜樣,唐逸覽在畫畫之外,才會一直堅持不斷地對父親的繪畫藝術進行研究,全身心投入唐云藝術全集有關資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中。經過十多年的積累,在唐云先生百年誕辰之際推出了由杭州唐云藝術館主編的《唐云全集》大型畫冊四本。整部全集的把關工作主要都是由唐逸覽來做的,入選全集的作品有五六百幅,不僅確保都是真跡,更重要的都是精品,力求通過這些作品展示出唐云藝術的風格和精神。此外,唐逸覽還積極參加繁榮海派書畫藝術的工作,他不僅是海墨畫會的發起人之一,而且還成為海上名家后裔聯誼會的骨干力量,更身兼上海中國畫院畫師、上海書畫院畫師,常年致力于繼承和弘揚“海上畫派”的優良傳統,不斷探索,勇于創新,續寫海派書畫新篇章。
父親熏陶、耳濡目染
《新民周刊》:走進您的家中,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懸掛在墻上的一幅您在22歲時和父親唐云合作的作品《秋柳山雀》,筆墨精到,設色雅致,難得的是,您的父親還親自為您題款,并且補畫了山石,以此肯定您的藝術創作。
唐逸覽:回想小時候,父親在作畫時,我常常站在一邊看,很好奇為什么父親刷刷幾筆,一朵牡丹,一只小鳥就躍然紙上。有時候,我也幫著在一旁拉拉紙。父親很嚴厲,但對于喜歡畫畫的我似乎格外喜愛。甚至他最寶貝的曼生壺,收藏的字畫,幾個孩子中,就只有我能碰。南方潮濕,過了黃梅天,到了盛夏,我就會陪著父親一起整理畫作,把畫掛一掛,就不會發霉。怎么卷畫,怎么收藏這些字畫,父親都會手把手地教我。天長日久,受他的影響,我喜歡用他裁掉的紙邊涂涂畫畫。而真正開始畫畫是在讀中學的時候,那時我在學校里畫書簽勤工儉學,父親畫了幾個稿子,我就對著臨摹,結果都賣了出去,給我很大的鼓勵與信心。后來,我從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畢業后,直接進入上海中國畫院,跟隨父親學花鳥畫。當時,畫院學員有陸一飛、邱陶峰、汪大文、徐志文、杭英、吳玉梅和我,班長是陸一飛。
說起這幅《秋柳山雀》,更有意思。當時,上海中國畫院的裱畫室正在重新裝裱江寒汀先生的一幅畫作,我當時看了很喜歡,就對著原作臨摹了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畫面上的柳樹和山雀,父親看了,認為畫得還不錯,于是就欣然替我在畫面下方補了一塊石頭,并題:“逸覽臨寒汀秋柳山雀,大石為補一石”,以此肯定了我的畫。當然,在鼓勵之外,父親對于我的畫還是批評指點得多。他往往不多話,關鍵之處提點幾句,全靠自己的悟性與勤奮去慢慢理解、消化。他要我畫過一段時間宋元的工筆畫,要求在工整之外,還要有筆意。記得父親當時說過,趁著年輕多畫一些工筆畫,到老了就畫不出了。特別是宋元時候的作品,非常好,來自生活,精細入微卻又沒有匠氣,對于提高繪畫水平是非常有幫助的。因此,雖然我畫的是小寫意花鳥,但基礎卻是宋元工筆畫。
回想那個時候,除了父親的畫稿,對于江寒汀、張大壯等畫院的老先生們的作品,我都曾花力氣認真學習、臨摹過。當然,主要還是學父親的畫,有的時候山水也畫一點。我認為,藝術的路是很長的,只有不斷學習,才能慢慢走出自己的道路來,但這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現在有很多年輕的人搞創新,想走捷徑,一夜成名,這個是值得探討的,在藝術上取得成就,要經歷長時間的磨練,還要得到社會的承認,父親曾說500年后才能見高低,藝術成就既要得到當代也要得到歷史的認可。這是父親這一代的大師們給予我的啟迪與感悟。
《新民周刊》:解放前就名聲大噪的唐云先生與江寒汀、張大壯、陸抑非一起被譽為海上花鳥畫的四位代表人物。他的繪畫藝術風格俊逸瀟灑,筆墨清健明潤,山水、花鳥、人物兼擅,尤以雋雅清麗的花鳥畫別開生面。受到父親的影響,您的創作風格也以傳統為基礎,講求筆墨,又從生活中汲取靈感,推陳出新,可謂既充滿才情,又兼具情趣。作為畫家,又是大師之子,親生嫡傳,您是如何看待和評價唐云先生的繪畫藝術的?
唐逸覽:我父親的藝術面目是很突出的。早年是清秀瀟灑,用筆灑脫,這和他的性格有關系。發展到晚年,變得老辣厚重。他的畫每十年有一個變化,字也在變。看每一件父親的作品,我能說出創作的年份,上下浮動不超過三年,就是因為他每個階段的畫有不一樣的特點。
在中國畫理論中,畫品與人品是一致的,父親的藝術成就跟他長期的修養、用功和學問都是分不開的。他收藏石濤、八大山人、金冬心等人的古代書畫作品,并從當中汲取營養。作品中既有南方的清秀雅意,還有北方的剛強粗獷。有人說唐云的作品就像一壇陳酒,一品芳香,再品醉心,有一股激情在里面。

桃花山雀
《新民周刊》:在您漫長的藝術生涯中,父親對您的指導與幫助,始終是無微不至,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唐逸覽:的確,我給你看幾樣東西,很能說明問題。這是一方硯臺,經祖父的手傳給了我父親,父親又在我考入美專時給了我。硯臺上刻著:“自食其力,寸陰是惜,守我此田,無枯日。”父親是借此勉勵我,藝海無涯,唯勤作舟,要自食其力,要珍惜時間。如今,這方有著特殊意義的硯臺我一直用到現在。還有這幅創作于1961年的《枇杷熟后》,是作為獎勵給我的。父親教學生時,筆墨訓練之余,特別講究詩文修養,他要我們多讀書,多寫字,畫院還專門安排了周煉霞老師來教我們填詞作詩。有一次父親得到一副草書對聯,要我和吳玉梅來讀,我第一個全部讀對:“石硯不教留宿墨,瓦瓶隨意插新花”,父親很高興,就把這幅畫作為獎品送給了我。他這是拿自己的作品為鼓勵,希望學生們增強文化修養,增加書法功力。還有這一張照片,那是上世紀70年代末我們父子受邀到北京釣魚臺國賓館作畫,照片中提筆作畫的我當時已經40多歲了,而在旁指點的父親也已70多歲,但他的指導還是很具體,這里該怎么畫,那里要加點什么……你看看,我都這么大了,他還在親力親為指導我,這就是老一輩人的風采。父親的精神讓我感動,也激勵我求索創新直至如今。
《新民周刊》:可以說,父親對您繪畫藝術創作最大的肯定與鼓勵,無疑就是在您的作品上題跋,或者是補筆合畫,這類父子合作的作品,也成了您一生最珍貴的回憶之一。
唐逸覽:的確。我們合作的作品前前后后約有三十余件,雖然現在大都零散在外,但每每再度見到這些作品,當年一起切磋交流的場景又浮現在眼前。我們唯一的一次父子畫展是1989年在新加坡舉辦的。1993年,我們曾計劃到寶島臺灣再度舉辦父子畫展,當時一切手續都已辦妥,臺灣的朋友也已經來安排接待了,可是由于父親突然心臟病復發住進了華東醫院,而且一進去就沒再出來,直到當年10月7日搶救無效過世,這不得不說是一大遺憾。帶著父親未了的心愿,那年我還是去臺灣辦了展覽,也算是圓了他老人家的一個夢吧!
大石嫡傳、德藝雙馨
《新民周刊》:除了向前輩、向傳統汲取養分,生活也是您創作的一大源泉。特別是花鳥畫,一草一木,一樹一石,一鳥一蝶,體現的其實是人的情趣與情操。正如唐云先生當年所說的那樣:“畫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花鳥畫”,這無疑也是您從藝的座右銘了。

上圖左:山花爛漫上圖右:竹報平安富貴有余
唐逸覽:的確,父親對于生活的觀察與熱愛,也深深影響了我。你看我現在,種花、養鳥,目的就是為了觀察、寫生,吸取靈感。幾年前,為了畫好雞,我托人從北京買來孵化箱,在家中養起小雞,每天觀察它們如何長大。最近我在后院養了許多相思鳥,我每天在喂食的時候就觀察它們,如何飛,如何戲水,如何鳴叫……這樣既為藝術創作細心觀察,積累素材,也使我的作品有濃濃的生活氣息,更豐富了我的晚年生活,一舉多得。
《新民周刊》:從您的繪畫作品來看,在繼承父親繪畫風格的同時,更發揮了色彩的作用,強調了花鳥畫的時代感,難能可貴。唐云先生當年大膽地創作出了棉花、向日葵等古人極少涉及的花卉題材,而您在父親的基礎上,更描繪表現了枸杞、紫荊花、馬蹄蓮乃至阿里山神木等的風采,令人感到耳目一新。
唐逸覽:無論是工筆還是寫意,我走的繪畫藝術道路都是十分具象的,通過對形的刻畫,最終要表達的還是神。中國畫離不開筆墨,這是中國畫的特性,是宣紙、毛筆、墨汁的特性所決定的。西洋畫講筆觸,中國畫也有筆觸,只是中國畫的筆觸是通過墨色濃淡來表現的。就好比我畫芭蕉,一點水、幾滴墨,乍一看畫面上是一整塊墨色,但仔細研究,里面是有枯濕濃淡的,是要分出陰陽向背和虛實不同來的。但如果再要我畫幅一模一樣的,根本做不到。為什么?因為中國畫在落筆時,畫家的精神狀態、思想感情、形象捕捉,都是不同的,所以會有“神來之筆”一說,妙也就妙在這里。
《新民周刊》:在生活中,逸覽老師與您的父親一樣,寬宏大量、古道熱心,助人為樂,性格開朗,廣結良緣,擁有很好的畫名與口碑。這是否也源自父親為人對您的影響?
唐逸覽:是的,父親很敬重有學問的人,也總是盡可能地幫助別人。上世紀70年代,有一年冬天,已經12月底了,父親看見一位同事孫祖白先生還穿著單薄的衣衫,在風雪中抖得厲害。那時,大家的生活條件都不好。可是父親還是毫不猶豫地脫下媳婦剛給他織的毛衣,送給了孫先生,要知道那還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呢,他自己的日子也根本不好過。還有一次,他的好友若瓢在香港得了病,沒錢治療,父親就在當地辦了一個畫展,賺來金條,為好友治病籌錢。1983年,父親在杭州住了一段時間,給浙江省殘疾人基金會畫了一百幅畫,用于拍賣換錢,投入殘疾人事業中去,政府表揚他“藝德可風”……這樣的事情不勝枚舉。父親一生的大量畫作,也都是無償送給朋友們的。在他看來,友情是最重要的。
除了畫畫,父親也喜歡喝酒。但他喝酒不是為了喝酒而喝酒,他喝酒是為了求知。父親愛用喝酒來廣交朋友。和詩人、畫家喝酒,談詩作畫,頗為風雅。遇上歷史學者就侃侃而言、博古論今。父親對中醫也略懂一二,也是在和裘沛然等老中醫一起喝酒聊天時,學來的知識。其實,連父親畫畫,也沒有拜過大師,都是和別的畫家在一起,耳濡目染,自學成才的。
《新民周刊》:您的作品與父親有著一脈相承的關系。在今天,古稀之年的您對于自己的繪畫藝術,還有著怎樣的追求與目標?

下圖左:小朵嬌紅別有姿下圖右:松鼠
唐逸覽:盡管我學的是父親的藝術,但我與父親不能相比,無論學識、資歷、造詣,我還要好好努力。當然,學父親的一派也絕不能走死,要慢慢地變,變出自己的面目來。這也是我今天的探索之路。藝術上,后輩要超越前輩,是真的很難的。但我也不懼怕,即使遇上困難,也要一步一個腳印地繼續向前探索。藝術的成功與否,最終是要歷史來評判,要后人來肯定的。
《新民周刊》:唐云先生所處的時代,海派繪畫綺麗多姿。到了今天,似乎海派繪畫已然不復當年的輝煌了。作為曾經的經歷者與見證者,您如何看待海派畫家今天所處的時代?
唐逸覽:所謂的海派畫壇,指的是居住、生活在上海的畫家們,但他們是來自各地的,海納百川,最大特點是雅俗共賞。上個世紀60年代,上海在北京舉辦花鳥畫展,震驚全國。但是現在,那樣占據半壁江山的實力確實已經不存在了。但是上海依然是藏龍臥虎的,實力不容小覷。在全國范圍沒有北京的畫家那么有影響,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上海畫家太過低調,不愿意大肆宣傳、包裝自己的結果。在這一點上,應該要有更為廣闊的心胸與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