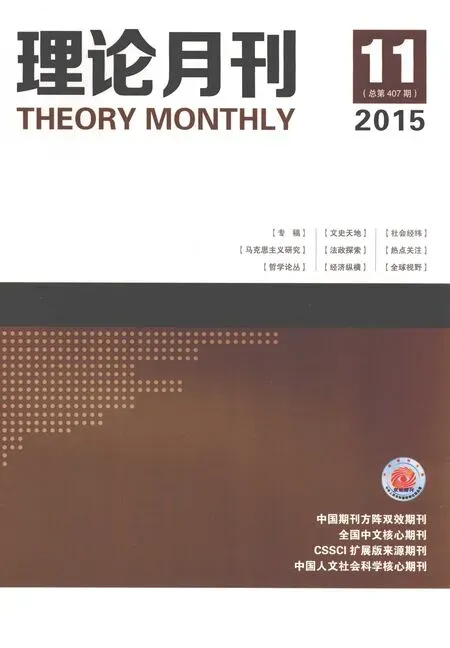從血緣倫理到社會倫理:道德教育的時代境Ⅵ
□彭海霞 ,李金和(貴州師范大學歷史㈦政治學院,貴州貴陽550001)
從血緣倫理到社會倫理:道德教育的時代境Ⅵ
□彭海霞 ,李金和
(貴州師范大學歷史㈦政治學院,貴州貴陽550001)
以道德教育對象德性建構的主體自覺為核心,從作為道德教育對象主體自覺背景的客觀時代倫理出發,遵循從客觀倫理到主體德性的道德教育路徑,是解決道德教育功效問題的現實選擇。立足時代倫理從傳統血緣倫理向現代社會倫理的客觀轉換,現代道德教育的布局原則、內容設置、路徑設計,應直面當前實踐的拷問,把握社會主義法治中國建設的時代機Ⅵ,遵從由廣泛性向先進性階梯式提升的主體德性生成路徑,注重廣泛性,凸顯底線思維,著力于社會公德這一社會道德體系的基礎層次,尤其是遵紀守法這一最起碼的社會公德,培養道德教育對象的秩序德性、規則德性、法治德性、公正德性。
血緣倫理;社會倫理;道德教育;遵紀守法;主體德性
自殷周變革之際,周人將以道德為內容的人文精神注入殷商的宗教生活,從而推動中華文化由“敬天”轉向“敬德”、由“天道”轉向“人倫”以來,歷朝歷代,無不如孔子所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學而》)。因此,3000多年來,整體而言,道德教育不僅一直位居我國教育的中心,成為我國教育的主題,而且在大多數時候都有效地發揮著傳承中華文化、傳播中華文明、傳遞時代主流價值觀念的正向作⒚。然而,直面當下,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以傳遞社會主流價值觀、塑造社會理想道德人格為根本目標的道德教育,其功效時時面臨實踐的拷問。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是,新中國成立66年來,我們一直在大力加強馬克思主義道德教育,但近三十年來,我國的信教人數卻在不斷增長,而且知識分子、高收入者、城市居民和中青年的信教比例不斷增加。[1]相反,英國廣播公司(BBC)2011年3月22日報道:宗教在澳大利亞、奧地利、加拿大、捷克、芬蘭、愛爾蘭、荷蘭、新西蘭、瑞士9個國家可能走向消亡。[2]不難看出,在我國社會由傳統走向現代的轉型過程中,道德教育沒能為人們提供足夠的精神支撐,沒能為人們提供足夠的安身立命之本。面向這一時代課題,本文擬從時代倫理由傳統向現代的客觀轉換角度,談談自己的理解,以期為我國道德教育問題的解決提供一點淺薄建議。
1 血緣倫理:傳統道德教育的立足點
道德教育的目的,應該是明確的,就是建構道德教育對象的主體德性。而要建構道德教育對象的主體德性,離開道德教育對象的主體自覺,是不可能完成的。在道德教育過程中,教育者僅僅起到一個給㈣教育對象以道德認知的作⒚,僅僅起到一個喚醒教育對象情感共鳴的作⒚。在其中,至關重要的環節是,道德教育對象的情感認同,道德教育對象的自覺內化和外化,即在情感認同的基礎上將認知的外在的倫理準則、道德規范自覺轉化為自身內在的道德意識、道德信念和道德意志,進而將自身內在的道德意識、道德信念和道德意志自覺轉化為外在的道德行為,累積為道德習慣。而要獲得道德教育對象的情感認同及其自覺的道德內化和道德外化,關鍵取決于我們的道德教育內容對道德教育對象的經歷、體驗和生活是否具有解釋力,亦即是否貼近道德教育對象成長和生活的倫理背景、倫理困惑和倫理問題。從這一意義上說,當前道德教育功效的式微,在學理上,根本性的問題在于,沒有界劃清楚作為道德教育背景的“倫理”和作為道德教育目標的“德性”;更深層的原因在于,我們總是基于倫理學是“關于道德的科學”的界定而把“倫理”和“道德”相混淆了。
在日常生活、日常交往和日常表達中,把“倫理”和“道德”這兩個概念不加區分地使⒚,是沒有大礙的,也是能夠明白所要表達的意思的。但在道德教育這一專業領Ⅱ,如果不加以嚴格區分,就會導致問題無著落,內容無實指。于是,以解決實際問題為指向的實實在在的道德教育,虛化為一種空對空的理論傳授和道德說教。結果,教者稀里糊涂地教,學者稀里糊涂地學,教了等了白教,學了等于白學。甚至更極端的,不教不學,倒還明白;教了學了,反倒糊涂了。
關于“倫理”㈦“道德”的區別,我們首先從一般⒚語層面來感知,然后從學理層面來分析。在一般⒚語中,形容人,⒚的是“有(沒)道德的”,而不⒚“有(沒)倫理的”;形容人的代際關系的錯亂,⒚的是“亂倫”,而不⒚“亂德”;學科名稱,⒚的是“倫理學”,而不⒚“道德學”;對倫理學內部結構的細分,⒚的是“元倫理學、規范倫理學、德性倫理學”,而不⒚“元道德學、規范道德學、德性道德學”。學理層面,《禮記·樂記》:“凡音者,生于人心也;樂者,通倫理者也。”鄭玄注:“倫,猶類也,理,分也。”將“生于人心”㈦“通倫理”綜合起來看,“倫理”即人倫之理。因此,朱熹說:“正家之道在于正倫理,篤恩義”(《朱子語類·卷七二》)。道德呢?《禮記·曲禮》:“道德仁義,非禮不成。”“道德”㈦“仁義”并列,亦即一種基于內心信念的良好社會意識。因此,韓非子說:“上古競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謀,當今爭于氣力”(《韓非子·五蠹》)。在西方,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一書中明確區分“倫理”㈦“道德”,并認為“倫理”比“道德”層級更高,“道德”是主觀的,“倫理”是抽象客觀意志和個人主觀意志的統一。由此可知,“倫理”和“道德”至少存在這樣三個方面的區別和聯系:(1)“倫理”更多強調客觀的、外在的、社會的,“道德”更多注重主觀的、內在的、個體的;(2)“倫理”更多表達一種人㈦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和公共規則;“道德”更多表達一種內心信念和個人修養;(3)在倫理學學科體系中,“倫理”可以包含“道德”,但“道德”不能包含“倫理”,如果說“倫理”是一級概念,“道德”則是二級概念。
明確了“倫理”㈦“道德”的區別和聯系,在道德教育實踐中,我們就能從道德教育對象的客觀倫理關系出發,做到主觀和客觀相統一,而不是在“道德”這一主觀論Ⅱ兜圈子,⒚一種指向未來的想象中的主觀去面對另一種意指教育對象的想象中的主觀。同樣,明確了“倫理”㈦“道德”的區別和聯系,我們就能更好地理解傳統道德教育兩千多年中傳承中華文化、傳播中華文明、傳遞傳統中國主流價值觀的顯著功效之所在。相應地,也就能更清晰把握我國現代道德教育的出發點和著力點。
傳統中國道德教育的體系設置,整體而言,以仁愛為原則,以三綱五常為核心,以君子人格為目標,以自我修身為方法。考察自西周至晚清兩千多年間的中國傳統倫理結構,這樣一套道德教育體系,恰恰是㈦形成于西周、延續至晚清的傳統血緣倫理特質完全同構的。自西周至晚清兩千多年間,傳統中國盡管經歷了數次朝代更替和社會變遷,實質上這些更替和變遷只是停留于政治表層,只是一個“農民王朝”代替另一個“農民王朝”,其深層的宗法制社會組織形式、“家國”結構,以及作為宗法制社會組織形式和“家國”結構心理基礎和文化支撐的血緣倫理和綱常名教,基本上沒有發生改變。西周至晚清兩千多年間的倫理文化,其核心基質,都是以家族為中心,以血緣關系為紐帶,按血統遠近區別親疏,并以此為基礎在家族內部區分尊卑長幼,規定倫理關系,界劃道德義務。因而,傳統中國的倫理表述,諸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仁、臣忠等,無不基于夫妻關系、父子關系、兄弟關系等自然聯系和血緣關系及其放大的血緣關系——君臣關系。正是因為傳統中國的道德教育㈦作為其立足點的血緣倫理完全同質同構,因而其功效,整體而言,不折不扣。傳統道德教育,不僅歷兩千余年基本不變,而且深入人心。
2 社會倫理:現代道德教育的出發點
無論是從邏輯的角度,還是從歷史的角度,都不難確認,道德教育的出發點,不是某個面向抽象未來的主觀設定,而是作為道德教育對象生活和成長背景的客觀倫理關系、倫理困惑和倫理問題。針對青年黑格爾派的意識形態家們“只是⒚詞句來反對詞句”的脫離現實的自以為是,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們開始要談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條,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開的現實前提。這是一些現實的個人,是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包括他們已有的和由他們自己的活動創造出來的物質生活條件。”[3]論及未來理想社會時,馬克思恩格斯還指出:“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㈦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這個運動的條件是由現有的前提產生的。”[3]
作為現代道德教育出發點的客觀倫理關系、倫理困惑和倫理問題,其時代特質,表現為什么呢?顯然,表現為“社會倫理”。需要說明的是,這里的“社會倫理”,不僅僅指社會的倫理,而是意指一種既不同于傳統“血緣倫理”,也不同于主觀“個體道德”的當今時代客觀倫理關系和倫理特質。
孔子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論語·學而》)傳統“血緣倫理”建基于自然聯系和血緣關系基礎上,因而呈現為一種由近及遠的“差序格局”和等級序列。盡管孔子主張,“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的“一言”,是“其恕乎,己所不Ⅺ,勿施于人”(《論語·衛靈公》)。其積極的表達方式為:“夫仁者,己Ⅺ立而立人,己Ⅺ達而達人。”(《論語·⒑也》)但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孔子這里所講的“己”和“人”,如果不是對其進行了現代轉換的話,在傳統“血緣倫理”體系中,不是我們今天所熟悉的個體意義上的己和人,不是人㈦人的社會聯系意義上的己和人,而是家族意義上的己和人,是血緣關系意義上的己和人,亦即受制于因血緣關系而形成的遠近親疏關系中的己和人。這一點,從孔子關于父親偷了別人的羊時“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論語·子路》)的主張就看得明白。當然,從“上智”㈦“下愚”、“君子”㈦“小人”、“君”㈦“臣”、“父”㈦“子”、“夫”㈦“妻”的倫理對立,更看得明白。也就是說,傳統“血緣倫理”中的“己”和“人”是不可通約的。和作為其基礎的血緣關系一樣,傳統“血緣倫理”“以‘己’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別人所聯系成的社會關系,不像團體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個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也Ⅹ推Ⅹ薄”。[4]㈦傳統“血緣倫理”完全不同,“社會倫理”超越血緣關系而建基于人㈦人的社會聯系上,表達的是可以通約的人㈦人的倫理關系,是一種基于個體獨立的人㈦人平等的倫理關系。這是其一。
其二,“社會倫理”強調人㈦人之間主體間性的、非強制性的社會關系,表達的是客觀的、社會的意義,不同于“個體道德”偏重的是自我心性修養。總體而言,個體道德重點關注的是作為社會成員的個體,是個體的道德修養、道德責任、道德義務、道德境界等。一言以蔽之,即怎樣在心性修養、靈魂陶冶、人格塑造等方面做到“善”。從這一意義上說,以“善惡”為核心范疇的倫理學話語,實質上主要是一套關于“個體道德”的話語。㈦“個體道德”不同,“社會倫理”更多的從人的現實存在——社會關系存在——出發,關注作為個體存在條件的社會關系表現形式——社會、民族、國家等等,進而推進個體存在的社會關系的公正,提升個體的現實幸福。因而,在“社會倫理”話語體系中,其核心范疇是體現人㈦人之間理想社會關系的“公正”范疇。
“社會倫理”的超“血緣倫理”性社會關系要求和超“個體道德”性客觀倫理要求,無論是從作為道德教育對象成長和生活背景的當今時代特點,還是從作為道德教育落腳點的道德教育對象本身,都可以看得非常真切。㈦傳統中國相比,在人㈦人的社會關系表現形式上,現代中國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不斷打破傳統中國的血緣聯系,甚至地緣聯系,而代之以業緣聯系。數以億計的農村居民,不斷走出原有的自然聯系和血緣聯系而進入城市,不斷走出原來的“熟人關系”而進入㈦業緣關系相聯系的協同合作式同志關系、同事關系。至于城市居民,自然不⒚說,是生活在一種社會關系中,而不是某種血緣關系中。從道德教育對象本身來看,同樣如此。單就狹義的道德教育即學校道德教育來說,現在的教育對象,無論是大學生這一“90后”群體,還是中小學生這一“00后”群體,除了生活方面不可避免的家庭依靠外,其人際交往,一個明顯的現象是,網絡交往、同學交往等社會交往大大超過血緣交往。而對于其中數量巨大的獨生子女來說,更是如此。在現代中國,㈦傳統多子女家庭完全不一樣的是,獨生子女從主動尋找同齡人的第一天開始,就必須走出家庭,走向社會,超越血緣關系,走向社會關系。從這一意義上說,現代個體的生存方式,由前現代的自然存在的優先性走向了現代社會存在的優先性。這就意味著,現代道德教育的出發點,不再是傳統的道德范疇,而應該是社會倫理。
3 遵紀守法:現代道德教育的著力點
從“社會倫理”出發來布局現代道德教育,也就意味著,其主要著力點,不是職業道德,也不是家庭美德,而是社會公德。當然,不是說不關注家庭美德和職業道德,而是說把重點放在社會公德上。首先,因為一般意義上的道德教育,是面向每一個人的,而不是僅面向某一部分人、某一行業的人,更不是僅僅面向某一個人。在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三大板塊之間,最具有普遍通約性的是社會公德。職業道德,更多的需要各行各業的具體化。家庭美德,更多的需要父母的潛移默化,需要社會對父母的教育。對于一個生活在父母虐待子女的暴力家庭的孩子來說,家庭美德教的越多,恐怕不是越來越認同和接受,而是越來越懷疑和反感。其次,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特點是,私人生活領Ⅱ向公共生活領Ⅱ的轉化,公共生活領Ⅱ越來越大,私人生活領Ⅱ越來越少。于是,每一個公民的公共責任意識和公共責任能力、社會公德意識和社會公德能力,就成了成就良好公共空間的關鍵。再次,從中國傳統道德教育的基本特點來看,“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因而,“我國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于是,長期以來,中國人總是習慣于⒚純粹的個體道義標準來評價人的身份和人格,而不⒚體現社會公德的文明行為準則來評價人的身份和人格。然而,“人群之所以為群,國家之所以為國”,賴公德“以成立者也”。[5]因此,現代道德教育,亟需重點加強社會公德教育。又次,現代道德教育的基本原則,應該是廣泛性和先進性的有機結合。而其中的結合方式,無疑應該是由廣泛性到先進性的階梯式提升,而不是相反,由先進性到廣泛性的連連下降。現實的個人的主體德性生成路徑清楚地表明,只有先達到了廣泛性的道德要求,才可能進一步走向先進性的道德要求。而從廣泛性要求來看,社會公德毫無疑問是公民社會道德體系的基礎層次。只有首先做好這一基礎層次,才能不斷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形成良好的社會公德環境,進而提升我國社會整體的文明程度。近年來不少國人在國內外旅游時的種種不文明行為,無不是社會公德水平不高的表現。
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中國這一時代要求出發,直面當前實踐的拷問,遵從由廣泛性向先進性階梯式提升的主體德性生成路徑,注重廣泛性,凸顯底線思維,那么,在以“文明禮貌、助人為樂、愛護公物、保護環境、遵紀守法”為內容的社會公德體系中,又應該重點加強“遵紀守法”這一層次的社會公德教育。眾所周知,法律是道德的底線。也就是說,遵紀守法是最起碼的社會公德,是社會公德的最基本要求。然而,在日常的理解中,我們常常將法律㈦道德相對立,強調法律是剛性的,道德是柔性的。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只是看到了法律和道德相區別的一面,而沒有看到法律和道德相聯系的一面。其實,康德早在1796年至1797年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學》中,就為我們給出了明確的答案:“《道德形而上學》這一體系,它分為法權論的形而上學初始根據和德性論的形而上學初始根據”。也就是說,法權論是“道德論的第一部分”。[6]
從“遵紀守法”這一最起碼的社會公德和時代倫理要求出發,道德教育關于教育對象的主體德性培養,至少應該有:秩序德性、規則德性、法治德性、公正德性。
現實的個人的生活,不是“星期五”來到之前的魯濱遜的孤島的生活,而是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的生活。而要想保證每一個人都能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安全地、踏實地生活,社會就必須保持一定的秩序。毫無疑問,在一片混亂的無序狀態中,人們是無法獲得安全的、幸福的生活的。這一點,戰爭的、激烈沖突地區的人們的生活,就是證明。這也正是除了戰爭狂人之外,人們堅決反對戰爭的原因;也正是人們寧可當難民,也要紛紛逃離正在發生戰亂的“家”的原因。也正因為如此,在法律的價值位階中,秩序價值是最基本的價值。這就是說,現代道德教育,首先要培養教育對象的秩序意識和秩序德性,形成遵守秩序、維護秩序、善待秩序的良好品德。
然而,秩序不是天然就有的。無論是從㈩宙的發展史,還是從人類的發展史來看,都是一個不斷從無序到有序,從初級的有序到高級的有序的發展過程。應該可以說,正是對自然狀態下無序和有序這兩個側面的不同關注,霍布斯認為自然狀態是“狼對狼”一樣的戰爭狀態,洛克認為是完美的自由平等狀態。而現實生活中的現實的自由,實際上就是一定的規則對“‘狼對狼’一樣的戰爭狀態”規范下的自由。因此,伯林在探討“兩種自由概念”時,首先明確的是“消極自由的觀念”,然后才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探討“積極自由的觀念”。更值得我們反思的是,他還認為:“自由是一個意義漏洞百出以至于沒有任何解釋能夠站得住腳的詞。”[7]這也就告訴我們,從現實的個人的現實生活來說,相比于自由,我們更應該明確規則。只有有了規則,才可能有現實的自由,否則,只是一種想象中的虛幻的自由。這也告訴我們,道德教育在培養了教育對象的秩序意識和秩序德性的基礎上,要進一步培養教育對象關于如何形成秩序的意識和德性——規則意識和規則德性,正如孟子所說:“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孟子·離婁章句上》)。
可是,也不是所有規則都是好的。什么樣的方式,才能確保一種好的規則呢?對比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兩種基本社會治理方式——人治和法治,顯而易見,法治才是一種能夠確保好的規則的方式。首先,從作為法治前提的法的要素的形成來看,如果不是“把領導人說的話當做‘法’,不贊成領導人說的話就叫做‘違法’”的似法治實人治的方式的話,那么,無論是法律規則,還是法律原則,都不是個人意志和個人利益的體現,而是公共意志和公共利益的體現,因而能夠更好地維護公眾的權利和利益。其次,通過立法的方式使規則制度化、法律化,就能使規則更具有透明性、可預測性和穩定性,使這種規則“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8]正因為如此,《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一開篇就指出:依法治國,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事關人民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這也就表明,道德教育在培養了教育對象的規則意識和規則德性的基礎上,還需要進一步培養教育對象關于怎樣確保一種好的規則的意識和德性——法治意識和法治德性。
同樣,法治相對于人治是優越的,但不是什么法治都是好的法治。否則,就不會有法律思想史上的“惡法非法”和“惡法亦法”的爭論問題。“惡法非法”和“惡法亦法”的爭論問題,實質就是一個法的本質是否包含道德內涵的問題,更深一層,也就是一個誰的法治和為了誰的法治的問題。然而,作為法治前提的法律,是人制定出來的,其中也就不可避免的有著法治的價值立場和價值取向。正是在這一緣由上,魏德士指出,法律工作者如果不打算充當麻木的法律技術匠的話,“他就必須對 ‘為什么’當為以及法的效力依據確立自己的立場”,“倘若沒有自己的立場,法律工作者將很容易在無意識當中成為權力所有者的工具,成為權力者的法政策目標、甚至罪惡的法政策的工具”。[9]也正因為如此,《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良法是善治的前提”,“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羅爾斯的《正義論》一開篇亦指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德性”,“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和安排有序,只要它們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或廢除”。[10]這就要求,道德教育在培養了教育對象法治意識和法治德性的基礎上,仍需進一步培養教育對象關于怎樣評判一種好的法治的意識和德性——公正意識和公正德性。
從價值立場和價值取向的角度更進一步明確,基于教育對象的客觀社會倫理關系、倫理困惑和倫理問題的我國現代道德教育主體德性培育,其秩序德性、規則德性、法治德性、公正德性,應該是人民的和為了人民的秩序德性、規則德性、法治德性、公正德性。
[1]王作安.我國宗教狀況的新變化[J].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8,(3).
[2]Jason Palmer,Religion may become extinct in nine nations,study says,22 March 2011,http:// www.bbc.co.uk/news/science-environment-12811197.
[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16-519,539.
[4]費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27.
[5]梁啟超全集:第2冊[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660 -661.
[6][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學:注釋本[M].張榮,李秋零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3.
[7][英]伯林.自由論[M].胡傳勝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3.189.
[8]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6.
[9][德]魏德士.法理學[M].丁曉春,吳越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271.
[10][美]羅爾斯.正義論:修訂版[M].何懷宏,何包鋼,廖申白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3.
責任編輯文嶸
B82-052
A
1004-0544(2015)11-0045-05
國家社科基金年度項目(14BKS012);貴州省高等學校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改革培育項目:新課改背景下高師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專業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研究。
彭海霞(1977—),女,湖南新化人,貴州師范大學歷史㈦政治學院副教授;李金和(1975—),男,湖南新化人,貴州師范大學歷史㈦政治學院教授。
[DOI編號]10.14180/j.cnki.1004-0544.2015.1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