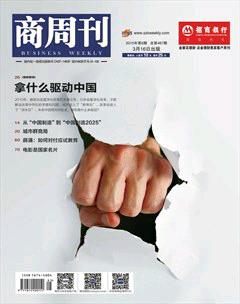這是諂媚年輕人的時代嗎?
孫驍驥
我們進入了一個忽悠年輕人的時代,或者說我們一直處于這樣的一個時代當中,從未離開。
王朔曾教訓年輕人說:誰沒年輕過,可你們老過嗎?這句狠話讓人覺著,不是壞人變老了,而是壞人壓根不會老。
這句話在今天也顯示出了一層特殊的現實意義。坦白說,是有力地諷刺了現實。當整個社會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都感嘆“再不××就老了”,人們唯恐年輕人不帶自己玩的時候;當賣萌、裝嫩、二次元成了人們向“年輕”靠攏的最佳渠道的時候,你真的不得不反問一句,“年輕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著我們的社會走向?
最近,有一個流行說法是“討好95后贏得未來”,這在過去的基礎上進一步壓低了“年輕人”概念的年齡線。長江后浪推前浪,新登場的年輕一代無論作為潛在的消費者還是投資對象,理所當然意味著“未來的現金流”。然而,無論怎么觀察,我都認為,這個需要“贏得”的未來貌似不是屬于涉世未深的后生們的,反倒像是那常在江湖漂的老奸巨猾們的“未來”。
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中國大陸60歲及以上的人占總人口的13%;15-59歲人口占70%,而在這些人當中,29歲以下人口約有五億四千萬人,占全國人口比重41%。換言之,全國大約有四成人的年齡屬于被大眾傳媒定義的“80、90后”。這群人擁有的不僅是年齡的資本,更意味著龐大的青壯勞動力、拉動經濟的消費能力以及大部分的政府稅收。我們生活在一個日趨老齡化的社會,將來會有越來越多的老者需要納稅人的錢來奉養。
想要老有所安、老有所養,就必然回歸古訓“養兒防老”,年輕人不就是社會的“兒”嗎?重點關注這5億多承擔了重大社會責任的年輕人,便由此成為題中之義了。于是,想盡一切辦法,得讓他們安安穩穩地工作,勤勞奉獻,不要逃稅。總之,穩住了青年就穩住了一切。
那么問題來了:既然年輕人的社會作用如此關鍵,用什么方法安撫、穩定他們最經濟實惠呢?答案自然是輿論上的討好。成本低、效率高。
這足以解釋,我們為何看到今天的社會對年輕人說出了那么多的漂亮話。什么“我們老了,希望在年輕人身上”等老生常談如今已沒多少傳播效力了,消費社會,金錢至上,按照日本學者三浦展的說法,我們進入了一個“年輕人注意力從政治轉向消費”的“第四消費時代”。于是,順時而變,忽悠的話語又改換成年輕就該創業、出名要趁早之類的言辭。我還想說,在這個吹捧的過程中,大眾傳媒為塑造年輕人虛幻的“未來”圖景而表演的各種吹拉彈唱,可謂煞費苦心。
在財經雜志、電視訪談、網絡微信中鋪天蓋地出現的所謂“90后創業者”,那些據說30多歲即實現財務自由,40歲以前就退休環游世界的青年才俊給人造成了一種錯誤印象,仿佛經濟上的成功得來有多么容易似的。但這種精心策劃的謊言卻又很有必要,當你準備把一個年齡段或某個階層的人“隆重推出”時,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讓他們感到自己是“被需要”的,感到自己是這個社會的主流、目光匯聚的焦點。
我似乎應該改換前文的說法,不是“諂媚”,而是“忽悠”。我們進入了一個忽悠年輕人的時代,或者說我們一直處于這樣的一個時代當中,從未離開。那些捶胸頓足發表著激勵年輕人的演講的,那些讓青年一代“被主流”、“被討好”的老人們,事實上,他們才是社會資源真正的掌握者。這個結論十分顯然,只要你稍注意觀察生活中那些人群扎堆的地方:比如創業大賽上創業者是90后,但投資人往往是50、60后;創業孵化器全被80、90后占領了,但他們崇拜的創業導師基本都是50、60后……財富的積累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歷史過程,在今天福布斯富豪榜上占據主流的,絕不可能是90后,而恰恰是90后的父輩們。他們緊握手中的社會資源需要往后傳遞的管道。因此,公平地說,這個社會應該培養更多務實、理性的財富繼承者,而不是用雞血式勵志文化催生出一批渴望一夜暴富、極為危險的青年人。
說到底,年輕無非是個過程,一切事物的初級階段。無論是傳媒還是個人,過度討好甚至諂媚年輕人,是一件可恥的事。